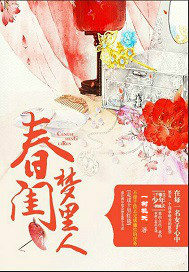于椒兰宫养伤这段时日,木丝言夜里前去雅光的寝殿内寻她多次,她都未在寝殿之中。
而后她逐渐发觉,这段时日中,她都极少见到雅光。她私下同宫内的宮婢们打听后才知,雅光是去了莫央宫侍奉蔡侯。
她气的跑回屋子里,抄起丹雪便要去找蔡候算账。
她踏门而出时,却见妃月慵懒地抱着肩,依靠在廊下。
她见木丝言走了出来,从怀中掏出一支墨色的瓷瓶,勾着手指,示意木丝言过她身前去。
早前在郡城时,木丝言亲眼瞧见过,妃月用瓷瓶里的蛊虫,将孔武有力的白素撂倒了。
她心里有些害怕,迟疑了片刻,却还是走到她面前。
“绣衣阁利用西夷蛊女在你身体里放了七只噬心蛊,看来是楚王已经开始懂得,如何操控西夷蛊女。”妃月将手上的瓷瓶塞到木丝言的手中。
“不过当初攻打影山时,我提前将蛊王的书房烧了,大部分阴损的制蛊之法,都在那场火中被抹去了,楚王他们也并不知高阶蛊女和低阶蛊女的区别,所以,若想要他们不知你身体里的噬心蛊被我解开了,便记得在月圆之时,服用瓷瓶里面的药粒,早晚一颗各一次。”
“这药会使你身体呈现出与噬心蛊相同的反应状态,想必绣衣阁之中,为你施蛊的蛊女是个低阶,她瞧不出我在你身上布下的障眼法,你且能顺利地蒙混过去。”
木丝言紧紧地握着瓷瓶,喉咙有些发干地问道:“阿月,你这是在赶我走吗?”
妃月长叹了一口气道:“我也不想赶你走,只是,现在的雅光公主同寄人篱下并无区别,更何况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啊。”
为了留下木丝言养伤,雅光才会被蔡候胁迫着,每夜前去莫央宫承欢吧。
激于愤怒,木丝言才会暴躁地拿着丹雪,要去莫央宫寻蔡侯拼命。
妃月一开始为木丝言解蛊时,便猜到那卑鄙的蔡侯,会以此做要挟,逼迫雅光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
所以,当初她在询问雅光公主时,才会当着她的面去质疑蔡侯。
如今,她蛊女身份暴露了才是最为麻烦的事情。
蔡国尚佛,自是容不得蛊毒这淫邪之物,而她,刚好是制造蛊毒的淫邪之人。
从今往后,这椒兰宫,怕是她妃月再也护不住雅光了。
“阿月。”木丝言双眸有些湿润,她趁着将瓷瓶放入袖袋的间隙,揉了揉眼睛。
“我此次回去楚国料理一些私事,待今年重阳祭祀过后,我便回尔雅,带你和雅光公主离开,我们寻处地方安居,远离这些是非黑白。”木丝言看着妃月,双眸之中澄澈清明,满载希望。
妃月歪着头莞尔一笑:“那你可要快着些,可别磨蹭到楚王寻到了高阶蛊女,做出连蛊王都无法解开的金蚕噬心蛊放到你身上,到时候你食言了,被困在了绣衣阁,我也不好责怪你不是?”
“若是当真有那一天,我便送你和雅光去一处好地方,自己回去绣衣阁赴死便好。”木丝言高傲地仰着下巴,誓在妃月面前,绝不做食言之人。
“那可不成,没你来耕田,我和雅光公主岂不是要饿死了。”妃月捂着嘴,明媚地笑着。
她还记得郡城关时,木丝言信誓旦旦要带着雅光私奔的傻瓜模样,既乖巧又执着。
木丝言于七日后回到了绣衣阁,由于蔡国的任务她只完成了一半,解决了那些生变的绣衣使,却没有杀掉锦葵。
她被白尧带去了绣衣阁传言之中的兽坑,但见三丈深渊的石坑下,游荡着些许长着獠牙的山兽。
石坑下吹来一股浓重的腥臭味,木丝言知道这腥臭味是腐尸的味道,想必绣衣阁之中有许多人命,便是陨落在这处石坑里吧。
“初次任务未完成的绣衣使,是要被丢下这石坑中自生自灭的,可你是暗人,这绣衣阁之中,初次没有完成任务的暗人,你可是第一个。”白尧勾着嘴角玩味地说道。
“我本是可以圆满完成任务的。”想到蔡国的妃月和雅光还在等着她,她便将心中对白尧的厌恶压了下去,换了一副笑颜,轻挑地朝着白尧笑道。
“只不过在刺杀锦葵那夜,不知怎地胸口忽生剜心一般地疼痛,痛到连丹雪都拿不起来了,这才刺杀未遂,还由此惊动了蔡宫之中的禁军,险些连命都丢了。”木丝言故意地露出手臂上的伤痕,并且将刺杀锦葵的谎言编织的极为流畅。
蔡国的绣衣使都被她杀光了,谎言的真假便没有人再为他们验证,所以不管她说什么,都不会有人拆穿她。
白尧的眼底略过一阵心疼,他沉下双眸,对一旁看管兽坑的侍卫道:“去将碧罗押来。”
侍卫领命前去,不刻,便押着一个身穿鸦青色交领曲裾的女子走了过来。
木丝言认出,这个叫碧罗的女子,便是那日在石室之中,推搡时娴的师尊。
当她抬头看到木丝言时,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面容,就好似她不相信木丝言会平安地回到绣衣阁。
“碧罗,绣衣阁待你可不薄,你做出这样的事情,可有想过后果?”白尧环住木丝言的腰身,慵懒地说道。
碧罗面色发青,因为害怕,不停地喘着粗气。
“掌司,我,我有将安宁丸送到她暗室之中,也有告诉过她缓解剜心之痛的办法,是她自己没有随身携带安宁丸,不关碧罗的事。”她双瞳飘忽不定,可却几次地偷瞄木丝言,似是想从木丝言的神情之中判定,她会不会追究到底。
白尧捏了一把木丝言的纤腰,低着头问她:“阿言,她说的可否属实?”
木丝言面无表情地看着碧罗,而后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我并没有见到她说的那些东西,想来她是把药送给了鬼吧?”
“不对,我有将安宁丸送去过你的暗室,就在妆匮的第二个格子,还有一张写了安宁丸的服用的时间和缓解剜心之痛的方法。”碧罗是在木丝言离开绣衣阁之后,送去她房间的,也是为了不备之需。若她平安地回来,留有充足的证据能保自己一命。
“阿言,要如何处置她?”白尧并未留心碧罗的辩解,反而兴致盎然地看着木丝言。
“既然她将安宁丸送给了鬼,那就送她去见鬼,让她亲自去问一问鬼,有没有收到她的安宁丸。”木丝言转过头,面无表情地与白尧对视。
生于光芒之中,圈养在暖室里的花,终于长出了带毒的花刺。
在碧罗的求饶,谩骂,嘶吼的声音中,白尧拉着木丝言行至到兽坑前,看着被推下去的碧罗,在山兽的獠牙间,被撕扯的七零八落。
山间的一切回归于平静,白尧拥着她回到了她所在的暗室,并将碧罗安放的安宁丸递给她,告诉她,在下次月圆,胸口疼痛之时,服用一粒,便可感受不到剜心之痛。
木丝言记着妃月话,能止住噬心蛊的痛有三种方法,一是剜心,二是服用失去痛感的药,三是将蛊虫从身体中分离。
想是这安宁丸,便是可以让人失去痛感的药吧。
白尧看着木丝言望着安宁丸的瓷瓶发呆,便跪坐与她的身旁道:“如今,你以暗人的名义留在了绣衣阁,便不能再有木丝言这个称呼了,你需要一个代称来代替你的名字,就像时娴的红棉一样。”
木丝言沉寂了片刻,而后轻启朱唇道:“欒。”
她记得父亲曾经与她说过:“木,万物之所以始生,木之为言触也,春生之性,你叫木丝言,便是父亲希望你,如同春生一般,芊芊而立。”
她就是木丝言,永远都是。
白尧闻后,淡然一笑。
他拉起木丝言的手,将她拽入怀里:“到底还是放不下你的过往,留在这里与我相伴,觉得委屈吗?”
木丝言没有说话,现在的她,不过是被白尧禁锢的牢笼之物,哪里配谈什么委屈。
白尧见她没有回应,便低下头去看她。
她的双眸虽然空洞,却无暇又清透,像是摇曳在风中的玉兰,散着阵阵幽香。
白尧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去,吻住了她的柔唇。
木丝言于神游之中惊醒,她抬起手企图推开白尧,却被他抱得更紧。
他顺势将木丝言压在小榻之上,伸手扯开了她腰间的衣带。
“不要。”木丝言弓起身子抗拒,别过脸避开白尧的薄唇。
可白尧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迫不及待地撕扯着木丝言的衣襟,将脸埋入她温热的脖颈之间,汲取着她的甘甜。
木丝言握紧手上的瓷瓶,思虑了片刻后,猛地朝白尧的额头上砸去。
白尧的额头被砸了一个口子,登时血流如注。
他捂着额头坐起身,瞠目结舌地看着木丝言。
木丝言白皙的脸上溅上了些许血迹,她坐起身面色冰冷地看着白尧:“若还想留我在绣衣阁里为你卖命,便不要再做这些越界的事情。”
“没有我的庇护,你当真以为能在这绣衣阁里存活多久?”白尧将额角的血迹抹干净,钳制着木丝言的双肩质问。
“没有你的庇护,我也从蔡国禁军的围困中杀了出来,你的庇护对时娴来说或许有用,但对我来说,不过是枷锁。”木丝言双眸凌厉,一字一句地戳着白尧的痛处。
“你若对我有恨,便将我交给楚王邀功,我不畏惧他用任何方法来折磨我,逼我交出攻山之器的图纸,大不了赐我一死,木家被诛的那日,我本就该死。”
白尧钳制着木丝言的双手缓缓地松了开,他颓废地望着木丝言,愧疚地道:“木家被诛,楚王亦是痛心,可为了楚国千秋万世,这些牺牲算得什么?”
“楚国不是凭着罔顾礼法,大好喜功便能千秋万世。”木丝言双目通红。
说什么千秋万世,不过都是一己之私。
“你不懂,你若能懂,便会心甘情愿地交出攻山之器的图纸。”白尧站起身,留恋她一眼,而后缓缓走出了门去。
接下来的一段时日,白尧和白素二人都没再出现于木丝言的暗室之中。传授木丝言武功心法的,也换了一个人。
这人也带着面具,从不外露真容,单从身形上猜测,倒像是个女子。
在传授心法时她也不说话,用纸笔写清后,令木丝言照她所写的步骤来练习。
木丝言于暗室内苦练剑法的日子再次重新开始了,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她今时可以作暗人的身份,带着面具在绣衣阁内畅通无阻地行走。
趁此方便,她开始在绣衣阁内寻找时娴的踪迹。
可找了大半月,却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找到,时娴就像在绣衣阁之内,消失了一般。
没过几日,便到了重阳祭祀,楚王携楚国重臣,前往乌蒙山岱宗明堂,祭祀天神青帝。
绣衣阁派遣五名暗人前去跟随队伍,暗中保护楚王,木丝言便在这五人其中。
楚王带足了人马浩浩汤汤地自东楚出发,过洞庭往乌蒙山而去。
木丝言御马,隐藏于林木之中,跟随在队伍的最末,以防遭人偷袭。
乌蒙山位于楚燕边界,由七座峰峦组成,岱宗明堂位于最东的岱峰之中。
越朝着乌蒙山走近,天气越是晴好,夹道一路由枯黄的落叶变成了柏翠松青,倒是比巴陵山的景色要美上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