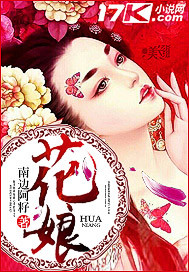阿月立即掏出瓷瓶打了开,从瓷瓶之中放出几根细线将白素困于地上,无法移动。
雅光公主思索了片刻,而后朝着白素的坐骑走去。
她将白素挂于马上的柘木熊首弓取了下来,转身走到白素身旁。
“这是我送你的,现在我要把它收回来。”
她神色平静,可目光之中仍有不舍之意。
“至于欠你的三箭,将来若是有机会,我会还给你。”她将熊首弓背在身后,朝着木丝言走了过去。
“谢谢你,阿言。”雅光公主抱了抱她,与她做最后的道别。
“好好活下去,我在尔雅等着你来寻我。”
她与阿月转过身,缓缓地朝着送嫁队伍的方向走过去。
待她登上车马后,队伍逐渐远去,慢慢地消失于天地尽头。
白素还在一声一声地唤着雅光的名字,可他挣脱不开束缚蛊,眼睁睁地看着雅光的身影远远消失,直至不见。
木丝言转过身,低头看着这个曾经叱咤战场,令人闻风丧胆的战神白素。如今的他,满身的残叶,俊朗的脸上沾满了尘土,双眼猩红犹如疯魔。
“你又输了。”木丝言轻声道。
“这是最后一次,她走了,不会再烦着你了,你可开心了?”
年少时的他,太过于热爱争强好胜,他并不懂雅光公主无理取闹般的纠缠。怕她流眼泪,是因为她哭起来的模样让人烦躁不安。执着于用各种办法击败他,让他屈服于她淫威之下的骄傲模样,更让他厌烦至极。
待他功成名就,心中开始空荡时,才明白过来,那时陪着他一路闹过来的雅光公主,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侵占了他的整颗心。
可是当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他的公主已经离开他了,并且再也不会回来了。
木丝言御马离开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悲怆的哭声,她没有回头,而是快速地朝着家的方向飞奔。
她的见燊哥哥还在等着她回去。
回到吴桥时,正是赶在时见燊公学放课之后,他这些日子总在这个时候于城门口徘徊,时而往远张望,时而来回踱步,使踩在冰雪之中的双脚回温。
少时,他见到了御马而归的木丝言,喜眉笑眼地朝着她招手。
木丝言停马不前,落下马去,朝着他飞奔了过去。
她扑在他的怀中,抱了他很久。
时见燊嘴上嗔道:“这才离开多久,怎生让你如此念我?”
“念君之心,寸阴若岁。”木丝言在他怀中说道。
听闻此话,时见燊将她抱得更紧了,后二人相携归家。
眼瞧着婚期将至,木丝言不知是出于紧张还是害怕,心中总有不安之感。
时娴安慰着她,说可能是因为是木丝言的第一次婚典,难免会焦虑。
木丝言听起来总觉着哪里不对,难不成婚典还能有第二次?
时娴想想也是,便让她做些事来分散精力,便不会想那么多从而导致焦虑紧张。
于是,木丝言便拿起木刻的工具,开始做起了手工。
她见时见燊不善武,怕他将来出门会有此而得亏,便又做出了一个机关手镯,送给了他。
时见燊嘴上温柔地说着不需要,可还是在木丝言送给他的第二天就带在手上了。
逐除那日一早,天空飘起了雪花,吴桥城内,一路的红妆伴着白雪格外耀眼夺目。
木丝言身穿玄纁嫁衣,头戴华冠,乖巧地坐在铜镜前。邻家的妇人为她抹粉施黛,在她面前不停地夸耀着她的好容颜,和时见燊的天赐鸿福。
木丝言只是在害羞地笑着,并未做任何回应。
不过多时,姨母走进屋内问她,可否见到时娴。
木丝言摇了摇头。
姨母听闻后面色慌张,急忙打发屋内闲着的人去四处找。
木丝言见姨母已有些六神无主,便站起身将她拉来身前问道,最后一次见时娴是在什么时候。
姨母翻着眼睛,认真地回想了片刻道:“昨日午时,她说要入山去见一个朋友,晚些就回,可是一直到晚上用饭时,她都没有回来,我怕她夜里归来饿,便放了些饭食在她房里,可今日去她屋内,见我昨日晚上送去她屋内的饭食压根就没有动过痕迹,床铺也是冷的,并无睡过地模样。”
“我本不想在此时惊扰到你和见燊的婚典,可这夜里这么冷,时娴又一夜未归,我真怕她出事。”姨母红了眼睛,惊慌失措地拉着木丝言的手说道。
木丝言起身连忙要冲出屋去,却被几个妇人拉住了,争相恐后地劝说她,新妇莫要未嫁时就穿着嫁衣四处跑,容易招惹祸事。
她这辈子经历的祸事已经够多了,不再相差这一两件。如今时娴生死未卜,她怎可能会安心与她的兄长成婚。
她跑了出去,找到了姨丈,将时娴失踪的事情告知了姨丈,并让他动员城内所有人去找。
而后,她迁出了马,骑着它往时娴时常采药的山林中去了。
天空的雪飘的愈渐密集,山路又极不好走。木丝言只能下马而行,一边喊着时娴的名字,一边缓缓地往林中走去。
不刻,她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熟悉的马蹄声响,她回身凝望,见一身闪耀的金乌,正朝着木丝言跑了过来。
木丝言激动地抱住了它,双手搔弄着它的鬃毛笑道:“金乌,我的金乌,你是逃出来了吗,你来寻我了,你来寻我了。”
“它不是逃出来的。”木丝言的背后传来一人的说话声。
木丝言回头望去,见到了穿着绀青色狐裘斗篷的白尧。
她连忙又将目光转了回来。
她希望这次的相遇是她的一场梦,她并不希望白尧能找到她,确切来说,她希望白尧一辈子都找不到她。
“是太久不见面,阿言忘了我是谁吗?”他抬起脚朝着木丝言缓缓走近。
木丝言惊慌失措,她抬起头看了一眼金乌,便翻身上马,想要逃走。
“你若走了,时娴便永远都回不来了。”白尧拉住了金乌的缰绳,仰着头对木丝言说道。
“你把时娴带去哪里了?”木丝言御着金乌,想要挣脱开白尧的拉扯。
可是金乌似是很听白尧的话,并没有将她带远,随后白尧也翻身上了马,坐在了木丝言的身后。
“我把她藏了起来,她暂时很安全,至于她以后能否安全,要看你是否愿意听我的话。”白尧趴在木丝言的耳旁,浅浅地吹着热气。
随着他话语而来的,还有阵阵带着香玉鼠姑花芳香的热气,木丝言霎时汗毛耸立,回身便是一掌,将白尧推开。
白尧受了木丝言这不痒不痛的一掌,向后倒去,起身后便抓住了木丝言的两只手腕,猛地向后一扯,将她困在了自己的怀中。
“阿言,当真要放下我,去和别人成亲吗?”白尧侧过脸,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木丝言冷笑道:“你不是也另娶她人了吗,怎地你放下就行,我放下便不行了吗?”
白尧神色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冷淡,他缓缓道:“这才是我认识的木丝言,方才那怯懦地模样,当真不像你。”
“我方才并未是怯懦。”木丝言缓缓地碰到了手腕上的机关。
“我只是厌恶你的触碰。”
手镯上的铜珠飞出,击打到了白尧小腿,他吃痛地放开了木丝言。
木丝言猛地踏着马鞍,缓缓下落于地面。
“你今日若不与我走,我便一把火烧了吴桥。”白尧恼羞成怒地道。
“哦?”木丝言张狂地笑道:“好一个金印紫绶的白丞相,趋炎附势后,便学着开始横行无忌,鱼肉百姓了。”
白尧不再与她多费口舌,他骑着金乌朝着木丝言飞奔而去。
待到木丝言三尺远的距离时,金乌停下了脚步,无论白尧怎样鞭打,都不肯再向前一步。
刹那间,木丝言似是在金乌的眼中看到了眼泪。
木丝言大声喝道:“住手,你若想要抓我,便亲自来抓,同一个畜生较什么劲。”
白尧停了手,见木丝言再次扣动了手镯上的机关,几个铜珠一同朝他飞来。
白尧侧身下马,抽出了腰间的青霜朝木丝言刺去。
“阿言,小心。”一道黑影掠过,将木丝言抱在怀中,滚落到一旁的雪地中。
木丝言毫发无损地起身,看到时见燊的手臂上被划开了一道剑痕。
好在冬日里的衣服厚实,时见燊只是礼服的衣袂被划去了一块,并没有受伤。
“你以后,莫要再这样吓我。”她吓的哭出了声,紧紧地抱住了时见燊。
若是方才那一剑真的伤到他,木丝言势必要内疚而死。
时见燊坐起了身,将木丝言抱在怀中,他抬起头,目光凶狠地看着白尧。
“于今日起,阿言便是我的发妻,她昨日的种种,我会与她一并承担。”时见燊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是木丝言这辈子听到的最好听的情话。
她抬起头看着平时温柔敦厚的时见燊,不顾所有保护她地模样而热泪盈眶。
白尧恼羞成怒地大喝:“你们尚未礼成,她还不是你的妻。”
“那她也不是你的妻,你亦无资格来干涉。”时见燊扶着木丝言站起身,却依旧将木丝言紧紧抱在怀中。
白尧怒发冲冠:“可我偏要干涉。”
他手执青霜朝着时见燊刺去。
木丝言抬起腿,将地上的雪横扫而起,暂时阻挡了白尧的视线,而后拉着时见燊往远处跑去。
白尧挥袖拨开朝他而来的雪,紧紧地追着他们二人。
此刻的白尧,心如刀割,恨不得将时见燊碎尸万段。
时见燊不如常年习武的白尧脚程快,才跑了几步早已是气喘吁吁。
木丝言见这样下去,并不能使时见燊转危为安,反而会激怒白尧,甚至可能会牵连到吴桥。
她猛地放开时见燊的手,转身朝白尧扑去。
白尧诧异地停住了脚步,连忙收回青霜剑。
木丝言将白尧扑倒于地上,抬起手朝他左脸刮了一巴掌。
“你胆敢用我造的剑去伤他?”木丝言抬起手再次抡了白尧的右脸。
白尧从没这般被人毫无章法地打过,他被木丝言的巴掌打的脑袋嗡嗡作响,慌乱中他死死地扣住了木丝言的手腕。
“你若不想让我伤他,便跟我回东楚。”白尧一个挺身反将木丝言压于身下。
“我可以同你回去,可若你在我同你回到东楚后,不信守诺言,伤害吴桥城里面的任何一个无关之人,我发誓,我会杀了你,还有白家所有可杀之人。”木丝言咬牙切齿地说道。
白尧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忽而勾着嘴角淡淡一笑。
“白家所有可杀之人?”白尧的话中有嘲讽,因为他并不相信,凭着弱不禁风的木丝言能杀掉白素。
须臾,时见燊手持一块巨石,便朝着白尧的后脑砸去。
木丝言见状连忙抱着白尧滚去了一旁,躲开这一击。
她的见燊哥哥举世无双,温雅无暇,她不能让他为了自己,而双手染满鲜血,更何况伤了楚国的丞相,那是处以极刑的大罪。
一个木家已经够了,不能再因为她,失了时家。
时见燊错愕地看着木丝言,不明白她为何要救下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