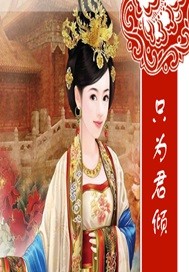“不就是驯服了一匹破马么,有什么了不起。”距离木丝言和姚绾二人不远处的一个姑娘细声嘲讽道。
“孋姐姐,你有所不知,那银鬃沙可是连主君都无法驾驭的呢?”坐在那姑娘身旁的另个女孩子说道。
虽然这话是在抬举木丝言,可话语之中听不到任何友好的语气。
“姐姐们说笑了,不过是主君抬爱,没跟我一个小丫头一般见识罢了,换做你们,也会是一样的结果。”木丝言拒绝莫名其妙的抬举,并顺便出口怼回了她们。
“呦呵,倒是个撒泼的。”被称为孋姐姐的人冷嘲道。
木丝言没再说话,她以为士族大家的姑娘都会如同姚绾这般温婉和煦,却没想还真有喜欢寻衅挑拨的。
她也懒得理她们,索性就当做听不到她们的挖苦,卖力地为雅光撒着月桂。
月夕祭舞结束后,木丝言的胳膊已经累的酸麻,本想着能回家去好好休息,却被雅光当场截获,邀她一同入宫参加月夕饮宴。
木丝言用了诸多理由尝试拒绝,比如身上的祭服不合适,头上的步摇不合适,月桂花的香味不合适。
可木丝言所提出拒绝的理由,一一都被雅光公主摆平了。
雅光公主的马车里已经准备了木丝言更换的衣服,而且为了搭配她的姓氏,还十分贴心地准备了水绿色的衣裙。
木丝言微怔,不经大脑地问了句:“那姚绾姐姐的,你莫不是准备了绾色?”
雅光公主略有吃惊地笑道:“你个小机灵,是怎么知道的?”
于是,木丝言被雅光公主和姚绾二人一左一右地挟持上了马车,并且亲自帮助她换好了衣裙。
儿时的木丝言长的太过讨喜,讨喜到姚绾将她的发髻梳成了平双髻,宛如神庙之中的神童子一般娇俏可爱。
她并未在意自己的装扮,只是慨叹,乘着大公主的车马入宫果然同自己入宫时不同。
她每次入宫都是给阿翁送午后小食,阿翁所在的驻马场就在第一道宫门口不远,进入第一道宫门之后便是要步行。宫门到驻马场的距离倒是不远,可怨就怨在驻马场的占地广阔的可怕,光马厩就有百十余间,还有马场,和摆放马车的库房,她每次走到阿翁所在的太仆阁都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而乘着大公主的马车,可以一直行进到第四道宫门口再下车去,这也是木丝言第一次看到第四道宫门里的光景。
她看着楚宫的朱墙玄瓦,灯火辉煌,不由得慨叹起宫殿的巍峨高耸。
雅光看着她发呆的模样,以为她是第一次入宫,甚是胆怯,便走上前拉过她的手道:“莫要怕,今日的饮宴都是主君的近臣,你阿翁和父亲可都在,还有你家的大哥,叫什么来着?”
木丝言十分感谢雅光公主的照应,知道她与自己闲话家常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紧张之感,便接口道:“叫木丝慎。”
“对,是叫木丝慎的,在云梦城做教书掌司的,主君还说要为他做主寻个士族家的姑娘呢。”雅光公主笑道。
木丝言想了想,自家大哥是到了该成亲的年纪,不过看自家的父亲和母亲的模样,倒是不急。
与雅光公主闲话家常之时,已过一处石桥,稍行片刻,便到达一处楼阁。
木丝言提着裙角随雅光公主走上石阶,登高后见一处灯火通明,四面通透的楼台。
透过这四面通透的楼台,能清楚地瞧见不远处的方廊上有妖娆的舞姬跳着舞,还有随之而来的淡淡丝竹之音。
这样远观,既不被丝竹打扰的彻底,亦能观赏的完整,倒也精巧。
楼台之中的饮宴本是到了觥筹交错时,自雅光公主带着她和姚绾走入,饮宴忽而安静了些许。
跪拜于襄公之时,襄公询问银鬃沙现下的情况。
木丝言乖巧地回答,争取做到滴水不漏。
许是今日的琼浆玉酿使襄公惬意万分,便没有再同她一个小丫头过不去,又询问了大公主几句月夕祭月舞的事情,便命她们入座去了。
木丝言瞧见自家大哥的身旁有空位,便抬脚要过去,谁知又被雅光拉了回来,盛情邀请与她同坐。
木丝言瞥了一眼高位上的襄公,乖乖地跟在了雅光的身后。
她坐在雅光的右侧,旁边挨着的是白家少年。
在她尚未确定坐在身旁的究竟是白素还是白尧,所以极力地保持沉稳和安静,不观四处,执着于案上的香糕和炙肉。
少时,雅光递来一爵翠色液体给她,她双手接过,鼻尖略过一阵馥郁的芳香。
她知道手上的应当是今年供奉的御酒,陈年翠竹夜,带着万分好奇想要尝试一口。举杯放于嘴边时,手臂上忽然传来一阵力道,将她送往嘴边的美酒压了下去,稍后一只素白又纤长的手拿走了她手上的酒杯。
她现在可以确定坐在她身旁的白家少年到底是谁了。
她瘪着嘴,侧过脸幽怨地看着白尧将她的酒一饮而尽,为了避免注目,她还是忍着没有说话。
在雅光递来第二盏翠竹液的时候,木丝言尽量背着白尧去接,可美酒才到嘴边时,又被他抢走了。
她一生气,索性做到了雅光公主身旁,与她共饮一爵,这次白尧没再上手抢酒喝。
雅光回过头,看着白尧笑了笑道:“尧公子似是管的有些过了。”
白尧长叹了一口气道:“她尚未饮过酒,若是等下醉了,做了逾距之事,公主可要想个法子护着她才好。”
雅光公主楞了片刻,转身抢下了木丝言手中的酒,将她赶回了原位。
木丝言吧唧着嘴,无限地回味着翠竹液的芬芳,只那么一口,她便觉着喝酒着实是一件能让人欢畅的事情。
须臾,有宫人来报,说白家的素公子与琼公子和孋家的修公子打了起来。
众人皆是惊慌失措,唯有木丝言开始晕乎乎。
几个少年被押来殿前,襄公闻讯原因之时,芈琼和孋修一致对外地指责白素先动了手,而且从外表来看,芈琼和孋修二人被揍的相当难看。
襄公问寻白素原因时,白素并未做过多言语的解释,想来他又是悍名在外,一时间指责他的人逐渐占了多数。
雅光公主幸灾乐祸地悄声道:“瞧瞧这回还有谁能帮你。”
还未等白尧起身为白素求情,坐在雅光左侧的昭公子忽然起身,行至殿前跪下道:“主君若是要怪,便怪儿臣吧。”
芈昭这突如其来的求情,让殿内的人疑惑不已,直到昭公子道出了白素为何痛打芈琼和孋修时,众人这才知晓,白素乃是赤血丹心的忠义之人,而非一介莽夫而已。
一年前,周王将周公主玉琢赐给楚国做新妇,能与她身份和年纪相配的便只有君夫人所生之子的芈昭。
玉琢公主嫁入楚国之后,被封为灵玉夫人,却始终不愿同芈昭行夫妻之事。芈昭自觉年岁尚小,不便过早历经人事,因此也没有再勉强灵玉夫人。二人虽同住昭华宫,算是举案齐眉,和谐相处,却未有真正的圆房。
于是,昭华宫内便传出了风言风语,说昭公子在夫妻之事那方面不行。
于方才的饮宴上,芈琼和孋修二人,便是用此风言风语来羞辱芈昭。碍于情面,芈昭并未做声,但与芈昭关系甚好的白素便坐不住了,趁着二人离席小解之时,狠狠地暴揍了二人一顿。
事情的原委一道出,襄公气的发狂,他最痛恨的便是庶子爬到嫡子头上耀武扬威,他持起案上的酒爵,猛地朝着芈琼砸了过去。
霎时,芈琼的额角血流如注。
芈琼和孋修二人早就吓的失了魂,跪在地上说尽各种求饶的话,就连的上卿孋家老丈也上前为自家子孙求着情。
木丝言恍惚之间,听到了事情的来历和经过,有些听懂了,有些没听懂,介于她现在已经是半梦半醒的状态,便拉住雅光问道:“夫妻之事,是什么事,很重要吗,为什么偏要行,不行会如何?”
殿前都是求饶的声音,偏偏她这一问十分突兀,且声音过于张扬,以至于所有人都朝着雅光公主望去。
雅光公主脸色已是泛青,连忙抱住木丝言,捂住了她的嘴,并且配合着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笑容。
木丝言常年驯马,力气大得很,她被雅光公主捂得难受,随即挣脱开她的怀抱,朝着白尧倒去了。
白尧好心的接住了她,可她偏又犯起了酒浑,拉着白尧问道:“她不说,那你说,夫妻之事,是什么事,小白,你说啊?”
白尧倒是对夫妻之事不怎么关心,倒是她叫他小白这事,确实得找个机会问问她才行。
她抱着白尧的手臂不停地痴缠询问,一直到殿内有人大笑了起来。
“都是小孩子,童言无忌,主君莫怪。”说话的正是木丝言的阿翁,木太仆。
他起身端起酒爵朝着襄公一拜,而后一饮而尽。
“是啊,主君,琼公子和孋修他们也都是孩子,孩子之间的玩笑和打闹,皆是无心,教育过后便好,不必如此大动干戈啊。”孋上卿诚恳地劝道。
襄公此时酒醒了些,便不似方才那般癫狂,他见芈琼头上的血洞,也是颇为心疼。他吩咐宫人先将太医署的医官宣来为芈琼包扎,又各自惩罚了芈琼和孋修思过,并禁止宫内的传播风言风语,违反的宫人立即处死。
一场危机被木丝言几句酒后浑话化解了,亦是木太仆的巧言及时,否则有心之人再添油加醋地说些什么,襄公必是当场将芈琼赶出东楚。
平息闹事的当事人也是酒醒之后才知情,她现在依旧沉浸在翠竹液带来的美梦之中,以至于雅光公主不得已求了襄公,将木丝言留在了宫里,同她回到了章华台。
木丝言于第二日晌午醒来,她擦了擦嘴上的口水坐起身,迷迷糊糊地打量着四周。
看着如此奢华的寝殿,她猜想自己一定还在梦中。
倒下头准备继续睡的时候,却被雅光提着脖颈,从床上拉了起来。
这回她算彻底清醒了。
在雅光的嘴里得知自己昨夜的壮举后,尤甚是抱着白尧的手臂又亲又啃,木丝言甚想当场撞柱去死,可是她依旧不知夫妻之事到底是什么事,于是带着这个疑问,她回到了家中,问起了自己的母亲。
当天傍晚,本来不想揍她的华容郡主,再次手持柳条,从院内,追她追去了木老太爷的书房。
木丝言知道在宫内言行不当,为木家丢脸了,才要同木老太爷求情,却被赶来的阿翁救了。
阿翁说她昨日的言行不当不但无过,还有功。
她倒是很想在问一问阿翁,夫妻之事到底是什么事,可见母亲一脸凶猛,便乖乖地闭嘴了。
也是阿翁讲出来,她才知道,昨日阿翁借着她的童言无忌说了下去,才将芈琼和孋修那两个小子救了。
阿翁之所以说木丝言立了功,是因为孋修那小子在辈分上算是木丝言的表兄。
木老太爷早殇的二儿子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女儿,名唤木心,便是嫁到孋家做良妻了。
早前的孋家不过是楚国都城一介小吏,木老太爷看重孋家的淳厚,便放心地将自己的孙女嫁了过去。可后来,孋家水涨船高,做了襄公身边的上卿,便瞧不上木家着亲家了。
这便是在木丝言出生之后,两家人都不怎么走动的根本原因。
华容郡主告诉木丝言,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姑姑曾偷偷来看过她,只不过孋家后来管的严了,限制了小姑姑的自由,她便很少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