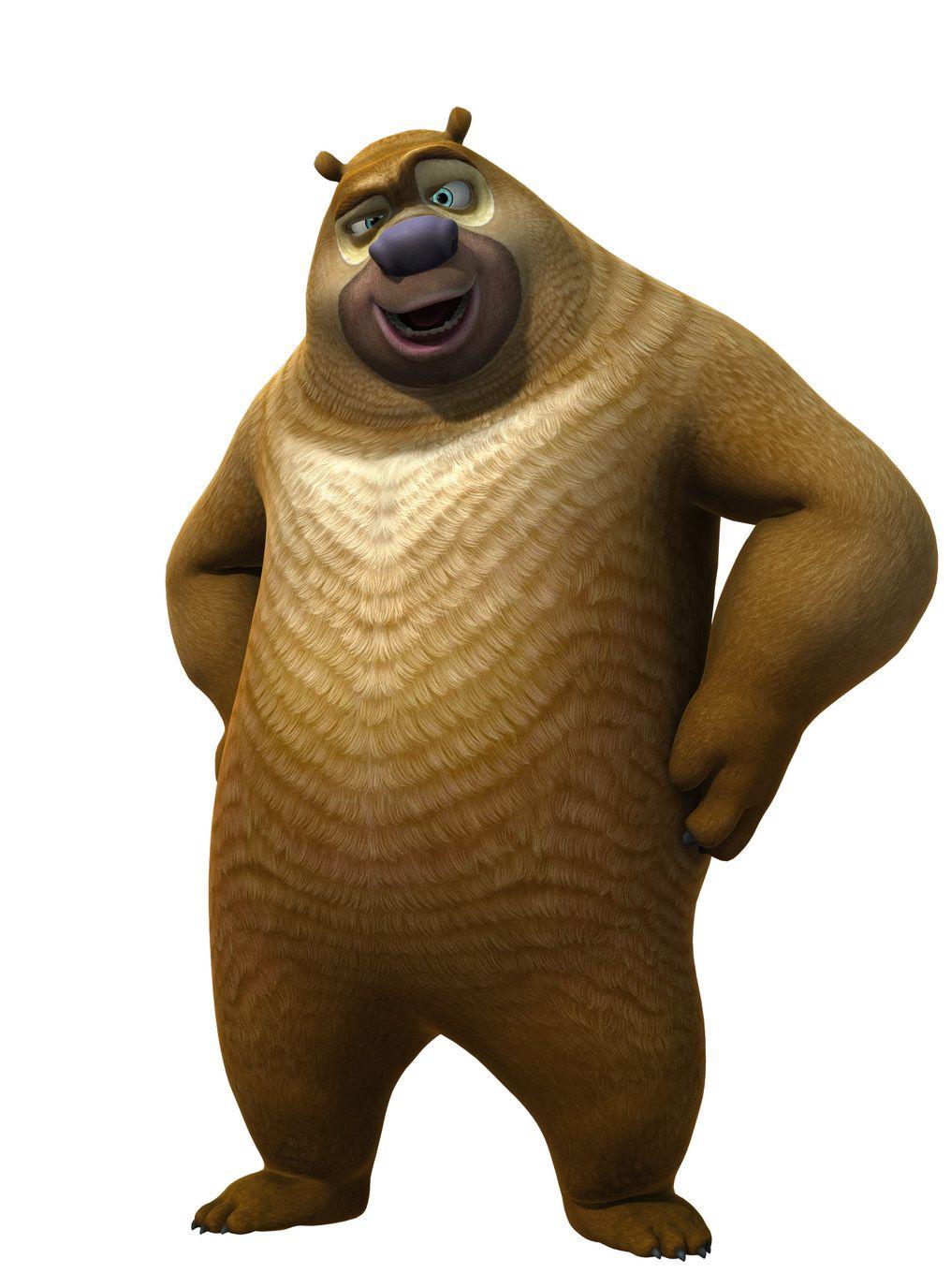滚烫的茶瓮从泥炉上翻滚下来,砸在男子腿上,更有些许滚水分别溅在昭明太子的衣袂与妫翼的小腿上。
男子拂袖打落茶瓮,匆忙站起身抖落着身上的水珠。
幸而他躲得快,热水顺着他的衣裳滑落,并未浸入里面的寝衣中去。
确定自己无事后,低头望见妫翼裤腿湿了一片,他喜上心头,抽出袖袋之中的手帕,向妫翼的小腿摸索过去。
那素白的一双手还没碰到妫翼,便被她猛地握住,随后轻描淡写地“咔哒”一声,扭了断。
男子登时哭嚎着在地上打起了滚儿,甚是委屈娇嗔道:“奴做错了什么,竟得陈侯这般暴虐地对待?”
妫翼拂去裤腿上的水迹,头不抬地说道:“还能这般愚蠢地问出口来,可见身处风月之所,并没能叫你学会曲意逢迎的生存之道,胆敢肖想不合时宜的,便要预料到自己的后果。”
男子因疼痛所露出的狰狞模样,吓坏了打翻茶瓮的女婢,她即刻匍匐在地,抖如筛糠地求饶。
“陈侯莫急着动怒,先确认是否烫伤,不如先行随我去暖阁更衣,传医官来瞧一瞧。”昭明太子湿了半边臂膀,却不如陈侯的暴戾,他丝毫未动怒火,言语举止似是如美玉一般温雅。
妫翼垂眸淡笑,妖媚且锋利地双眸扫过那女婢:“昭明太子果然怜香惜玉,孤且未怪罪祸首,太子反倒先行替个女婢解围。”
妫翼的话乍一听并无他意,可入了昭明太子的耳中,便令他觉着,是妫翼的醋意萌生,他心中窃喜,恨不得当即拉着她的手,带去暖阁更衣。
“并非如此,陈侯愤愤而然,忧愠难解,我虽不能慰藉陈侯心中不畅,却也不愿陈侯时常处于愁绪当中。”昭明太子道。
“孤的愠怒,昭明太子岂会不知?”妫翼厌恶他在众人面前的虚伪,他明明对妘缨,对她存着不轨之心,却能如此面不改色地为自己开脱。
这般蝇营狗苟,令她恶心。
“莫不是陈侯还在怨怼,今夜并未送去驿馆的邀请?”昭明太子温和地笑道。
他冠冕堂皇地同妫翼言语暧昧,对妘缨的筹谋却只字不提,他心血来潮地想要携妫翼入室更衣,更能心安地任由女婢打翻装着滚水的陶瓮。
他的豺狼之心,昭然若揭,却在极力地粉饰着太平,继续将妫翼当做以前那般,戏弄于鼓掌之间。
妫翼转过头,看着仍旧在地上打滚申吟的男子,她伸出手,重击男子脖颈。
男子随后止住声音,昏死过去。
妫翼心中的怒火,随着方才宣泄般地出手,消去不少。
她缓了一口气,冷却心头的愤怒,道:“话以至此,既是太子承认怠慢了孤,那就请太子按周礼之制还礼,与孤同杯共饮,以释前嫌,来化干戈,如此这般,孤才更加能有恃无恐地留在筵席,陪伴太子身侧。”
昭明太子逐渐止住笑容,他凝望着眼眸深邃的妫翼,心中已然明了她接下来想要做的事。
他目光扫过一直沉默不言的妘缨,内心的苦闷与不甘汇集成一股从天而降的冷流,冲刷着他的热烈,撕扯着他坠入冰渊。
昭明太子心中如历经海啸般的波折,妫翼并不在乎,她不想再浪费多余的口舌,只道:“孤不愿咄咄逼人,更不耻反客为主,太子若觉着勉强,便不必了吧,孤这便携宋公离去,不搅尔等欢愉。”
妫翼缓缓起身,与众人作别,随后扯着妘缨的手,作势要离去。
“陈侯自行离去便是,何故带着宋公一同?”楚公见妘缨要走,立即起身阻拦。
妫翼冷笑,道:“楚公这般纠缠,可是舍不得孤,那不如随孤同去如何?”
楚公眉宇紧锁,颇为厌恶,道:“谁要随你一同?”
“那怎地,昭明太子尚未留客,楚公倒是喧宾夺主强留宋公,这旁人不知的,到会认为楚公对宋公有着什么肖想。”妫翼轻蔑道。
楚公被妫翼点透了心思,有些心虚,可转眼一想,肖想妘缨对他来说,又不是一件说不得的羞耻之事。
况且曾在东楚,楚公确实与妘缨亲密无间,男欢女爱,对他来说亦如吃饭睡觉一般平常。
他欲再度开口辩驳,妫翼先行打断了他:“孤劝楚公好自为之,这殿中方才也有个胡乱肖想的,也不知现在还有没有气了。”
随着妫翼的言语,楚公目光掠过不远处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男子。
他即刻闭上了嘴,不知为何,心里竟有些发憷。
男欢女爱本没有错,可错在实时上的楚公,在享受男欢女爱时,只顾及自己的欢愉,从不管对方是否愿意。
见楚公缩头不语,妫翼冷哼一声,再次携妘缨转身欲走时。
昭明太子忽而起身,道:“陈侯留步。”
“我愿与陈侯同杯共饮。”
妫翼停下脚步,脸上是不屑一顾的冷笑,可在她转过身,面向众人时,脸上神情却变回了原来地模样。
她稀松平常地指着方在妘缨位置后面立着的女婢道:“你来斟酒。”
女婢身躯一颤,双眸不自主地向罗绮望去。
罗绮面色发紧,他自然知道妫翼所令女婢的酒瓮里面掺了什么,且如今也已心知肚明,自己在殿外的那些所作所为,定然是被妫翼瞧见了。
他起身方开口阻止,却听妫翼道:“这女婢瓮中的酒,本是太子赐给宋公的,可不巧最近宋公有位挚爱惨遭横死,方过世不久,宋公正为其守祭,不便饮酒,孤虽不才,扪心自问,也配得上太子这一瓮的赏赐。 ”
“这可是孤,成为陈国君侯之后,首次厚着脸皮向太子讨赏呢?”
妫翼这一番言语,堵住了罗绮的嘴,他僵在原地,硬是将更换酒瓮的话语吞了下去,只能寄期望于那奉酒的女婢。
那女婢神色慌乱,许久不动身,且神色迷茫地望着妫翼。
“怎么,孤说的话不及昭明太子,即便是个奉酒的婢子,也要看对主人摇尾巴吗?”妫翼语气凌冽,使得女婢浑身一颤,身体不能自主地向她行去。
待快到妫翼身边时,女婢脚下一软,连同手上的酒瓮向地面上栽去。
妫翼一早料到会如此,脚下蓄力,猛地向那女婢飞去。
她一只手稳稳地接住酒瓮,另一只手薅住女婢的衣带。
“看来这园中的婢子各个身子盈盈弱弱,也难怪昭明太子会特别怜惜。”她一边说着良善温和的话语,一边松开了抓着女婢的手。
那女婢猛地瘫软在地上,却顾不得摔疼,连忙伏在地上求饶。
妫翼手持酒瓮,仰头豪饮,嘴角留下些许酒液,待瓮中酒液还剩对半时,停了下来。
她用袖口擦了擦嘴角,捧着酒瓮,缓缓踏着台阶向昭明太子走去。
二人渐渐相隔咫尺,却已然远于天涯。
昭明太子从她手中接过酒瓮后,沿着她方才豪饮过的印记,将剩余酒液饮尽。
辛辣之感登时穿胸而过,化成一支支的铁锥,戳向心口处的金蚕母蛊。
他强撑着站立,摇摇欲坠想要触及妫翼的脸庞。
妫翼回退一步,令昭明太子扑了个空。
昭明太子苦笑,心中又是一阵刺痛。
也不知是因为妫翼拒绝了他的触碰,还是那酒液中的添加,惊醒了心房之中的金蚕母蛊,片刻过后,他神色痛苦,面容通红地向妫翼倒过去。
妫翼见状,如同怕被沾染上脏污的事物一般,再度向后退了几步,眼睁睁地看着昭明太子覆面栽倒于地上。
最先起身的是罗绮,他猛地冲过去,抱起昭明太子,愤怒地质问妫翼道:“即知太子不适,陈侯却还咄咄相逼与太子同杯共饮,陈侯此刻可已然心安?
妫翼冷笑,道:“咄咄相逼的岂是孤,尔等逼迫宋公饮酒时,便不是蓄意逼迫了,况且太子当着众人应许孤同杯共饮,你不过是一小臣,有甚资格来质问孤?”
罗绮心虚,可见昭明太子晕倒,心中甚是不爽,故而又道:“既是如此,眼见太子不胜酒力,陈侯身为故友,连扶衬一把都不肯吗?”
妫翼环住肩膀,歪着头,悠然地笑道:“这台上四周站着多少奴仆婢子,太子不胜酒力,不斥责他们的失职,偏叫孤伸手,原来安阳这些恃宠而骄,以下犯上的奴才们,是由罗小臣来照护着的,难不成这园中的上下,与你有什么苟且不成?”
妫翼随意的三两句话语,令罗绮吓出一身冷汗,他目光瞥向不远处的楚公,发觉他并未听到妫翼方才所言,这才放下心来与妫翼赔罪道:“方才是小臣一时心急,还望陈侯莫怪。”
她故意不张扬这里的龌龊,并不是为了昭明太子,而是她厌恶楚公,所以并不想当着他的面,揭开这园中的勾连。
她就是喜欢看着他们互相算计,至死方休。
“嗬,孤可不敢责怪小臣,所幸太子与孤共饮的酒液,乃是由小臣经手的,若是孤从外面带来,小臣指不定便会冤枉孤为太子投毒,皆时,孤这一两句,怕是也已辨不清了。”妫翼借话点拨罗绮,让他心里明白,殿外他做的事情,她已经知道的一清二楚。
罗绮鼻尖冒汗,将昭明太子放心地交给后面围上来的女婢。
他从容地站起身,与妫翼作揖赔罪道:“陈侯哪里的话,太子前段时间偶感风寒,才愈不久,确实不宜饮酒,小臣方才也是关心则乱,才口出狂言。”
“陈侯不记小人过,待太子无恙,逐除祭礼一过,小臣定然设宴为陈侯赔罪。”
妫翼摆摆手,神情温和,道:“设宴赔罪便免了,将来若是孤有求于罗小臣,还要请小臣莫忘今日之许。”
罗绮一怔,仿若一只脚踏入了妫翼的圈套中。
故而他沉了沉心神,笑道:“陈侯抬举小臣,小臣也不过是太子身旁的掌事,哪能有用处可帮陈侯的。”
妫翼倒也不急,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太子能有罗小臣这般忠义之士相伴左右,却是幸事。”
随后,她缓缓上前,贴在罗绮耳旁,细声道
“但愿,不如前人一般,善终不得”
妫翼气息如兰,温软轻和,却令罗绮打了个冷颤。
于罗绮发愣时,妫翼已然转过身,似是在替他决定宾客的去留:“太子既然不胜酒力,这席便散了吧,如何?”
未等罗绮说话,楚公却拍案而起,怒火冲天地指着妫翼,欲口出狂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