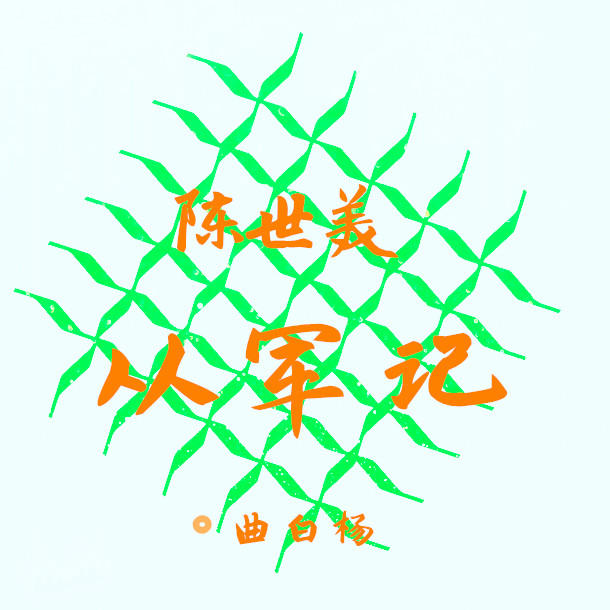“如若两样都不选,国君便遣散了旌阳兵,若愿意留在陈国的,便按照陈国的军队的俸禄来接收,并且给予留在陈国服役的旌阳兵一笔安家的钱财,让其接来家里的人,与其共同在陈国生活,若不愿意的,限七日之内离开陈地回到卫国旌阳去。”
“至于卫姬夫人的结果,定是有国君来决定的。”
“如若卫国公两样都选了,倒也是省了国君心思,将这两样全部送还给卫国公便好,这样也算是卖了个人情,让卫国公记得国君的宽宏大量。”
我眼神惊艳地看着百里肆,他俯身内敛,眼神却神采奕奕,说话时既带着坚定的胸有成竹,又含着温润君子的谦卑。
我细细地瞧着他的神情并且深陷其中,就连父亲喊我,我都没有听见。
手臂轻微地摇晃让我回神,我侧过头看着老茶,却被老茶告知父亲已经接连喊了四声我的小字。
我连忙回道父亲,却不知方才在我失神时,他说了什么。
“你可学到了什么?”父亲开口问。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实话,百里肆的心机,我这一辈子都学不到。
“孤听闻,你昨日恢复了崇明的禁军统领之位,又恢复了老茶的内侍总管之位。”父亲问道。
我点了点头,连忙回道:“昨日父亲昏睡,所以我便私自做了主。”
“口谕既出,也要及时由刀笔吏拟写出来,执盖玉印后,再贯以落实,这次,孤代你拟了文书,盖了玉印,往后你自己出的口谕,要自己完成后续之事,可懂?”父亲挥了挥手,便让老茶从书阁的绘金麒麟的檀香木盒子里,拿出一个锦袋装着的事物。
父亲将它递给我,告知这里面装着的是福祥公主的玉印,权力等同于国位继承人。
我接过,忽而觉得肩膀有些沉重。
“卫姬夫人与旌阳兵的事情得以解决,现如今就只有那些宗亲公卿了,绥绥,你惹的事情,你可否想到了什么主意?”父亲靠在凭几上看着我。
我将玉印收好,抬起头回道:“免官的免官,放逐的放逐,该杀的便杀。”
“听说,你昨日还将太仆的官给免了?”父亲问道。
我垂下头,心有忐忑地回答道“是他自己不要的,可不是我免去的。”
父亲长叹了一口气,而后缓缓地道:“你要知道,若是同时免去那么多宗亲与老臣的官位,会使陈国陷入动荡之中,更何况你现在还未找到更好的人选去替代他们,那五人,一个是地官司徒,一个是马政太仆,一个是典狱廷尉,一个是人官司空,还有一个是礼官宗伯,听闻那李家的少师也被你禁足在李家,不得外出。”
这样一说,好像除了昶伯和百里肆,我将陈国所有的公卿全都给抓了起来,好似这事儿挺严重的。
随着父亲的话音落下,我也长叹了一口气道:“谁让他们阻止我救父亲了,我也很为难,我也想要皆大欢喜,可他们不答应啊。”
“他们不答应,你便另想办法,莫要一下都将他们关起来,好在昨夜信北君放走了身为宗亲的太仆与司空,否则今日,宗亲的那些长者早就来孤这里告状了。”父亲说道。
“绥绥知道了。”我撅着嘴,不明白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宗亲,为什么要供着。
“孤给你三日时间,这三日你要想出来如何软硬兼施,平定你惹得那些人,你可以向孤求助,也可以向昶伯或是信北君求助,三日之后,孤要听你的办法。”父亲说完话,便叫来了老茶,撤走他身后的凭几。
我俯身回着“诺”。
“至于卫姬夫人和旌阳兵的事,就按照信北君说的去做,孤身子困乏,这信便要劳烦信北君代孤笔,明日朝立议事之后,你再呈给孤。”老茶将父亲的身子放平,并将锦衾掖在了他的双臂下。
百里肆也应了一声,诺。
父亲抬了抬手,示意我们可自行离开了。我与百里肆和昶伯便一同俯身离开了景寿宫。
景寿宫门前的高台上,欒与长信宫的宫娥正等着我。
见我同百里肆和昶伯一同走了出来,便上前作揖。
“作为长信宫的管事女官,应当时时刻刻劝诫公主的言行,在众目之下,让公主独自一人不顾礼节跑出了宫,不说是罔顾了礼法,但凭这宫规,长信宫所有奴婢也免不了责罚。”百里肆说道。
欒与她身后的宫娥皆花容失色,随即跪在了地上,伏地求饶道:“奴婢们知错了,奴婢下次定劝诫公主注意言行,绝对不会再有今日这样的事发生。”
我觉着百里肆这厮,自打在我近了这陈宫之后,忽而变得越来越讨人嫌了起来。
不说万事要管着我,就连我身边的人,他也能说责罚就责罚,一点面子都不给。
我一直认为他还记着我给他下迷香的仇,所以对他还是仍有退让。
“信北君,我也是一时糊涂了,由于太过于担心父亲,这才没顾忌到礼数,犯错的人本就是我,跟他人不相干,若要罚,那便罚我好了。”我轻轻扯了扯他的衣袂,神色无辜地道。
“公主要知道,惩罚不是目的,目的是公主今后要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百里肆侧过身看着我道。
“信北君说的是,我明日就像父亲上秉,寻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来做少师,专心学习六艺。”我谄笑道。
“其实公主面前就有一人挺适合的。”站在一旁的昶伯突然开口。
我歪着头看了看信北君,又看了看昶伯道;“难道昶伯想要亲自教我六艺?”
闻我言语,昶伯笑了起来,他摇了摇头道:“我这老人家可没那么多精力了,国君叫我掌管陈国半壁的兵力我都觉着分身乏术,哪里还有力气教你六艺。”
“礼、月、数、射、御、书,这六艺没有一项是信北君不精通的,公主何必再找,面前的信北君便是作为少师的最好人选。”
我强颜欢笑地看着百里肆,见他面含笑意,似是很赞同昶伯的话。
若是百里肆成了少师,我已经能想象得到,今后在陈宫之中的生活,我必定过的十分悲苦。
我一边与信北君和昶伯相聊,一边抬手示意欒与宫娥赶紧站起身,莫要再跪着了。
欒懂我意,连忙带着宫娥起身,站在一旁。
随着宫娥的起身,我瞧见高台之下,由一寺人正带着一个身穿铠甲的兵卫走了过来。
瞧那兵卫的服制,倒不像是禁军的人。
昶伯也发现了,他忽地变了脸,不再言笑,却让我有种十分不好的预感。
“秉昶伯,燎公子方才闯营,虐杀了几个旌阳兵,导致营中过半的旌阳兵欲有反意,飨将军现已将他们暂且安抚了下来,并且将燎公子关在营中,现如何处置,飨将军派我前来请示昶伯。”那人跪在地上,向昶伯禀报着圣安城外暂安的大营之中,所发生的事。
“燎公子不是身负重伤吗,怎地会跑去城外大营之中,还有他为何要虐杀旌阳兵?”昶伯紧锁着眉头问道。
跪在地上的兵卫一无所知地摇了摇头。
“是我答应他的。”我开口说道。
昶伯讶异地看着我,而后摇了摇头叹道:“公主当真是糊涂了。”
他拂袖叫了跪在地上兵卫一同,连忙转身疾步地走下了景寿宫的高台。
我见状提着裙子想要跟在昶伯后面,却一把被百里肆拉了回来。
“昶伯是骑马入宫,你身上没有出宫的宫牌,若跟着昶伯,你没法出去。”
我望着信北君,满眼焦急。
昨天夜里,确实是我答应妫燎,让他处置几个旌阳兵的,虽然我并不知他为何一定要虐杀那几个旌阳兵,但他给了我赵南子乱政的证据,做以交换。若是因为这事让他被昶伯给处置了,那我这承诺便是冠冕堂皇了。
“公主,带着你的女官与我一同乘车马先出宫,留有一宫娥在景寿宫门口等,待国君醒后,即刻禀报国君你与我一同出宫的事宜。”说罢信北君便带着我与欒一同,尾随着昶伯一同往正阳门走去。
由于百里肆被父亲特许,车马可过正阳门,因而我才能偷偷地坐在他的马车里面,跟着他一同出宫。
看守着旌阳兵的大营设在圣安城北郊,我与百里肆赶到的时候,却见大营的中央的空地上,所有的旌阳兵围坐成一个圈,圈中央则是几个血肉模糊的尸体。
许是百里肆深觉我会害怕,连忙抬手捂住我的双眼。
我觉着他这人怎地变了矫情,想当初在勤政殿东阁的时候,可是看着我拿短剑伤人的,怎会觉着我会害怕死人不成。
我拉掉他的手,信步走了进去。
那些旌阳兵将那几人的尸身围的水泄不通,让人没办法靠近。我仰着头,看着那些残肢,蓦然有些好奇,这妫燎到底与这几人有何仇怨,居然下这样重的手。
片刻,营帐之中走出四人,昶伯走在最前,跟在昶伯身后的,是一个身穿银甲,披着藏青色披风,手持长戟的壮汉。
走在壮汉身侧的,便是方才前去宫内通知昶伯的那位小兵。而他身前押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
我眯眼瞧去,看清了那个被绑着结结实实的人,正是妫燎。
他青丝四散,衣襟凌乱,花白的衣服上全都是密密麻麻的血痕。这旧伤未好,便添新伤,更使他走路踉跄,面色凄惨。
“各位皆是卫国的精兵强将,更为识时务者的英豪,老身昨夜承诺各位必定毫发无损,今日便出了这样的事,老身愧对各位,在此求得各位原谅。”昶伯俯身一拜,与对面跪坐的旌阳兵道。
“若要我们原谅也不难,杀了他。”跪坐在最前面的一位士兵带头说道。
而后,所有的旌阳兵全都异口同声地喊道:“杀了他,杀了他。”
妫燎勉强地站直身子,他面带笑容地扫视着所有的想要杀了他的人,也是此时他看到了我。
他定住了视线,带着功成身就地笑容缓缓地朝我眨了眨眼。可我却觉着他的笑容异常的凄零,就像是终首山上寒冬的风一样,刮在脸上,割得直痛。
“如若不杀他,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兄弟。”又有旌阳兵带着头,振臂高呼着。
呼喊声一波接着一波,甚至有旌阳兵站起了身,拿起地上的石头,朝着妫燎砸了过去。
有人起头,就有人效仿。
妫燎身上被束缚着麻绳,身上又是新伤加旧伤,他躲过了一个,却躲不过第二个。
他被石头砸倒在地,额头顿时血流如注。
昶伯连忙命人将妫燎护住,又派兵前来镇压这些意图造反的旌阳兵。
百里肆怕伤到我,便要拉着我往远走。
走了两步,我见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处高台,高台上驾着一座大鼓。
我见状甩开了百里肆的手,奋力地跑向了高台上,拿起一旁的鼓锤,用力地敲响大鼓。
咚咚咚的声音传出,也吸引了那些蠢蠢欲动的旌阳兵。我听地上的杂乱声没了,便转过身,站在高台上看着他们。
“昶伯昨夜在本宫的面前以自身信义保了你们,本宫才决定不杀你们,让你们安然无恙,等待一道旨意回家,可如今看来,本宫这个决定怕是错了。”
“尔等与卫姬夫人一同乱我陈国,残害我父,对本宫更是围追堵截,你们自认为这罪是可以免死吗?”
“本宫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们,我大陈不惧任何,若尔等还恬不知耻地暴乱,本宫便将你们全都砍了,丢到潼安的林子里面喂狼。”
我胸中虽如击鼓震天,亦是慌乱无章,可面目却不经波澜,声音更是振聋发瞶。
旌阳兵安定了下来,他们相互看着对方,面上露出了胆怯之情,我还窃喜,自己吓唬住了这些人,少时,便有个声音传了过来。
“一个并无实权的山野公主,得以这般猖狂?”说话的人,仍是最开始带头的那个。
我双拳紧握,更是目眦尽裂地盯着他看。
“来人,将方才辱我之人砍了。”
昶伯没有动,所以这大营之中的任何一位士兵也都没有动。
那人仰头看着我,满脸都是嘲讽的笑,似是在告诉我,这陈国像来都是谁说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