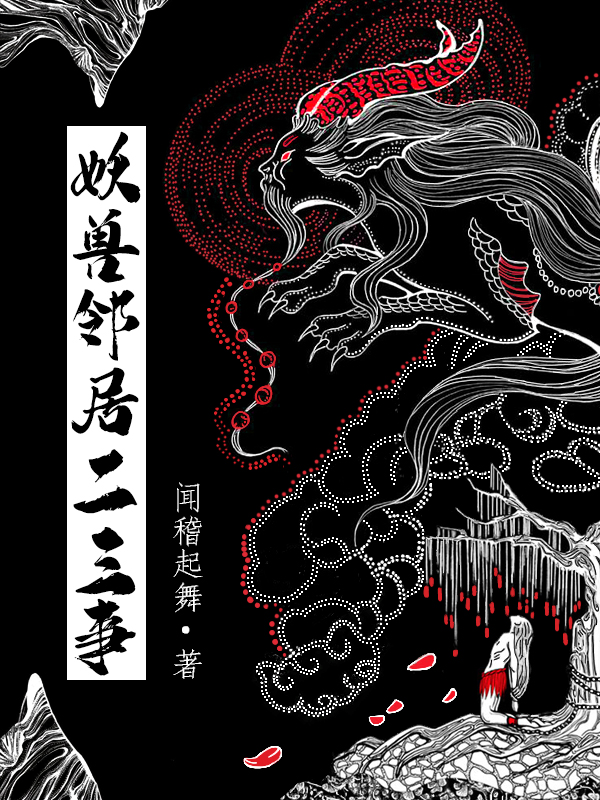一路吵吵闹闹,在天将黑的时候,五人终于见到了目的地。
岔路口,必然不是什么安全所在。所以在老江湖苏仲碌的建议下,一行人借着最后的天光,又急行了不到两里地天就全黑了,只得在一处山脚宿营。
这个年代可没有路灯、车灯之类的玩意,更别提所谓的官道也是时宽时窄、东扭西拐、坑洼不平的,就算突然冒出来深沟、大坑之类的大杀器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所以这年头除了极特别的情况,比如军队急行、官府拿贼、生了急病之类的,基本没有人敢走夜路,尤其是在有车马的情况下就更加危险了。
众人在路边一块还算平坦的空地上安置好牲口、点起了篝火,安霖又拎起横刀割来大捆的艾蒿驱赶蚊虫,忙活了大半天,可算是安顿下来。
然后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饿,好饿啊!
这一天下来除了早晨算是垫过肚子,然后就是走路、看打仗、被人打、跑路之类的各种高消耗运动,不饿才怪。现在安顿下来,更是饿得叔可忍嫂不可忍了。
“小七,把你的私货交出来吧。”
大家的吃食日用都放在马车上集中保管,自然都被强盗卷跑了,现在哪来的吃食?不过安霖相信据说曾在整座安府里藏满了零食的小七肯定是个例外。
“哦。”
果然,小七有些委屈的答应了一声之后,便在马骡驴身上东掏掏、西翻翻,一大票麦芽糖啦、枣儿杏儿梨子啦、肉脯蜜饯啦都被翻了出来,虽然七零八碎,却也能勉强充饥。
肚子里有了货,人就精神了。苏仲碌马上把在肚子里憋了半天的问题抛了出来。
“安郎君,你到底有多大的力气?”
也是啊,且不说安霖这货把棵两百多斤的大树当暗器抛来扔去的,就说那辆帮众人挡住弩箭的大车少说也有三、四百斤,这家伙说扔就扔出去了。更别提那些盛满泥土的木箱,怎么说也有好几十斤重,人家一扔就是俩,一出手就是三十多步了。
“这个嘛……”
说实话,安霖也不知道他的力气有多大。记得他被小师妹刺杀的时候,近百斤的石桌子让他抡得跟风车似的,然后又跟那个叫孙通的军官打了回架,倒是劈得那货连连后退,可也不知道这把子力气算大算小。
安霖站了起来,走到一棵碗口粗细的树前。他前世看过《水浒传》,里边的鲁提辖倒拔垂杨柳的段子他还记得,鲁智深算是力大的吧?我也倒拔一个试试?
双手倒把住树干,身子紧贴上去,双足一踏、腰间一用力、双臂一环,大吼一声:
“起!”
身后传来一片惊呼。
安霖脸红脖子粗,大树动都没动。
“起呀起!!”
安霖再用力,大树只是晃了晃。
身后观众的评论声传来了。
“郎君加油——”不用问,这是小七。
“这棵树太细,郎君懒得跟它一般见识……”吹牛打屁,这是安寿。
“这棵树没于土中,拔出来少说也要七、八百斤的气力。”理性分析,这是苏仲碌。
“拔出来又如何?不过一莽汉罢了!”这是谁说的?还用问!
——你见过长得这么妩媚……呃,这么英俊的莽汉吗?
安霖怒了,浑忘了刚才还足、腿、腰、臂逐步发力的科学方**,双臂一箍、一声大吼、抡开了膀子——
咔擦一声响,就见树干底部的泥土以肉眼可见间的速度裂开一道道巨大的缝隙。再一声吼,就听“嘭嘭”的闷响不绝,已经被拔得半露出地面的树根被纷纷崩断。再一声吼,安霖已将这棵足有三百多斤的大树高举过顶。最后一声吼,将其抛出数丈之远……
“好神力!”苏仲碌大声喝彩,小七眉开眼笑,安寿更是谀声不绝,小师妹则是痴痴不语。
难道我是属绿巨人的,不发怒就没力气?安霖也有些呆,然后浑身一软,哎呦一声惨叫便跌坐于地:
“完了,刚才白吃饭了,小七,再给我整点!”
……
关中大地的秋天就是这么古怪,白天能热死人,晚上能冻死狗。纵然点了篝火,秋寒露重的也让人难以入眠,小七就叫嚷着明日一定要找家客栈好好洗个热水澡,再买件新衣服。
安霖却一激灵,蹦了起来,叫道:“你们有钱么?”
众人面面相觑,忽然间都动了起来,各自在身上翻翻拣拣。好一阵子之后,大家凑一块一数,好么——
最有钱的是小七:一小串钱,一百一十文。最穷的当然是安霖:身无分文……安寿有七十文,苏仲碌有五十文,小师妹有十二文。五个大活人,浑身上下就二百四十二文钱。
一路走来,衣食住行都是苏仲碌安排,众人自然不用操心这些小事,可如今,却成了要命的大事。
苏仲碌苦着脸叨叨着住店要多少钱、吃饭要多少钱、喂马要多少钱,最后的结论是这点钱再怎么省着花,也就够两三天吃用的。
“咱们要去河东的那个什么地方来着?”安霖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他要去啥地方娶媳妇儿,便去问苏仲碌。
苏仲碌翻了个大白眼。敢情这位大爷连去啥地方都没弄明白,不把他拐卖了真是对不起自己。
他哼哼唧唧的答道:“晋阳。”
“哦对,是晋阳。”安霖毫不难为情,继续说道,“这一路不近吧?怎么也有几百几千里吧?咱们没有钱怎么去?”
苏仲碌被这位毫无常识的家伙搞得很无语,生怕他继续胡说八道下去,赶紧打住道:“贫道可以化缘。”
“化缘?这几百几千里路咱们就一路讨饭过去?我可是要住上房、单间、独立卫生间、洗浴、大床房。吃饭要有鱼有肉有青菜,餐后有汤有水果有甜点,还要几套换洗衣物,要纯棉……呃纯丝的。你再去搞辆马车,骑马太热。我还要……”
安霖这一嚷嚷,小七跟着起哄,安寿跟着助威,就连小师妹也跟着心有戚戚……气得苏仲碌干脆转过身去,决定这辈子都不再理睬这几个傻蛋。
嚷嚷了半天,可谁都知道就凭身上这仨瓜俩枣,要什么都是镜花水月,也就渐渐没了心气。关键还是没钱啊!
“要不咱们拦路抢劫吧!”
安霖沉吟半天,终于想出来一个好主意。
苏仲碌继续不理他,小七没心没肺的表示赞同,安寿不管好恶自然是要赞同郎君的,小师妹可不干了:
“我辈侠义中人,怎能行此腌臜龌龊事?你若敢行不轨,我必治你!”
“我说姐姐,要不我跟你去要饭?啧啧啧!你瞅瞅,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要饭都不用化妆。”
安霖口中啧啧有声,对着小师妹指指点点。确实,小师妹身上的那件青色道袍早就被祸祸得脏污不堪,还被刮扯得丝丝缕缕的,要是再破烂点都能走光了。而她那张原本白皙粉嫩的脸蛋,也早就成了花猫脸。
小师妹大怒,本要张牙舞爪的扑过来,忽然脸色一红又顿住了,转过身去闷不做声。
安霖压根没注意到,眼珠一转,又道:
“那我们不拦路抢劫了,我们去惩善扬恶,劫富济贫吧。”
苏仲碌撇了撇嘴,小七叫着“好啊好啊”,小师妹默不作声。
“好了,就这么定了,睡觉睡觉,明天早起!”安霖怪叫一声,翻个身,抓过小七的小手,呼呼大睡。
第二天一早起来继续赶路。这回可没有小七的私货了,只能饿着肚子走路,可算在中午时分路过一条小溪,众人才得以简单清洗了手脸、装满了水囊。
一路采拾到了零星的野果,却不足以充饥。就在安霖饿得叫嚣着要杀驴、跟小师妹吵得不可开交之时,探路的安寿突然叫了起来,却是前方远远的似有人踪。
安霖催马跃上路旁的小丘,手搭凉棚望去,只见前方一里地左右行来一辆马车,马车前后还有七八个人随行。
“打劫啦!打劫啦!”
安霖顿时兴奋起来,肚子似乎也没那么饿了。他打马冲下小丘,招呼过来苏仲碌和小师妹两大高手,就要奔向他的鱼肉青菜加餐后水果,还有大床房……
“站住!不是说好了不抢劫的吗?”小师妹犹豫了一下,还是拦住了安霖。
“那咱们去惩恶扬善”安霖道。
“你如何知道那些人是恶是善?”小师妹毫不退让。
“那些家伙看上去就很恶嘛!”安霖满嘴胡诌着,那些人恶不恶他不知道,他就知道自己很饿……
“如何证明?”
“你真的要证明?”
安霖有些无奈,瞅了瞅目光不再那么坚定的小师妹,又拽过小七,在两人的耳朵边上嘁嘁喳喳了半天,然后就见小七雀跃欢呼,小师妹的脸色则是阴晴不定。
……
郑大彪,韩城县河阳镇人,是镇里有数的富户,家有良田数百亩,商铺作坊数间,奴仆雇工近百人。郑大彪有很多诨号,比如说“郑胖子”、“郑二升”、“郑大斗”、“郑八女”、“郑大善人”等等。“郑大胖子”是形容他的体型——身长不过五尺三寸(不到一米六),体重却有一百五十斤上下(隋斤,约等于现在的200斤),简直就是一座小型肉山,不过这里边也有郑大彪自己的无奈。在这个温饱仍困扰着绝大多数生民的年代,肥胖几乎就是财富乃至权力的象征(参见某国三胖),尤其对郑大彪这样的土财主来说,发了财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撑圆肚皮。叫他“郑胖子”跟叫他“郑财主”几乎就没区别,没看河阳镇首富的诨号叫“孙大胖子”吗?诨号比他多了个“大”字,体形自然比他大上一圈,财富也是多出一筹。
这“郑二升”和“郑大斗”其实是一回事。隋文帝开皇年间,改古斗三升为一升,而民间大户的田租大都仍按旧例收取每亩三升,导致佃户的负担陡增三倍。郑大彪在河阳镇是个外来户,又是新晋富户,为了吸引佃户,就定下了田租每亩二升,果然不愁没人上门来给他种地,却惹恼了当地的其他大户,联手官府要收拾他。吓得郑大彪赶紧用大斗收租,这样收上来的租子也就跟其他大户的差不多了,于是就得了这两个诨名,也成了当地的一个小小的笑料。
至于这“郑八女”说的倒是两回事。一是说这厮好色如命,有妾室十好几个。虽然官府规定“庶人一夫一妇”,严禁平民纳妾,可实际上谁管得着?你说郑大彪纳妾,人家郑大彪说那不是妾,是婢女,反正妾与奴婢在身份地位上本来也没啥区别。再说世风如此,但凡手里有俩闲钱的,少有不纳妾的,官府也是睁一眼闭一眼,除非是要找茬收拾你。
不过郑大彪的女人也着实多了些。什么青楼的红牌、插标的流女、漂亮的寡妇、还有交不上租拿来抵债的佃户女儿,只要他看上眼的基本都跑不掉。他的妾室早就不止八个,之所以叫他“八女”说的是他连生了八个闺女,就是没一个儿子。郑大彪一个外来户,钱财在当地人看来有些来路不明,自然观感风评不咋地,叫他“八女”不免包含着羡慕嫉妒恨等各种情绪,咒他生不出儿子。
“郑大善人”是郑大彪唯一喜欢的诨号。这个诨号的来历是三年前河阳水患,官府号召大户赈灾。本来这种事,大户们也就是意思一下,给官府一个面子,毕竟大户的钱财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可郑大彪当时与一位王财主有隙,不知怎么的就斗起富来,脑子一热生生扔出了两年的收入捐给官府,方才吓退了王财主。虽然事后醒过神来的郑大彪心疼得足足几天吃不下饭,活活瘦了两圈,却也从县尊手里请回了一面“河阳首善”的牌匾和“郑大善人”的美名,让他感觉稍有安慰。随着日子久了,叫他“郑大善人”的渐渐少了,他却越发的喜爱这个名号。凡是有求于他的,不好好叫几声“大善人”,什么事也甭想办成。
从郑大彪的这几个诨号也能看出,他不过是没什么大善、也没什么大恶的普通土财主一个。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毕竟这个世上,纯粹的善与恶都是极少数,绝大数人都跟郑大彪没什么两样。
不过郑大彪现在却是很恼火。他的第十七房小妾,本是离河阳四十里外陈家村一个猎户家的女儿,两个月前去河阳售卖山货被郑大彪看上,花了整整二十贯礼钱才纳进门来。这个小妾虽然是个山姑出身,长得却可他心意,尤其是在大山里狩猎锤炼出来的长腿蜂腰,简直爱煞了他,不顾暑热体肥一身臭汗,整日与她在房内耍乐。谁想半个月前这个小妞说家里老父病重要去探望,结果一走再无踪影。郑大彪一等再等,等得欲丨火中烧,又隐约感觉自己上了当受了骗,于是叫上几个护院家奴,匆匆赶去陈家村兴师问罪。
这关中大地自打入了秋就没怎么下过雨,热得让人没处躲没处藏的,普通人尚且受不了,更何况郑大彪这个大胖子?一路上燥热不堪的郑大彪对家奴们连声叱骂不绝,马车赶得快了他骂,赶得慢了他还骂,身边给他打扇子的小婢女更是被他骂得啼哭不止,仍是污言秽语不绝于耳。
突然间,郑大彪的骂声消失了,家奴们都觉得很不适应,有些面面相觑,继而四下张望起来。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让郑大彪闭嘴的原因——路边站立着一大一小两个美丽的小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