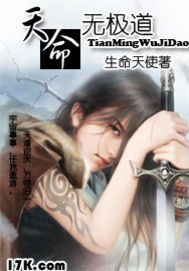词曰:
未知君在哪处修仙,渠会是何年?恨东风欺梦,霜华染鬓,孤枕惊寒。镜里朱颜见老,槛外落花残。昨夜星辰落,露浥危栏。
只雁南风北雨,寂寞沙洲冷,来去阳关。万里横烟浪,千载记人间。问金樽,谁斟谁劝;想醉来,怎慰怎相搀?空回首,悠悠流水,渺渺云天。
——小词调寄《八声甘州》。
当时那鹿明觉得为难,自己不好插嘴,想等陆三丫抱怨完了,再为自己所在的西灵仙山黄山主、郎副山主,以及自己几个作点儿辩解。
谁知陆三丫说着,圣姑听着,渐渐地,圣姑的脸色变冷了,表情严肃了!看着这一幕,鹿明心里可就紧张起来了!
鹿明不由得心底暗念:阿弥陀佛!陆姑奶奶,我们西灵仙山也没把你怎么滴呀,你不带这么任性损人的吧?照你那么说,这一场误会,全是我们西灵仙山的错喽?
仿佛心到神知一般,鹿明心底念佛之际,陆三丫住了口。翠姑道:“三丫,你想见小棒儿,他现在不在这里,待会儿你跟我去东跨院吧,我有话跟你说。”
陆三丫点头“嗯”了一声。
那鹿明觉得逮着了机会,赶紧施礼道:“阿弥陀佛,圣姑您老人家不能光听陆道友的一面之词啊,我们西灵仙山跟陆道友发生冲突,起了误会,这事儿的经过是这么样这么样的……”
翠姑含笑向鹿明道:“好了,不须多说,我自然知道该怎么做的;只是眼下得赶紧通知你们的黄山主,不可为难李诗剑和他的妻子——
只是明宗对我们禅宗颇为抵触,特别是近几年来,似乎是在酝酿着什么大的图谋,你们过玄木关,虽是用计闯了过来,但是你们回西灵仙山时,终究还是要走人家玄木关通过的,这可就有些麻烦了!”
传灯子道:“阿弥陀佛!师母,待我走一趟,护送鹿居士等人过玄木关。”
“方丈,你是我们这一界的禅宗领袖,你一出面,必然就会引得明宗宗主广明子坐不住的,那时事态扩大,反为不美。目前我们是不能跟明宗撕破脸皮的——还是由我出面,送他们过玄木关为好!”
传灯子念了一声佛:“阿弥陀佛!师母说得是,此事还真得劳动师母了!”
翠姑道:“方丈既然同意,那么事情就这么定了。你先安排鹿居士他们休息,我回东跨院去,跟三丫说点儿事情。”
此时的陆三丫,一肚子的话想问翠姑,为什么小棒儿不在这里?他人到底去哪里了?然而却又碍于情势不好紧紧追问,正满心疑问和期待,听得翠姑说回东跨院去说话,恨不得拔腿风遁而去!
当时翠姑又道:“三丫,我们走吧。”
说话之际,翠姑站起身来,禅堂众僧有尊称曰“师太奶奶”的,也有称“师祖母”的,有喊“师母”的,也有恭恭敬敬地呼曰“圣姑老人家”的,都纷纷离座躬送。
陆三丫则是紧跟着翠姑出了禅堂,犹自回首怒目,瞪了鹿明等人一眼,瞪得鹿明等一男四女心中发毛。
却说陆三丫随翠姑去了禅宗圣姑独居的东跨院,这院子是另开大门,跟这边缁衣寺隔开;前文交待过,这院子是个单独小院,三间正殿两下厢房,穿堂正门处另有侧室里间,当初正是小棒儿居住之处。
陆三丫跟随翠姑到了这边小院里,才进了穿堂正门,翠姑便指着侧室里间道:“三丫,半年前,小棒儿他就住在这里。”
陆三丫听了,忍不住推门进来瞅上一眼,但见房间不大,室仅一丈见方,可容一人居住,而所见唯有一具石床,床正中放着一具蒲团,干干净净,此外还有一张桌子而已。
陆三丫情知这都是小棒儿所用之物,睹物不免思人,眼中自是含泪。
翠姑安慰道:“阿弥陀佛!三丫,小棒儿他跟随玄根子大师去了明离世界,必有机缘,你也不必难过——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你们必有夫妻相见的一天!”
陆三丫此时再也不作掩饰,而是纵情任性地放任两泪滑落,哽咽道:“话是这么说,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说到这里,泪光中,陆三丫抬起头来,望定翠姑,问道:“师叔,那玄根子为何要带小棒儿去明离世界?”
哪知翠姑听了这句话,却是脸色一红,答道:“你先跟我来正殿禅堂里坐,我跟你慢慢分说。”
陆三丫却是心中一突:师叔她脸红什么?莫非真的如那木元子话里暗示的,小棒儿他跟翠姑有苟且之事?
陆三丫当时只觉得一阵子心慌意乱,头大,却也自拭今宵泪,跟翠姑往正殿里来。
到了正殿,也就是那北面三间正房,迎面是三尊大佛像,旁边则是罗列着许多诸菩萨像,佛前海灯,不知用什么油,日夜不熄,也不见少。
翠姑与陆三丫两个是面对面,就两具蒲团上盘膝趺坐,翠姑的声音幽幽地在空气里响:
“——三丫,你不知道,当初我和小棒儿一路寻找缁衣寺,恰恰在西灵仙山下遇到了那山下村祭神巴天龙……”
说到这里,翠姑脸上又是一红,遂继续说道:“后来到了山上,他们都说我是禅宗圣姑,那山主黄啸亲自送我来缁衣寺。
路上也曾经过玄木关,那关主木元子也曾阻拦过,只是听说了我的禅宗圣姑身份之后,便立即放行。到了这里,缁衣寺方丈传灯子口口声声尊称我“师母”,我也问了他,怎么这样称呼我呢?”
陆三丫接过话来道:“师叔,莫非你不曾跟那个老老和尚结过婚么?”
“什么老老和尚?结什么婚?”
陆三丫道:“方丈那个年纪,分明是个老和尚,他的师父,那必然就是个老老和尚喽,师叔你没跟那个老老和尚结过婚,那方丈老和尚怎么会尊称你为师母呐?”
翠姑红了脸道:“瞎说,哪有那么一个老老和尚?传灯子倒是有个师父,你可知道他师父是哪个?”
陆三丫摇头。
翠姑笑道:“他师父,就是那个无根大师。”
陆三丫惊讶道:“那无根大师早就在那乾元寺里圆寂了么?”
“是啊,从那莫雨手中救了我和小棒儿,并送我们来到这边,耗尽了仙家真元灵力,早已圆寂了,只是他圆寂之前,用灌顶大法,将修为封藏在小棒儿丹田之内,要成就小棒儿,并赠送我一颗珠子——哎,就因为这颗珠子,那传灯子才会口口声声称我为师母的,可不是羞死人了么?!”
“是什么珠子?”陆三丫不解地问道。
翠姑红了脸解释道:“据说这珠子是无根大师亲手炼制给他的心上人的,叫做定情珠,能护主呢。”
“师叔,你是说,那传灯子方丈就因为这颗珠子就认你做了师母?”
“是啊。可是我到这边不久,就遇到了麻烦——”
翠姑话未说完,陆三丫已经忍不住问道:“师叔,什么麻烦?”
“哎,传灯子有四个乖徒弟,延公、延平、延恩、延义,大徒弟法号延公,渡劫失败,身死道消了,他那个二徒弟,叫做延平的,给我添了不少堵!”
“师叔,那延平和尚敢给你添堵,我打他去!”
翠姑笑道:“延平和尚修为境界,半年前就达到了仙道五阶了,我都未必能打得过他呢,况且他如今也不在缁衣寺,你想打他也打不着的。”
陆三丫听了,不由得问道:“他这么厉害,可是上面不是有他师父传灯子管着么?”
翠姑又红了脸道:“传灯子死了大弟子,因而对剩下的三个弟子更是上心,特别是这个延平和尚;而且,这个事情,最初我也不想让外人知道,所以,传灯子先是不知情,后来倒也狠狠地罚过他面壁。”
陆三丫此时心情早已平复,她虽是个粗枝大叶的人,但那是习性,并不是智商低,此时不由得又一次联想到了那木元子的话,不由得脱口而出:“师叔,是不是那延平和尚对你……?”
虽然陆三丫没有明说,点未到而止,但是翠姑本就是个极明白的人,闻言也不由得吃惊道:“三丫,你才到这边,竟是从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
陆三丫也不隐瞒,将过玄木关时所听那木元子所说的话,一五一十地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翠姑也听明白了:敢情先前在那缁衣寺禅堂之中,这些话,陆三丫当时碍于人多,没有跟自己说。
当时听了陆三丫的话,翠姑是红了面皮,怒道:“阿弥陀佛!明宗的顽固派们都是故意造谣!哼,造谣归造谣,难不成他们还真敢无视我禅宗圣姑的身份么?”
说到这里,看到陆三丫似疑非疑的模样,翠姑当即对陆三丫道:
“三丫,别信那些谣言!你不知道,作为修仙者,传灯子对于本宗弟子寻找道侣的事情并不禁止的,那延平和尚若是向别人求爱,传灯子也不会处罚他的,然而他居然向我求爱!
起初我倒是想着,爱不爱我是他的事情,接爱不接受是我的事情,爱本身也不是什么罪过,所以呢,我就当作听到蚊子哼一般,又如风过耳,随他去呗,终有一天,他自会醒悟的。
不曾想,延平和尚竟是不知进退,因此惹恼了小棒儿,他两个不知什么时候打了一架,明里都不给我知道,暗中却是两个较起劲儿来了,结果是两个人比拼修炼,修为境界一个比一个提升得快!
唉!延平和尚不知好歹,把小棒儿视为眼中钉,小棒儿呢,也是十分厌恶那延平和尚,直到后来,大约是一年前罢,终于有风言风语传到了我耳朵里,也传到了传灯子耳朵里了!
传灯子狠狠地训斥处罚了延平和尚,那时我才知道,小棒儿跟延平和尚已经结成了仇人!”
“师叔,小棒儿跟可恶的延平和尚结了仇,莫非小棒儿他也是吃醋……”
“三丫,别瞎胡想。小棒儿哪里会是因为吃醋啊?他不是有你了么!他是看不惯那延平和尚扰乱我清修,替我抱打不平的。
那时候,他也不想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也不想告诉传灯子,后来事情闹了出来,小棒儿才跟我说了:
‘师叔,这个延平和尚虽是自作多情,我怕的是这个事儿一旦传出去了,会影响你的清誉。’”
陆三丫道:“嗯哪,师叔,我就知道,我们家小棒儿遭过罪吃过苦,心好,体贴人。”
翠姑道:“可不正是么。那时我和传灯子商量过,传灯子也舍不得灭了延平和尚,我也不想因此让传灯子处死他的心爱弟子。恰恰半年前来了一个玄根子大师,于是综合考虑之下,传灯子就让那玄根子大师把他们两个都带去明离世界那边了。”
“带去那边,他们两个在一起,不还是矛盾没解决吗?带走那延平和尚倒好理解,干吗把我们家小棒儿也带过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