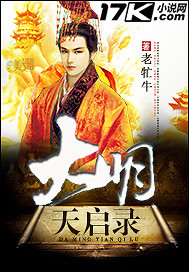不过数日之内,通州、遵化、密云守军相继在守将率领下归顺燕军。
奉旨统帅五万大军,驻守开平卫所的都督宋忠闻燕王叛逆之事后匆匆率领军马前来,意欲进驻居庸关遏制燕军,半道中获悉居庸关失守,忙即率军前往怀来。
十数日后,燕王朱棣留朱能,张信率一万士卒守卫北平,亲领大军攻克怀来,蓟州,杀都督宋忠,都指挥彭聚,孙泰,指挥马宣,收降四人麾下大半兵马,永平卫所指挥使郭亮率军投诚。至此,燕军总数已然接近十万之众。
奉天殿之上,身穿五爪金龙袍的建文皇帝朱允炆面色铁青,扫视殿中一众文官武将,默不作声。
一个身穿大红色官服,白发苍苍,年过六旬的老者在殿门宦官宣召下缓步走上殿来,叩首道:“微臣耿炳文参见陛下。”此人正是昔年追随洪武皇帝征战四方,后在鄱阳湖大战之时率军遏制张士诚,避免了朱元璋率军迎战陈友谅大军时腹背受敌,封爵长兴候,早已赋闲在家养老,被皇帝降旨急诏而来的耿炳文。
朱允炆眼见耿炳文虽则年岁老迈,言语之际声若洪钟,颇显老当益壮之态,心中略安。他得兵部尚书齐泰举荐此老之时,心中略微担心这个在大明开国武将中资历深厚的耿炳文老迈昏庸,不堪重用,此时眼见对方上殿之际步履沉稳,当即降旨,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督甯忠为左、右副将军,帅师讨燕。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耿瓛,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友、陈晖、平安,分道并进。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侍郎暴昭掌司事。
兵部尚书齐泰看了看殿中一众伏到在地接旨的武将文臣,心中微微叹息,暗自忖道:昔日先皇滥杀之下使得本朝无将可用,若是昔日蓝玉,傅有德,冯胜任一人在世,朱棣便是三头六臂,也难逃败亡,今时今日唯有期盼耿炳文有廉颇之勇,旗开得胜了。
“诸位爱卿乃军中宿将,望戮力征战,剿灭叛逆,勿使朕背负弑叔之名。”端坐高处的建文皇帝朱允炆冷冷说道。
一众跪倒接旨的武将闻听皇帝陛下如此颇显矛盾的言语,不禁有些面面相觑,不知该当如何作答。
耿炳文赋闲在家久矣,与这位登基不久的皇帝陛下可谓素未谋面,抬头之际眼见朱允炆面颊寒霜,不敢违拗下只得勉为其难的道:“微臣耿炳文谨遵陛下旨意。”
约莫一个时辰后,兵部尚书官衙大堂之内,今日奉诏剿灭朱棣的一众文官武将各分两列而坐,静静注视着高踞桌案后的兵部尚书齐泰。原来大军出征非是儿戏,一应粮草军械调集皆须谋划,而这些便要身为兵部首脑的齐泰统筹安排。
齐泰眼见诸人已然到齐,皱着眉头问道:“各位心中对于陛下言及弑叔之事可是心存疑虑?”
安陆侯吴杰方才在殿上接旨之时,便是老大气闷,此时忍不住站起身来瓮声瓮气接道:“两军交战之时刀剑无眼,谁认得什么王爷叔叔?两军阵前,唯有王师和叛逆之分。陛下如此下旨,岂非让我等自缚手脚?”一众武将方才在奉天殿接旨之时,碍于天威难测下默不作声,此时给吴杰这么一撩拨登时觉得皇帝陛下这般旨意过于荒诞不经,纷纷起身响应,将个兵部大堂吵得不可开交。
齐泰扫视众将一眼,眼见堂上除了老成持重的长兴候耿炳文皱着眉头默不作声外,唯有一个年约三旬有余的武将面带微笑下自斟自饮,心中不禁微微一动,挥手让一众武将落座,转头问道:“盛将军好似全不在意此事一般?”原来这个在众将吵嚷不休时依旧好整以暇的汉子,便是昔日追随蓝玉在捕鱼儿海侧扫灭金帐元军,生擒鞑虏悍将王保保的嫡亲弟弟,北元权臣脱因帖木儿,后在蓝玉保举下升任都指挥使的盛庸。
盛庸方才在奉天殿上眼见皇帝陛下言语神态,早知他对燕王朱棣恨之入骨,闻听其言及什么众将率军平叛,不可使得他身负弑叔之名时,心中略一思忖下早已透彻无比,故此方才闻听齐泰言语也就无动于衷,此时闻得兵部尚书大人言及自己,登时省悟过来方才失态之举,忙不迭站起身来抱拳躬身说道:“末将无礼之处,还望尚书大人海涵。”说到这里,又团团作揖向一众资历远远高于自己的侯爷们告了个罪,沉声接道:“以末将看来,陛下此言另有深意。”
齐泰闻言目光一闪,心中暗自忖道:军中武将多是耿介性子,这个盛庸倒有这般慎密性子,实为难得。难怪以昔日蓝玉那般素来眼高于顶的桀骜不驯,对此人也是颇为看重。他昨夜给皇帝召到御书房商议剿灭朱棣之事,心中对于皇帝的意思自然是一清二楚。
耿炳文昔年追随洪武皇帝朱元璋扫灭群雄,阅历丰富,此时闻得盛庸这般言语,心中微微一动,情不自禁转头问道:“以你之见,陛下言下之意是个什么意思?”
“兵凶战危,两军阵前刀剑无眼,末将等马革裹尸尚不过平常事,何来能力反倒让燕逆朱棣得保平安?”盛庸娓娓言道。
齐泰闻言颔首,沉声接道:“讨逆有功,杀贼岂能有罪?若是哪位将军将燕逆朱棣生擒活捉,献俘于奉天殿上,文武百官之前,反倒让陛下念及亲情,左右为难了。”
到得此时,一众将校便是脑筋再不开窍之辈,也听懂了兵部尚书大人的意思,更知晓了皇帝陛下说什么“勿使朕身负弑叔之名”的言下之意,心中疑虑尽去下纷纷躬身抱拳领命。
长兴候耿炳文心中微微苦笑,暗自腹诽道:也就是这些腐儒们教出来的皇帝陛下,肚中才生得这般转弯抹角十八拐的肠子。明明便是让我们不要手下留情,最好让朱棣死于乱军之中,偏生说得这般冠冕堂皇。
朱瑛粉嘟嘟的脸蛋被朱权的胡须刺得生疼,心中恼怒下扬起小拳头在其父宽阔结实的胸口上狠狠砸击两下,挣扎不脱下反倒惹得朱权呵呵大笑。
徐瑛眼见夫君刚一归家便即这般为老不尊的欺负女儿,心中不禁又是好气又是好笑,疾步而来夺走女儿,牢牢抱在怀中嗔怪道:“身为人父,整日这般捉弄女儿,哪里还似一个堂堂王爷。”言语之间虽则颇有嗔怪之意,心中却是颇为喜悦。原来自从冯萱诞下朱汉民后,她内心之中颇有隐忧,此时眼见朱权全然没有重男轻女之念,对于儿子女儿向来一视同仁,倒是放下了老大心事,伸手轻拍爱女背脊之际轻轻叹道:“皇帝陛下将朱棣的三个儿子放还北平,看来倒也未必存了个赶尽杀绝的打算,只可惜此举无异于纵虎归山。”
朱权闻听此言,心中不禁微微叹息忖道:朱老四绝不是个肯坐以待毙之人,便是朱允炆不放他三个儿子,他便会引颈受戮么?自从周王朱橚被贬为庶人,只怕他已然难免背水一战,死中求活了。心中虽则这般想,不知何故,却没有宣之于口。
荆鲲坐于亭下,细细看过自北平传来的朱棣奉天靖难的檄文后,面上流露出几许讥诮之色,轻轻叹息着说道:“道衍秃驴这篇顾左右而言他,所谓奉天靖难,诛灭奸佞的檄文,倒是抵得过数万雄兵。”
朱权回想今日自北平传来的消息,皱着眉头说道:“朱老四目下手中兵马虽则不下十来万,毕竟不过一隅之地,想要以弱胜强,只怕非是易事。”
“以目下殿下手中兵马,即便前往北平与朱棣合兵一处,彼强我弱之下难免徒作他人嫁衣,唯有厉兵秣马,静观其变。”荆鲲转头看了看朱权,沉声说道。
朱权沉吟片刻后颔首说道:“若是朱老四损兵折将,本王即刻率军前往北平。”此时此刻他早已心知肚明,目下的建文皇帝朱允炆削藩之举,意在一举铲除所有藩王,目下虽则唯有朱棣兴兵造反,但自己身为率军藩王,同样会被皇帝和一众文臣视若眼中钉,肉中刺一般,必欲除之而后快,绝难在这场靖难之役中置身事外了。
正在此时,马三保疾步而来,躬身禀道:“启禀殿下,方才得城外巡哨军马回报,钦差李公公一行自山东登州坐船跨海而来,此刻怕是已然入城。”
朱权闻言不禁皱起了眉头,略一沉吟下苦笑道:“皇帝陛下不会还天真到以为一道诏书,便能让本王率领麾下军马进攻北平,和朝廷大军前后夹击朱老四吧。”说到此处,便即低声吩咐马三保几句,转身朝自己的卧房而去
约莫半个时辰之后,一个满面风尘,尽显疲态,年约三旬的宦官在二十个御前侍卫的簇拥下迈步踏入了大宁城中的宁王府。
他乃是千里迢迢传旨的钦差,昂然率众步入宽敞的客厅之后吩咐摆设香案,冷冷喝道:“咱家奉旨而来,便请宁王殿下前来接旨吧。”
片刻之后,身穿华服的徐瑛缓步而出,面露戚容言道:“王爷他偶然风寒,已然卧病在床半月有余,实在起不得身来,公公不妨到卧房宣旨。”
李公公闻言登时不悦,语含讥讽的冷冷说道:“殿下该不会也是神志不清了吧?陛下亲笔旨意在此,如何可以这般藐视?”原来身为臣子便是病得再重,只要尚有一口气在,也须得跪伏于香案一侧接旨,岂有这般要钦差卧房宣旨的无礼之事?徐瑛这般说实在是岂有此理。
徐瑛自幼习武,加之身为宁王妃久矣,闻言丝毫不见慌乱,一双大眼扫视钦差和一众御前侍卫,轻声说道:“先帝昔日曾有严令宦官不得干政,哀家是否藐视圣旨,却还轮不到公公说三道四。”
李公公眼见徐瑛目光扫过,心中微微泛起一股惧意,无可奈何下便即带着手捧圣旨的小宦官尾随徐瑛而去。
刚一步入朱权的卧房,冲鼻而来的尽是一股药味,锦帐流苏下的卧床上仰卧一人,双目紧闭下似乎昏睡不醒,不是朱权却又是谁。
徐瑛面露忧色,伸手接过丫鬟手中的热毛巾,给朱权擦拭面庞,低声说道:“夫君醒来,钦差李公公前来传旨。”虽则嫁于朱权日久,但今日当着素不相识之人这般轻唤“夫君”二字,还是忍不住涌起一股羞意。连唤数声下眼见朱权依旧高卧,双目紧闭下嘴角噙着一丝淡淡的笑意,心知他是故意捉弄自己,伸手轻推之下悄然拧了他胳膊一下。
朱权吃疼之下强忍着没有叫出声来,双目豁然睁开之下却无法再行装睡,连连咳嗽数声后缓缓转头,故作气若游丝之声问道:“目下什么时候了?爱妃。”
徐瑛眼见朱权故作三魂倒似去了两魄一般病态,强忍笑意,柔声说道:“陛下有旨意自应天而来,夫君还不起身接旨?”
朱权缓缓转头之际看了看不远处的李公公,强自撑持两下之后终于无力起身,摔回床上,口中哀道:“本王这身子骨怕是不成了……”话未说完又是一阵咳嗽。
李公公看这夫妻二人双簧戏演得似模似样,心中狐疑下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接过身侧小宦官手中黄绫圣旨草草宣旨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宁王朱权即刻返回京师面君,不得迁延。”
朱权听圣旨虽则不是命令自己统帅军马前去对付朱老四,却是命自己即刻返回应天,心中不禁冷笑,暗自忖道:真不知晓皇帝以及一干腐儒脑子中究竟在想些什么,还妄想仅凭一道旨意便让我千里迢迢的赶回去送死么?
徐瑛一面以手中丝巾“拭泪”,一面自床沿站起身来,转头对李公公轻声说道:“王爷他病成这般模样,若是千里奔波,只怕非得送了性命不可。陛下虽有旨意在此,你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