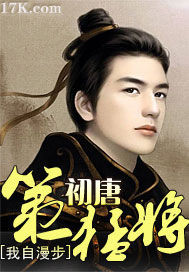御书房中,朱元璋默然不语的扫视着老老实实站在不远处的朱棣,朱权二人,心中也甚是烦乱,所为并非只是为了朱权二人就藩之事,所引来的一众文臣激烈反对,还因为他的内心之中也隐约觉得黄子澄,方孝孺等所言未尝没有一些道理。
“你二人就藩之前,尚有一件大事须得了断。”说到这里,朱元璋在书桌后缓缓落座,看了看一副耳提面命之状的朱权二人,目光闪烁着沉声接道:“你二人也老大不小,就藩之前,朕就会为你们各自择一个贤良淑德的勋戚之女完婚。”
朱权闻得此言,回想起徐瑛的娇嗔模样,不禁喜动颜色。
朱棣倒还颇为沉得住气,躬身道:“儿臣婚姻大事,自然尊奉父皇一言而决。”
朱元璋眼见朱权一副喜色,鼻中不禁轻轻哼了一声,沉声说道:“徐达家中不是有一女名为徐瑛么?棣儿,便由父皇做主将她娶了给你做王妃吧。”
朱权犹如给当头浇了一桶冷水,脑中不禁一片空白。
朱棣闻言心中也是大震,心中苦笑下却没有一丝高兴之意,他虽也颇喜徐瑛却素知她和朱权情投意合,父皇这般安排当真……
朱元璋看了看双拳紧握,身形气得有些微微发抖,却依旧默不作声的朱权,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听闻信国公汤和膝下也有一小女,就许给权儿做王妃即可。”他乃是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让臣下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为王妃,乃是一种殊荣,自然无需征询任何人的意见。通过锦衣卫密报,他自然知晓徐瑛和朱权过从甚密,显见得情投意合。让朱权成为大明军权最重的戍边王爷,却要将他心爱的女子嫁给朱棣。这根扎进心头的刺会让这小子怨恨自己,但他更会恨朱棣一生一世,永远不能和朱棣联手成为朱标的威胁。为了不让任何人威胁到他日执掌这个帝国的朱标,不论是朱棣,朱权也好,徐瑛也罢,都只能成为大明帝国这张棋盘上的棋子。
朱权心中愤懑难当,但毕竟曾经历过千军万马的浴血厮杀,心中犹自保有一分清醒,他是太明白面前的朱元璋那种乾罡独断的决绝性子了,目下自己纵然反抗也是徒劳无力,反抗也须得走出皇宫再说,当下强自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低声说道:“微臣遵命。”说着话,嘴里满是苦涩,脑海中似乎有另外一人嘶声怒吼:强烈谴责封建包办婚姻。
回到王府,朱权吩咐景骏,司马超去请师父秦卓峰和荆鲲前来相见。
景骏,司马超二人对望一眼后,连忙领命而去。殿下今日出宫之后,脸黑得乌云密布,显见得是在宫中遇到了极为棘手之事,二人也不敢多问。
待得听完朱权所述,荆鲲不禁皱起了眉头,默然不语。
秦卓峰手中把玩着酒葫芦,眼中神光闪烁下沉声问道:“你意如何?”
“我的意思是是趁圣旨未下,今夜就拜堂成亲,把生米做成熟饭。”朱权看了看窗外已然过午的天色,嘴里咬牙切齿,一字一顿,恶狠狠的说道。心里也是暗自忖道:大不了明天被拉去砍头,老子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想到这里,转头问马三保道:“府中银子可还办得喜事?”
马三保微笑道:“前两日小人才去宗人府领得两千两纹银。”
荆鲲和朱权相处日久,自然明白他也是一经决断,马都拉不回的倔强性子,也就轻叹一声,没有说话。再说他深知秦卓峰的性子,此时若是出面反对,只怕老友非得和自己当场绝交不可。
朱权闻言不禁甚喜,点头道:“事急从权,也顾不得许多了。你等三人,即刻出府采买所需物事。”
秦卓峰眼见马三保躬身领命后转身便要离开,忙道:“且慢,这婚姻大事也非儿戏,好歹得有个章法。”言罢站起身来沉声说道:“徐达兄弟身故后,为师倒是可代父母之命,可这媒妁之言须得思量找个身份合适的人才可。”
朱权也是病急乱投医,对当世的婚姻礼法不甚了然,闻言笑道:“老师权且当个媒人便是。”说罢转头看了看荆鲲。
“不可,这成亲岂可皆成了咱们自己人自说自话?最好找一个声名显赫的勋戚重臣做媒最好。”秦卓峰笑骂道,他向来视徐瑛犹如亲生爱女一般,纵然是平日里不拘小节,视繁文缛节为无物,可处理爱徒的这般婚姻大事,终究还是不能对世人尽皆讲究的明媒正娶免俗。
朱权面露难色的思忖片刻后陡然开颜,转头对马三保笑道:“你即刻前往曹国公府,就说本王有事和他商议,切不可说及成亲之事。”
马三保闻言颔首,心领神会的转身离去。
随着一阵马蹄得得之声,一个轻袍华服的青年带着几个府中随从来到宁王府大门外,翻身下马通禀后在王府下人的引领下缓步朝客厅而来,正是目下的曹国公李景隆。
李景隆落座后接过丫鬟奉上的茶盏,一面浅酌一面忍不住心中有些微微奇怪。他隐然便是这应天城中勋贵子弟之首,平日里最喜宴饮郊游之类的乐事,只是对于今日午后这般时分,宁王方才相邀不禁有些纳闷。耳中听得一阵脚步之声,抬头见得朱权和秦卓峰来到,忙自站起身来见礼道:“下官李景隆参见殿下。”
朱权和李景隆相识已久,心中暗自忖道:若是将做媒之事合盘托出,只怕再借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做这个媒人,还是骗上贼船的为妙。主意打定后便即淡淡笑道:“今夜本王在府中宴饮,想请应天城中一应勋贵子弟前来府中。因此便想劳烦曹国公亲自上门邀约诸位贵客。”
李景隆闻言不禁一怔,暗自思虑道:殿下不日就要就藩大宁,目下在朝中可谓炙手可热,一个帖子发将出去,如我等这般世家子弟岂不个个欣喜?却要我上门亲自邀约?这却是唱的哪一出?
朱权眼见对方眼中略微露出狐疑之色,不禁笑道:“曹国公在应天城中交游广阔,代本王邀客方才不会遗漏贵客。”
李景隆闻言不禁豁然明了,暗自思忖道:目下我大明的武将勋爵乃是世袭罔替,看来殿下此举却是想在就藩之前和应天城中的一众世家子弟多多亲近。想到这里,不禁暗自赞叹宁王殿下深谋远虑。
秦卓峰笑道:“老夫正待前往中山王府。便与曹国公李景隆结伴同行如何?”
原来当世的婚姻礼法甚是考究繁琐讲究,尚需依据周礼中的六个步骤,即纳采(送礼求婚,即媒人提亲)、问名(问女方之姓名及生日时辰,以卜吉兆,今称“合八字”)、纳吉(男家卜得吉兆后,办礼通知女家,婚姻初定)、纳征(向女方送聘礼)、请期(议定婚期)、亲迎(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其中只有“亲迎”为嫁娶当日的仪礼,其余五礼则为婚前仪礼。今日朱权仓促行事,须得在半日之内走完这些诸多礼仪自不可能,但纳采却是不可或缺,须得让这个至今蒙在鼓里的媒人李景隆亲自出面走一趟徐府方可。
李景隆自然知晓秦卓峰乃是朱权,徐瑛二人的师傅,闻言也丝毫不疑有他。他虽则素来和目下的魏国公徐辉祖不对路,却明白目下要说应天城里的世家子弟,自然是以继承徐达魏国公身份的嫡子徐辉祖为首,自己前去邀客,自然也须得先往中山王府一行。
秦淮河畔,夫子庙附近,徐达的府邸客厅之中,徐辉祖肃客奉茶后落座,看了看秦卓峰又看了看不远处的李景隆,淡淡说道:“在下和宁王殿下素无交往,至于宴饮一事,却是俗务缠身,无暇前往。”他和朝中一班文臣一般无二,深深以为皇帝陛下所采用的分藩之事对大明江山社稷有百害而无一利,更对李景隆这般膏粱子弟没有一丝好感,只因目下自己乃是一家之主,却不可失了礼数,只得婉言谢绝。
“别的酒宴倒也罢了,今夜的酒宴你却是非喝不可。”秦卓峰一面说着话,一面站起身来走到客厅门口,挥手吩咐侯在外面的马三保等人将一众聘礼搬进厅中。他自徐瑛幼时就教授其武功,对徐达府中一众人等甚为熟悉,却历来不喜徐辉祖那一副少年老成,说话老气横秋之状。
眼见马三保指挥着几个手下将一个个红绸覆盖的箱子搬将进来,徐辉祖不禁目瞪口呆,李景隆也是一头雾水,浑然不知马三保等人采买一众聘礼后便即悄悄等候在徐府之外,待得自己前脚入府,后脚便在秦卓峰的安排下将一众聘礼抬了进来。
徐辉祖指了指这些聘礼皱眉问道:“不知前辈这却是何意?”他虽则隐然自这些箱子的包裹独特之处看出似乎是提亲的聘礼,却因此事太过突兀,犹自没有回过神来。虽则闻得秦卓峰语气不善,内心颇为不悦,却碍于其身为自己姐姐徐瑛授业恩师的长辈身份,不好发作。
秦卓峰嘿嘿笑道:“今日便是朱权下聘迎娶老夫的徒弟徐瑛。”
李景隆眼见如此一幕,听得这般言语,不禁呆若木鸡,心中隐约有了不祥之感。
徐辉祖闻言心中大震,断然道:“婚姻大事,岂可如此儿戏?此事太过荒谬,恕晚辈难以从命。”他内心极为不喜朱权,更念及其亲王的身份,婚姻之事自然须得皇帝陛下一言而决。这般草率行事的将自己的姐姐徐瑛嫁与朱权,实非内心所愿。
秦卓峰伸手施施然自怀中掏出一张下聘的帖子,扬手笑道:“枉你饱读诗书,岂不闻天,地,君,亲,师之言?目下徐达兄弟夫妇俱已不在,瑛儿的婚姻大事,自然可以由为师我做主。”
徐辉祖闻言不禁气结。口中犹自强道:“父母之命由前辈以师尊之命代为,姑且不论,可这媒妁之言却在何处?”
秦卓峰哈哈一笑,手指坐在一侧的李景隆笑道:“曹国公家世显赫,乃是李文忠将军嫡子,这媒人身份以老夫看来,倒也不会辱没了瑛儿。”
李景隆此时正自喝茶,闻言惊得将一口热茶喷出,连连咳嗽下伸手接过那张大红色的下聘帖子,眼见上面媒人的名字赫然便是“李景隆”三字,差点没骇得三魂去了两魄。他虽是无甚大才,却非不知厉害之辈。回想当今皇帝陛下那般雷霆手段,自己这个名正言顺的媒人只怕明日就得大祸临头,思虑及此,一屁股坐回椅中,动惮不得。
徐辉祖张口结舌面红耳赤的道:“这,这……”父母之命由秦卓峰这个师尊代劳,媒妁之人吓得面无人色,倒还是名正言顺,让他气急败坏,倒是难以在仓促之间想到反对的理由。
秦卓峰深知朱权今日迎娶徐瑛之事万不可张扬开去,走到徐辉祖身前笑道:“今夜的喜酒,你这个舅郎官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去喝。”言罢伸手一指点来,封住了徐辉祖的穴道。
徐辉祖闻得朱权今夜就要强横霸道的迎娶自己的姐姐徐瑛,不禁脑中一片混乱,犹自没有反应过来便即软到在地。
正在此时,却听得一个女子的娇呼一声,一个身影疾步走进客厅,正是身穿淡黄衣衫的徐瑛。她方才在后院练剑,闻得丫鬟禀报师傅到来,回到闺房换过衣衫后,这才赶来相见。刚走到门口便即目睹师傅出手制住自己嫡亲兄弟的一幕,不禁有些花容失色,不明所以。
待得听闻师傅诉说朱权这般横蛮的迎娶之道,不禁心如鹿撞,满脸绯红的跺足嗔道:“岂有这般行事之理?”
“事急从权,倒也怨不得朱权这小子。”秦卓峰呵呵笑道,言罢转头对正自想悄悄溜出厅去的李景隆淡淡说道:今日曹国公下聘而来,可是众目睽睽之事,你今日逃去,难道明日便也逃得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