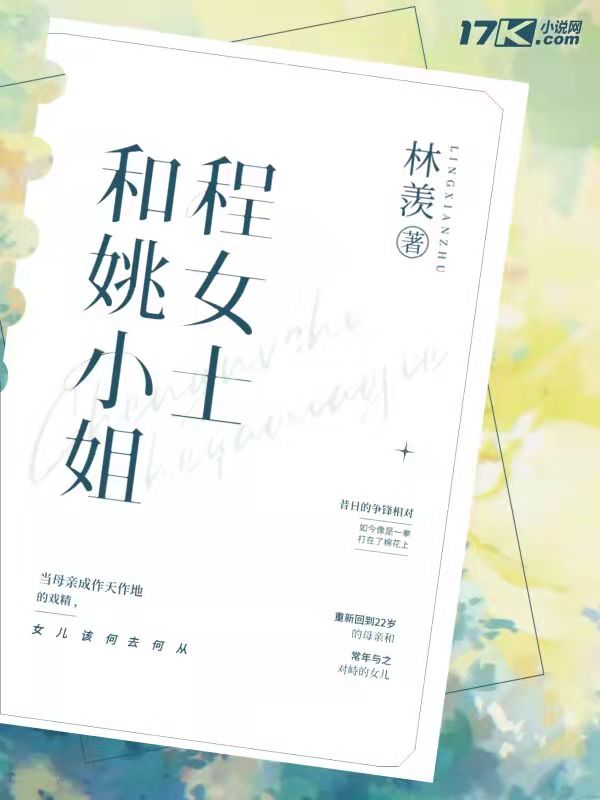宋顺才看看郑庆义的面色就劝说:“你也有愁的时候?不过你担心啥,我相信你的判断能力,只不过是出手早了点。你要是现在出手,那可就稳操胜券了。”
郑庆义有些不自然地笑笑说:“大哥不是挖苦我吧。你说这是怎么了,我总觉得有点不正常。往年大豆也不会降到这种程度呀。”
宋顺才安慰着:“寒山别瞎猜了,我估摸着是快出头了。”
郑庆义两手向外一摊说:“可我快要榨干啦呀。”
宋顺才:“瞧你都眍喽眼儿啦,别说出口,我知道你啥意思,到不了那个时候,不是还有我呢吗?”
郑庆义听到这话放下心来:“有大哥顶着,我还轻松些。”
因为郑庆义知道宋顺才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咋说也是两码事,于是说:“你不知道,向斋跟我说吉林牛家的事了。”
宋顺才说:“你说的事我知道。其实,你跟他家不一样,他家是借钱做买卖,所以买空卖空,吉林永衡官银号就得透支支付押金。那么长的时间堵不上这个窟窿,谁敢不封他家财产清帐?虽说是我给你担保,可你到现在还没到透支那份堆上。就是透点支也无妨,我是信得过你的。再说你多拿点利,我还多赚你钱呢。不过你也得快点了解取引所的情况,看是哪儿出了问题,不行赶紧合卯。”
郑庆义说:“大哥你的眼睛也都红了。现在就得挺着了,要不亏的太多了。手头能活动的钱都交了押金。实在不行,我反正也做好准备了,大不了我回老家去。”
宋顺才拍拍郑庆义的肩膀说:“就这么退缩了你,就不是你郑老寒呀。放心吧,即使透支到那份堆上,还有大哥我吗?”
郑庆义说:“大哥,你这么说我就放心啦。我想回老家,顺便到旅顺、天津看看,摸摸那里的情况。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真要是到了那一步,败家了,家乡那两个铺子给我留下就行。”
宋顺才:“瞅你,变得有点婆婆妈妈的了。我咋听着象是拜托后事似的。不要太伤感,既然走到这一步,你认为对就走下去。有大哥我,不会让你走那步的,放心吧!哎——,你和玉花咋样了?要不我找她唠唠?”
“大哥,你就别费心了。能做到的事,我不会轻意放弃。”
宋顺才看看无奈的郑庆义,不仅叹口气地说:“这玉花是咋了。那大烟不抽不行吗?我看你趁回家的机会,再跟她好好唠唠,你俩分开一段时间,让她也好想清楚了。不然这么就放弃真是太可惜喽。”
“大哥,跟你说实话吧。是有人整事,当然我不能说我没责任。可我也不能把一个活人绑在自己身上。我一离开那个李奇岩就来我家。把我的堂弟和小舅子都拉下水。人啊,一抽上大烟,不像个人样了。我就按你说的,回家前,再找她唠唠。如能跟我回去,是最好的结果。唉——。”
回老家前,郑庆义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想起宋顺才的劝告,决定和玉花好好的谈一谈。宋顺才也惦记着这事,不时的来电话问他谈了没有,还为玉花说了不少好话。郑庆义忽然想起女儿郑常馨,这次回老家,玉花不走,也得把女儿带走。女儿不能长期跟她妈在朱瑞卿家。这次回家,啥时能回来还说不定,郑庆义担心玉花的不良行为,会对女儿有不好的影响。长时间让郑常馨在玉花身边,郑庆义放心不下。想起女儿,他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女儿在玉花身边,长期被大烟熏着不好。哎呀,光想着玉花了,咋没为女儿想想。郑庆义这时才着急了。经过深思熟虑,郑庆义决定把郑常馨带回老家,女儿不在玉花身边,或许她为了女儿着想,会使她痛下决心把大烟戒掉。
朱瑞卿家临街房五间,大儿子结婚用了一间,还有两儿子两女儿未婚。玉花来后,专门把女儿住的房腾出来,让玉花住。因为玉花抽大烟,谁也不愿意跟她住。本来就不太宽敞的杜家只好挤着睡了。后来,郑庆义又把郑常馨送来,显得更挤了。没办法,谁让人家是东家了。杜家每天还得伺候玉花吃饭,当然了工钱是少不了的,不过这事到是挺烦人。有时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来这儿,打扰了杜家平静的生活。这不三不四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李奇岩,大衙门里的人,杜家那敢惹呀。
郑庆义下车,敲朱家大门。开门的是朱瑞卿老婆,郑庆义乐呵呵地说:“老大嫂,你好呀。让你受累了。”
“哎呀,东家,累点怕啥。就是事多,忒烦人。常馨,你爹来了。东家快请进屋。”
郑常馨在屋里听见,连忙跑了出来喊:“爹,我想你了。”
郑庆义把郑常馨抱起来,进玉花住的屋。一推门一股强烈大烟味呛得郑庆义咳嗽几声,郑庆义回身问:“常馨也在这屋?”
“那能呢,跟我两闺女在一起。跟她妈受得了吗?”
郑庆义放下郑常馨,强忍着这难闻的气味,进入玉花住的屋。只见玉花背身躺在炕里,正摆弄大烟枪,她把烟灯点着,并将灯芯火调大。看样子是准备抽大烟了。看到玉花佝偻着身子,心里一阵难受,一时不知这话咋开头,就扭过身子坐在炕沿上不再看她。
郑常馨趴到炕上,推她妈说:“妈啊,爹来了。你看呀。”
玉花费劲地转过身来,眼睛惺松,没等说话,就张着嘴打着呵欠。满脸的倦意地说:“知道是你来了,等我抽一口再说。”
玉花说着把烟枪冲着烟灯点起来,随口吱吱抽着。一连几口入肚,很久鼻孔里才冒出丝丝烟来。大烟枪慢慢地冒着烟雾,云雾般缭绕在玉花周围。忽然玉花呛了一下,止不住地咳嗽起来,一口粘痰湧出,玉花吐到地上。
郑庆义胸口不觉往上一涌,一股怒火上来。想想不是发火的时候,他强压下来。这可真是看不着还有点想,看着了还烦。
郑庆义:“常馨,你出去吧,这里太呛人,忒儿嚃地多埋汰。我和你妈说几句话。”
郑常馨很听话地出去了。
抽完大烟的玉花来了精神,坐起来说:“咋?这么好心看我来了。我就这德性了,你也别劝了。”
看着玉花的神态,郑庆义心里觉得直恶心。想好的词一句也说不出来。他坐在离玉花挺远的炕沿上,也不看她就说:“回老家,最好是跟我一堆儿回去。”
“我不想戒了,还回去啥呀。”
“你就不能为女儿想想?”
“女儿有你呢,我放心。”
“常馨她奶想她了,到时候的时候我要带她走。”
“我就这德性,跟着我也不合适。带她走也行,省得拖油瓶子。”
“你说的这是啥话?”
“啥话?唐伯虎名画。你把我放到老朱家,人不人鬼不鬼的,还能在这儿呆一辈子呀。我早晚得找人家走喽。”
“瞎说!找啥人家。我在南头找好地场了,过年开春就给你盖几间房。你搬出去自己在那儿住,多咱你把烟戒了,到时候的时候再搬回来。”
一听这话,玉花“哼”一声说:“瞅你那抠样,盖个破房子显啥大方。连点烟钱都不给。”
郑庆义没吱声。玉花扯过一个笸箩,从里面掏出一把瓜子嗑起来。沉默一会儿说:“你郑老寒也忒损了,手指缝拉拉点就够了。也好,你不让我抽,有人供我,咋说比在你面前自在。”
郑庆义听到这话,更无话可说,只剩下捯气了。
玉花嗑瓜子,一会儿瓜子皮嗑了一堆,玉花擦擦手说:“你给我盖房子,让我单过算是咋回事?”
郑庆义大声吼着:“咋回事?还用我说吗。瞧你这德性,照镜子瞅瞅,都啥样了。几天没见,看你这脸灰突噜的,象个病秧子似的。咋就不能戒了呢?”
玉花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是想戒掉,可这口癮咋也戒不掉了。你既然烦我了,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郑庆义心一软说:“玉花呀,还是跟我回老家吧,上回戒得挺好的。这回你下点决心,肯定能行,咱再不回来了。省得在这儿又遭了道。行吗?”
玉花望着郑庆义的背影,不仅心潮起伏,心里一阵阵剌痛,强忍着泪水:“寒山。我知道你对我好。是你把我从火坑里救了出来,没你也就没有我自个儿的新生活。我知足了,比玉红多活了那么多年。自从进了你家门以后,过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享尽了福。可是,过惯了那样的生活,每天孤单单的让我感到枯燥乏味了。都是我不好,也没怨你的意思,这都是没事找乐上了瘾。想和你好好地过日子,可你的洁癖让我受不了,这也烦那也烦。我还烦呢,跟谁说去!还让我回乐亭,你说我还能回去吗?还不得让人家笑话死我,烟都戒了,又把它捡起来,这是啥老娘们呀,我没脸见她们,你爹妈对我挺好,大姐也不烦我,一口一个妹子,对我们娘俩好着呢。说实话在老家那一年,过得真挺很开心,要是不回来就好了。”说到这儿呜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