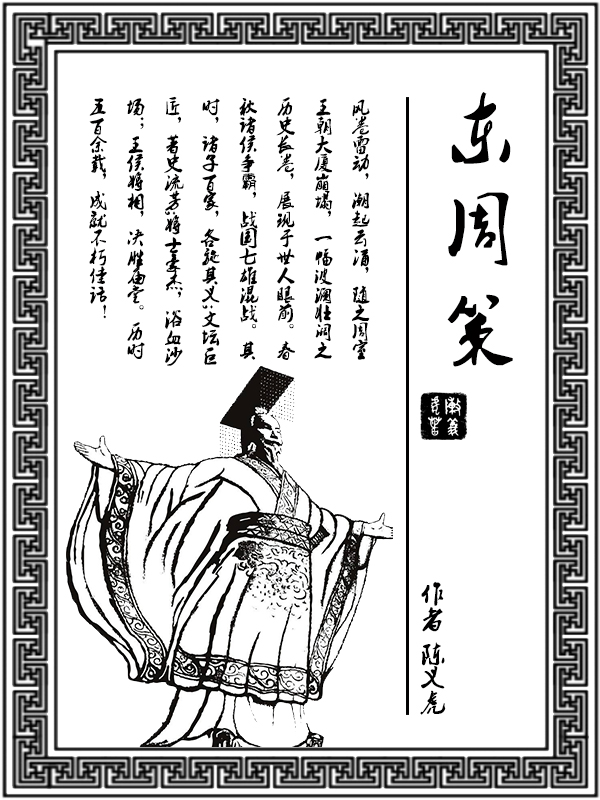第二十二章
爷俩用乐亭土话,演得活龙活现。每到爷爷因唱皮影开心的时候,郑庆义就说:“爷爷等我赚钱了,我一定要专门给您盖个大戏院,给您搭个合手的戏班子,让您上台好好唱出戏。”
爷爷就会笑呵呵地说:“我孙子就是孝顺,知道爷爷得意那口。”
驴皮影,也叫乐亭影。起始于明代末期,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不过,清末、民国初年才盛行起来。一般有两个人操纵,一人为上线,另一人为下线。所看到的影人动作,是有三根杆子,一根主杆和两根手杆。两人在影窗后,拿、贴、打、拉、唱,相互配合默契,使影人活灵活现。皮影告白是乐亭方言,具有良好的唱功基础。唱腔分为大板、二性板、三性板、散板以及平唱、花腔、凄凉调、悲调、游阴调、还阳调,还有特殊句式而得名的三赶七等各种腔调。驴皮影形式简单,实际是很复杂的艺术。驴皮影的雕刻制作,人物造型唱腔分类,等等都很严格的要求。
想想小的时候,爷爷最喜欢自己,常常领着走街串巷唱皮影,自从离开爷爷,很少能见到爷爷了。爷爷的离世让他感到内疚。……
这时胡勒根的爹过来说:“孩子,时候不早了,赶紧发送吧,人走了入土为安。”
郑庆义点点头和郑庆和、郑庆恭一起看了爷爷最后一眼,在张家烧锅和合林子众多乡亲们帮助下,把爷爷安葬了。郑庆义又摆了酒席,答谢乡亲们的帮助。
郑庆义这时才有时间和自己的两位老朋友说话。他拉着王贵和胡勒根的手说:“谢谢二位哥哥,这情义让我无法报答,如果不嫌弃寒山,二位兄长就随我到五站。到时候的时候我那小米铺也需要两位哥哥帮帮。”
两人相互看看对方,王贵先开了口说:“我也不想在烧锅干了,只是不能这么急跟你走,待跟家人商量商量,有些事还得处理处理。消停儿的再到你那儿,咋样?”
郑庆义说:“帅哥在烧锅里费点事,蒙哥没啥事就跟我走呗。”
胡勒根冲郑庆义笑笑没等吱声,王贵就接着说:“胡老三现在可牛了,是一带有名的斗官,他要走比我还费事。”
赵正义看着胡勒根说:“蒙哥,这是真的?”
胡勒根这才说:“我进了粮铺吃劳金了,还给了我二厘身股。”
郑庆义说:“我现在还不行,别看现在是小铺,到时候的时候,一定会办成大粮栈!”
胡勒根:“我没说不去,都是弟兄好说话。只是有一条:老话说的好,有准斗,无准手。我这斗可是有准头的,我不能帮你坑人。坑蒙拐骗的事我决不干。师傅临终时拉着我的手说:‘千万别存坑人心,斗里能量出好坏人。’”
郑庆义非常高兴,上前拉着胡勒根的手说:“蒙哥,就凭你这话,现在就到我小铺当掌盘。到时候的时候给你最少四厘身股。”
随后把两人脖子一搂说:“我是啥样人你们还不清楚吗?爷爷在天之灵看着我们,坑、蒙、拐、骗发不了大财。藏奸使坏我做不来。要想做大买卖,诚信才是本。我在那几年了,凭的就是这个才站住了脚。我坚信我的小铺到时候的时候一定会变成大粮栈,哥哥们可快来呀!”
合林子,西北风飕飕刮过,阴沉沉的天空灰蒙蒙。王贵请郑庆义哥俩到自己家里:“郑老寒,你来一趟不容易,想让我去你那儿,得你嫂子同意。”
郑庆义:“说的对,是得拜见帅大嫂。”
王贵不好意思地说:“你嫂子长得蠢,见了可别笑话。”
胡勒根在一旁说:“谁说的,可好看了,就胖了点。不过,人都说帅哥娶了个母夜叉。我可不知道咋回事了。”
王贵挥起拳头,胡勒根快速躲过。
王贵随后对郑庆义说:“孩她妈给我生了三个儿子。都挺好的,就是疑心重点。”
胡勒根又凑到跟前:“要说帅哥娶了个好老婆。嫂子娘家是开大买卖的,怀德、公主岭都有分号。不知咋地,就看上了帅哥。”
王贵沾沾自喜地说:“那是,想当年,你嫂子是非我不嫁。十里八村谁不说我俩是天造一对地设一双。”
胡勒根马上接话说:“帅哥就是有福,人长得漂亮,娘家又有钱。听说她爹不同意,要你入赘?”
王贵:“我老丈人不是不同意,是要我入赘。只要我同意,生孩子姓她周家姓,公主岭的铺子交给我。哦——,你嫂子姐五个,她是老大。”
郑庆义很感兴趣地问:“这不挺好的吗?到时候的时候,你就是大东家了。”
胡勒根:“可不是,有钱人不当,非得给人扛活。”
王贵庄重地说:“有辱祖宗的事我不能干!我说为了你嫂子,入赘勉强可以,财产我不要,孩子必须跟我姓。你嫂子真够意思,宁可跟我出来受苦,受罪。一分钱陪嫁没要,非得跟。现在好点了,开始是她娘偷偷给点。后来,她爹也就不管了,有个为难遭灾儿的,老丈人也出面周济。”
郑庆义:“这不挺好的吗,咋叫母夜叉了。”
胡勒根哈哈大笑说:“帅哥越来越帅了,嫂子越来越胖。”
王贵委屈地说:“我从不拈花惹草,可她生完孩子后,疑心越来越重。每天干啥了都得跟她学一遍,要不然就跟我作。真是受不了。翰臣,我让你到家,就是想让你说说,要不然别说五站,哪儿都不行!”
就在郑庆义去合林子时,玉花所在的宝顺书馆出了大事。
这天,任理堂正在喝茶水,有人报告说:“有个自称是黑龙江省督军府的人,说是来这儿找她媳妇的。”
任理堂腾地站起来说:“哎呀,还真的找上门来了。打出去,不准进屋。”
来人下去后,任理堂转了一圈自语道:“不给点厉害,不知我马王爷长三只眼。”说着拿起电话就拨,接通后说:“警察署吗?我这儿有人捣乱,他说是黑龙江省督军府的人,不知真假,你们给查查。”
电话里回答道:“你谁呀,口气这么大?”
“别他妈的费话,我是任理堂!”
“哎呀,任大掌柜。我李奇岩可是服你了。给人一巴掌,马上就来个甜枣。”原来是李奇岩接的电话。
任理堂:“我寻思谁呢。记仇不是?”
“哪里,任大哥仗义,我李奇岩唯大哥马首是瞻。不就是个当兵的吗?值得你大惊小怪的。”
“少费话,管不管。我不想再见到他。”
“别生气我可没说不管。我知道你手眼通天,关东州要是来人管,我可是得罪不起。马上去!”
“这就对了,我新整来的好货,比玉花那娘们儿强多了。这事办利索了,我让你尝新。”
一个身着东北军服装的人正在门口,被两打手打得鼻孔、嘴角都出了血。李奇岩带两个小腿子赶到,见此情景就大喊:“咋回事?咋回事?”被打的人以为来了救星,忙说:“我媳妇走丢了,有人说可能在这里。我来找,他们不让我进,还打我。”
李奇岩装模作样:“哦,有这事?让他看看不就完了?”说着看两打手使眼色。
打手说:“巡捕长,我们这里的人可都是警察署上了户口的。啥人都上我们这找人,还开不开了。他这是无理闹,到这里嫖女人不给钱,仗着自己是个当官,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巡捕长,你得给我们做主。”
李奇岩:“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有理到警察署说去。带走!”
来人见是警察,没有一点怀疑就跟着去了警察署。到了警察署,李奇岩就变了脸。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毒打,任那个人如何分辩都不好使,从此,再也没见这个人出来。
任理堂得到实信放心了,手拿着卖身契来到小黑屋,向冯萃英说:“从今个儿起,你叫玉红。冯萃英这个人不存在了。我不能白养活你,现在就出去接客。”
冯萃英说:“不!不!我找我丈夫,打死我也不接客。放我出去呀。”
任理堂把手中卖身契让冯萃英看:“看到了吧,我是花两千大洋买的你。想出去行,拿两千块大洋你现在可以走。”
“我身上的东西都让你们收去了,我那儿来的钱,先放我出去,找到我丈夫,要多少钱都给你。”
“哼!你还在做梦,拉她出去接客。”
打手上来就拉冯萃英走,冯萃英死死抓住坑沿嚎叫着。任理堂:“狠狠地打,就是别碰着脸。”
两个打手上来就是一阵毒打。冯萃英紧咬牙关,就是不应。
老鸨子过来说:“哎哎——,指着她赚钱呢,打坏那个多那个少?是不是换个法子。”
任理堂:“啥法子?”
“攻心为上!”
任理堂就拉下脸来:“她丈夫来折腾我,我也得折腾折腾她。好吧,我先攻攻她的皮肉。去——,把她衣服都脱了。”
已经没有力气的冯萃英死死扯住裤子。任理堂大喝道:“把裤子都给我撕了!”
打手们上去一阵乱扯,衣服碎片扔了一地。冯萃英光着身子,抱着双腿蹲在地上。她已经没力气反抗了。她咬着牙,怒目而视,心中充满仇恨。
这时,任理堂拿起烧红的烙铁,吐口吐沫,“嗞”一声冒股热气,在冯萃英面前一比划:“尝尝烤肉的味道?”随后示意打手,把冯萃英按在木板床上,然后问:“去不去接客?否则别怪我下死手,我可不能花大钱买你白养活。”冯萃英挣扎几下,无济于事,无奈地闭上眼睛。
任理堂凶残把烙铁在离冯萃英身子很近处晃了晃,终没下手,随手把烙铁往火盆里一扔恶狠狠地说:“既然她不主动接客,那好,就让你们兄弟几个享受享受吧。”
打手们大喜过望:“东家,你说的是真的?”
“你们也辛苦了,这次不要钱,可别折腾坏喽。下次想干的话,到柜上交钱!”
听到这话,手下人乐不可支,急忙脱下裤子,**了冯萃英。
任理堂看了看:“这个犟种,再不听话有你罪遭的。”
出门后,叫来一个岁数较大女人:“这几天你好好照顾她,劝劝她。再犟下去没好果子吃。想宁死不屈,我也不怕白瞎两千大洋!”
女人小声说:“我都磨嘴皮子了,一点也不进盐境。要是找个会唠嗑的劝劝她呗。”
任理堂老婆,也就是老鸨子喜姐过来:“你呀,现在老宠着玉花,事儿都不让我管了,你就让玉花劝去呗。把她折腾死,那钱也不是打水漂白来的。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任理堂恍然大悟:“我这辈子多亏了你,要没有你能发财吗?听人劝吃饱饭,这就去找她。”
且说,郑庆义一行五人,很快就到了王贵家了,这是一个小四合院。出来一条狗“汪汪”几声,被王贵一阵吆喝,夹着尾巴回到窝里。
王贵说:“该咋地是咋地,我老丈人心眼也挺好使的,这院套是老丈人出钱盖的。要我自个儿,不知啥时才能盖得起。”
胡勒根进院就喊:“嫂子,有贵客来了。整点啥好嚼咕?”
一个胖胖的女人推门出来:“你胡勒根,没事就来噌酒,今个还当贵客了。”
胡勒根:“嫂子,我那敢骗你呀,你看,真有贵客。”
郑庆义一看,可不一般的胖女人,而是太胖了。特别是臀部向下悬垂,大而松弛,腰部脂肪特多,使腰和臀的曲线没了,形成桶状。身上穿着暗红色丝绸子大褂,紧紧地贴在身,看上去肉嘟嘟。走起路来,浑身肉发颤。她手里提着一根碧绿烟嘴的大烟袋锅。引人注意的是身上挂着一串钥匙,系在胸襟靠腋窝的纽扣上,随着她的走动,叮当作响。
王贵忙介绍说:“老婆,这就是我结拜的三弟。”
胖女人打量一下郑庆义说:“哟——,我以为三弟瘦小,象个秀才呢,原来五大三粗的人啊。说起你呀,耳朵都出茧子了。嗨——,爷爷过世了,节哀顺变,听孩子他爹说,爷爷可惦记你了。”
王贵打断:“有话进屋再说。”
胖女人忙说:“对对,你可是贵客,快进屋。我马上炒几个菜,你们哥几个喝两盅。”
然后对王贵说:“我先把孩子送到我妈那儿,你先沏点茶,一会儿我就回来炒菜!”
郑庆义进屋就小声说:“胡三哥,嫂子哪象母夜叉呀。分明是贤妻良母。”
胡勒根:“那当然,嫂子非常大方。我一来就得喝点。要不就不高兴。”
王贵:“行了,别唠你嫂子了。说点别的。”
胡勒根:“说啥呀,有啥好说的。”
王贵:“寒山,你现在开小粮米铺了,还记不记得当年你要拜我为师?”
郑庆义:“当然记得,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还当不了糟腿子呢。”
郑庆和这时才有机会问话:“哥,咋会跟王哥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