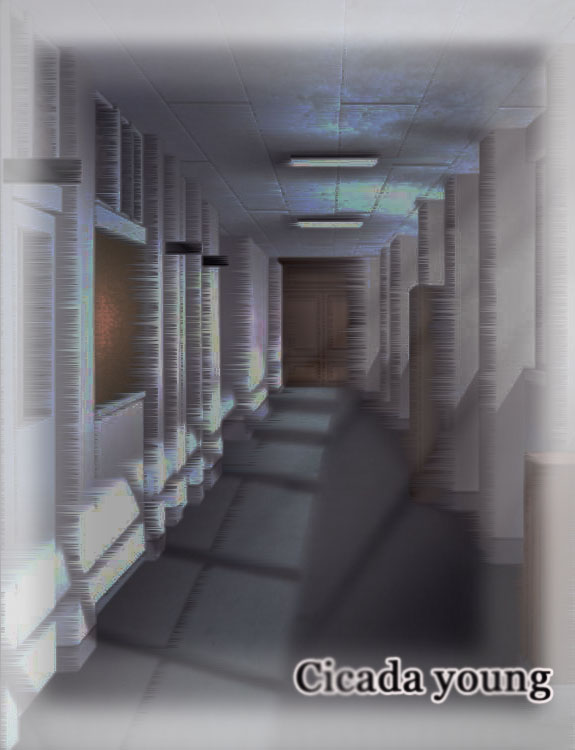此时,城门前已乱作一团。本来未时是一日里出进城门最繁忙的节点,但是接到指令要关城门。这边是赶着关城门前出城,那边是赶着关城门前进城。再加上城门外众多的灾民,拥在城门前。进也进不来,出也出不去,两边的人群皆是炸窝般七嘴八舌的叫嚷。
眼见相持不下,魏千总又调来一队兵卒,这边刚堵住一个口子,那边又被挤破一个口子,跑进来的人被兵卒抓住。兵卒显然人手不够。魏千总气势汹汹地站在城门洞大吼:“关城门……”但是,城门洞里全是人,有百姓有兵卒,启动门闸的兵卒干着急,没办法。
这时,从大道上飞驰而来一队甲胄闪亮的骑兵,单从服饰上看还以为是从三大营调来的兵部将官,一些守城的兵卒大喜,去叫魏千总:“千总,兵部来人了。”魏千总正自纳闷,那对人马离近了才认出是锦衣卫缇骑。
高健一马当先,直奔到魏千总面前:“魏千总,这里发生何事?”
“高千户,你来的正是时候,灾民围城,我已遣人上报朝廷。”
高健翻身下马,对着魏千总干笑了两声道:“老兄,我如今已不是千户,降做百户了。”高健说着扶了下头盔,露出额头,额头上缠的棉布上还洇有血迹。
“哦?高健你受伤了?”魏千总盯着高健的额头问道,“谁这么大胆,敢对锦衣卫下手。”
“唉,别提了,诏狱里跑出去几个囚犯。”高健压低声音道,“宁骑城没割下我的脑袋已是万幸,这件事被王振生生压了下去,即便严防也还是露了风声,让几个大臣参了一本,要不是找到一个背锅的倒霉鬼,宁骑城的锦衣卫指挥使也不保了,他被迫交出了东厂掌印。”
“哦……”魏千总瞪着眼,张着大嘴半天没合上,“那……那个倒霉的背锅人是……”
“是孙启远,”高健近似幸灾乐祸地说道,“这小子那天出门定是没看黄历,怎么那么倒霉,在关键时刻,他带着宁骑城出了诏狱,说是遇见什么逃犯,结果逃犯没抓到,诏狱里倒是逃走了几个。”
魏千总乐的扯着嗓子干笑了几声,笑过又问道:“他个小小的百户,再降……降到……”
“被扔进诏狱大牢里了。”高健沉下脸,摇着头道,“这小子只能靠自己的命数了。”
魏千总绷起嘴,眼珠子在眼眶里转了几圈,压低声音道:“兄弟,忘语国事,咱们还是当好咱的差吧。”
高健点点头,向身后的一个校尉喊道:“到人群里盘查。”
今日,高健奉宁骑城之令去各个城门巡查,海捕文书在每个城门都张贴上去,已过去两天,扔没有任何动静。他望着城门前聚起的人群,也不知萧天他们出城了没有?正胡思乱想,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背后响起,高健回过头,看见一队人马飞驰而来,打头的正是宁骑城。
高健忙迎着跑过去:“宁大人,这里……”
宁骑城一挥手,显然已知情,他翻身下马。一旁的魏千总看见宁骑城过来,急忙跑过来行礼:“见过宁指挥使。”
“魏千总,速速关上城门,放跑了逃犯,你这差事可就别干了。”宁骑城说着,望了眼城门洞里已烂成一片片的海捕文书,皱起眉头。
“是卑职的错,卑职马上差人换新的。”魏千总说着,转身跑向城门。
宁骑城鼻孔里哼了一声,走向高健,高健急忙恭顺地低头静立一旁。
“高健,你说那帮逃犯现如今出城了没有?”宁骑城冷冷问道。
“他们傻呀,都两天了,还不走,等着被抓呀?”高健低着头道。
宁骑城似笑非笑地端详着高健,看了看他脑门上伤,问道:“是谁把你打伤的?”
“这……我哪会看清……光线太暗,人太多……”高健嘟囔着,一只手扶住头,一脸可怜样。
“你知道当值的牢头怎么说吗?”宁骑城笑道,“还有那几个狱卒,众口一词,说劫匪穷凶极恶,个个三头六臂,从地底下钻出,黑压压望不到头,说你像个天兵天将从天而降……”
高健脸一红,道:“大人,是有点夸张,他们也是想……”
“我倒是想……”宁骑城打断他的话,阴森地盯着他的脑门,一阵冷笑,“这一招,分寸拿捏的真是好呀……”宁骑城说完转身向城门走去。
高健站在原地,寻思着宁骑城的话,脸上冷汗冒出来。
在离高健十丈之外的巷口,萧天拉低帽檐和明筝躲在一个铁匠铺里。“萧大哥,那人是高健。”明筝认出高健,“他看上去没事,也没受到牵连。”
萧天点点头:“这次多亏有他,走吧,宁骑城过来了,咱们快撤。”
大道上一个校尉快马加鞭赶过来,直奔宁骑城面前,然后翻身下马,走到宁骑城近前低语了几句。宁骑城脸色一变,转身叫高健:“你在这里守着,我进宫去。”
宁骑城只带了两名护卫向宫城疾驶而去。他此时脑子里颇不平静,猜不出王振急着召见他又为何事?那日诏狱被劫后虽下了封口令,但还是泄露了风声,震动朝堂。平素与王振为敌的那帮朝臣立刻联名上疏要追究他的罪责,有言官更是列出他十宗重罪。
此奏疏被王振截下,并有意让他过目。他无话可说,十条大罪条条属实,却皆是为王振所差使,但在朝臣面前,他百喙莫辩。不得已他交出东厂掌印以封众人之口。为俺人耳目,他又交出了孙启远,算是替他受过。到此诏狱之事才算翻了过去,今日又是所为何事呢?
宁骑城顺着甬道走进司礼监时,天已擦黑。正是掌灯时分,司礼监里小太监们挑着宫灯到各处点灯,一个小太监眼尖看见他走进来,忙跑到里面通报去了。不一会儿,高昌波笑眯眯地走出来。
“先生正在里面候着你呢。”高昌波笑着说。
宁骑城随高昌波走进房里,看见王振斜靠在炕上一堆软垫上,有气无力,面色阴郁,似是刚发了一通脾气,一旁伺候的两个太监连头都不敢抬。王振看见宁骑城进来,招手指着一旁一张椅子让他坐。
高昌波给宁骑城捧上一盏茶,宁骑城接过端着,并没有喝,而是关切地望着王振,问道:“干爹,你脸色这般不好,莫非身体有恙?”
“无妨,只是偶遇风寒。你说怪不怪,这大日头的得此症?”王振说着,手里摆弄着一串佛珠再无下话,只是用眼角瞥着宁骑城。
宁骑城端着茶盏,慢慢啜饮,只等着他开口说下文。
“此次收了你东厂大印,也是权宜之计,”王振数着佛珠开了口,“先要堵住那帮老家伙的嘴。再说了,东厂督主的位置一直空着,放眼朝堂哪个人敢接这个印,早晚不还是你的吗?但是……以后若再出纰漏,我可是无脸面再给你兜着了。”
宁骑城放下茶盏,抖袍服跪倒在地:“干爹教训得极是,儿子知罪。”
“唉?坐得好好的,如何出溜到地上去了,来……坐着。”王振向地上的宁骑城摆手,“来,坐着……你说那日逃出去三人?”王振眯着眼睛突然问道。
“是。”
“于谦呢?”
“还在。”宁骑城低着头回道。
“唉?你说这老东西为何不跑呢?”王振瞪起眼睛,“他要是借机逃出去多好,我便沿街放十万鞭来庆祝,这个老东西真不让人省心。”
“此人便是茅坑里砖头,又臭又硬。”宁骑城道。
“又臭又硬也得放了,当初拿他入狱,也是仅凭王浩之死以他兵部守卫京城不力为由,并没有抓住他的把柄。”王振神经质地猛抓着头皮,“我今日唤你来,说的便是这事。吏部尚书陈柄乙,户部侍郎高风远联名上疏奏请皇上赦免于谦,皇上已经准了。不过,这次我之所以不露声色,他们也是高兴地太早了。如今山西河南大旱,皇上已准从国库拨三十万两银子赈灾,这个差我力荐陈文君去办,皇上也准了。”
“啊,干爹,你这招暗度陈仓,用的好。”宁骑城干笑着,一个劲奉承,“怪不得这两日城门口,灾民围城,这个差……以于谦那个老东西交换,咱不亏。”
“你懂什么?”王振干咳一声,道,“我担心于谦插手赈灾事宜,他可是才从两地巡视回京。”
“此次给他个教训,若再不老实,再抓进去不得了。”宁骑城道。
“娃子,此人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要时时派人盯住他,不要掉以轻心,决不可让他搅了咱们的事。”王振眯起眼睛寒光一闪,盯住宁骑城嘱咐道。
“是。”宁骑城急忙点点头,眼角的余光瞥见王振闭上双眼,便起身告辞,王振微点了下头,依然闭着双眼声音含糊地道:“下去吧,好好办差。”
宁骑城走出司礼监时,夜色已深,宫里更夫刚好敲过头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