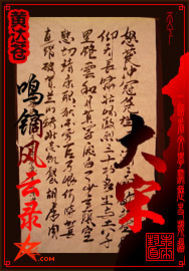即便不是阴雨天,外面日头高照,牢里也如同风雨晦暝一般,暗无天日,清冷凄凉。牢头王铁君顺着石阶往下走,近日犯了风寒的老寒腿越发不听使唤,下了几节台阶便出了身大汗。
石壁上插着火烛,昏黄的光照亮牢门,那门上画有狴犴画像,青面獠牙,狰狞可怖。这边便是‘人’字号牢房,五步一岗,戒备最为森严。牢房里没有窗,只有靠近铁栏栅外走廊里,石壁上插的火烛,发出微弱的光。
几个值岗的狱卒向王铁君打着招呼,王铁君点着头,一路走过来,一边叮嘱着:“哥几个,精神着点。如今咱这牢里关了重犯,宁大人随时都会来,谁碰到刀口上,可别埋怨老哥没提醒。”
“是,是。”几个狱卒应了几声。
“那个白莲会堂主关在哪间?”王铁君问道。
“老哥,你右手第二间。”一个狱卒回道。
王铁君向前面走了几步,看见这间牢房面墙坐着一个白衣囚徒。他面壁而坐,眼睛专注地盯着石壁。水珠从石壁上渗出,在地面砸出一个个小坑,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由于这座牢房是建在地下,免不了要受地下水汽的叨扰,但有一点好处,便是固若金汤,任何人进了这座牢房都会打消逃出的蠢念,逆来顺受。这便是诏狱让人闻风丧胆的原由之一。
王铁君看了眼铁栏栅里面纹丝未动的牢饭,叹息一声。他是听送饭的狱卒说这个牢里牢饭三日未动,他才赶紧跑来,他可不想犯人还未审,便在他的牢里一命呜呼,让他对宁大人无法交差。他又叹息一声开口道:“这位人犯,听老夫一句劝,好死不如赖活着,你且吃下饭,将养好身子,才有力气受审。或许你也听说过,诏狱里十八般酷刑,那可不是浪得虚名,若要在这鬼门关里过一遭,没有个好身板,那可要白瞎了。”
王铁君看白衣囚徒依然一动不动,便接着劝道:“你瞧你隔壁的人犯,此人姓于,大名于谦,人家获罪前可是朝里大员,但进了诏狱便很守规矩,每日送的牢饭人家吃的一粒不剩,送回碗时还要对我言一声谢,这么好的人犯着实让我很是爱戴呀。”
王铁君看他依然不为所动,便依然耐心地开导道:“这位人犯,你若觉得冤屈,便更要吃饱饭,好有力气伸冤呀,最起码要见到主审官,这样你便可以有冤伸冤……”王铁君还没说完,突见白衣人站起身来,他几步走到铁栏栅前,端起碗呼噜呼噜往嘴里扒,不一会儿一碗冷饭便进了肚。
王铁君看自己说服了他,吃下了饭很是高兴,兴奋地道:“你终于想通了,太好了。”
“你可以走了,我不想有人再来打扰我。”柳眉之寒冰般的双眸,瞪着他,把碗扔回到托盘上,起身又回到石壁前,面壁而坐。
王铁君愣怔了片刻,没想到自己的好心换来如此的奚落,悻悻地叹息一声,低声道:“保重吧,若是你见到宁大人,还是这般骨气,我便是真心服了你了。”
王铁君伸手到铁栏栅里收拾好碗,拿回托盘。只要看到人犯吃了饭,他便满足了,以后的生死靠自己的造化了。他站起身,抱着托盘,瘸着腿往回走。脚步拖拖踏踏的声音回荡在走廊里。
柳眉之不知这样坐了多久,他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目光盯着石壁,神思却早已飞走。他一直在想,究竟是哪里出了错,让他栽了如此大的跟头。他在一年前终于如愿以偿被总坛晋升为北部堂主,统领北部上万的信众,即便近年几次受到朝廷打压,他们被迫转为地下,他还是干的风生水起,眼看他部署完便可离开京城,却在这个时候被抓住,七八年的努力付之东流,一切前功尽弃。
但是哪里出了差错?柳眉之此时的心情便如油煎火燎般苦不堪言。眼前突然模模糊糊浮出一个人影,柳眉之想到那日在虎口坡看见萧天,心里便一阵后怕,没想到自己的优柔寡断还是毁了自己,当初就该一剑了解了他,便不会有后面的变故。定是此人通告了官府,把自己逼入绝境,还夺走了明筝。
想到此,柳眉之又是满心的不甘。不过是一招落败,岂有满盘皆输的道理?即然进了诏狱,他坐在这里三天三夜苦思冥想,怎么对付宁骑城。但是等了三天,宁骑城这个大魔头一直没有露面,他心里没数,对这个人,他一向拿不准。他把他抓来,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他不得而知,但是他想脱身的念头,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点变得渺茫。
苦闷之极的柳眉之,面色似雪,眉宇间一片凄楚之色,他突然低吟起一段曲调:“……迢迢路不知是哪里?前途去,安身何处?一点点雨间着一行行凄惶泪,一阵阵风对着一声声愁和气……”
突然,旁边牢房传来击掌喝彩声。柳眉之突然顿住,甚是扫兴地大喝一声:“何人击掌?”
“同是圜土之人。”从墙外出来话音。
“于大人?”柳眉之想到刚才牢头口中所夸罪臣于谦,便问道。
“正是。”一墙之隔,于谦坐在草铺之上答道。
此间牢房与别处有一点不同,多了一张矮案,案几上放着一盏油灯。于谦正借昏暗的光读一本兵书,忽听得隔壁幽幽曲调,不由放下书细听,瞬间也已猜出是谁。
柳眉之入监时,他是知晓的。也从高健口中得知这位柳牌子的另一重身份,虽震惊,但也不无惋惜。他一路巡查进京,怎会不知民间疾苦,由此派生出各种名目的教门引诱信众,多打着佛祖之名,念佛持戒,可以往生,可以幸福,可见民间百姓对富足安康的向往和渴望。一路之上,他虽对州府的酷政有所矫正,但官官相护,积弊深重,岂是他一人之力可以扭转。
想到此,他不由对隔壁之人充满好奇。同样让他好奇的还有宁骑城对这位柳眉之的态度。一关数日,不闻不问,这个宁骑城打得是何主意?人字号牢房还从未这么平静过,记得月初押进来三人,都是朝中官员,也是与买卖试题有关联的,天天上大刑,整个牢里都充斥着鬼哭狼嚎的叫声,四天不到,三人都已半残,扔到地字号去了。
于谦正在若有所思之际,便听见隔壁说道:“于大人官誉清明,怎也落得如此下场?”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呀。”于谦道,“刚才听闻先生的曲调,不愧为长春院的头牌,听过仍是余音袅袅啊。”
“大人如此境地,竟仍有心听曲,心真是宽呀。”柳眉之平时最忌讳别人说他是长春院的头牌,一时恼羞成怒,便讥讽道。
“即是唱曲之人,不待在长春院,如何坐到了我对面?”于谦听出对方话中有刺,便也打趣道。
“说出来吓死你,”柳眉之不屑地仰头长叹,“天下不公,豪杰蜂起,胜则为王,败者成寇。这岂是你附庸朝堂之人所能明白的道理?”
“哈哈……”墙壁后的于谦朗声大笑,“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这岂是你贪慕私利之人所能明白的道理?”
柳眉之大怒,自小也是浸洇经文,岂有不知被于谦比作小人,便怒道:“你自诩是君子,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君子,会是个什么下场?”说完,话峰一转,又唱上了一曲,“……翠巍巍西山一带,碧澄澄寒波几派,深密烟林数簇,滴溜溜黄叶都飘败。一两阵风,三五声过雁哀。伤心对景愁无奈。回首家乡,珠泪满腮……”
“呵呵,你们挺会玩的……”走道上突然响起一个低沉阴森的嗓音。
柳眉之和于谦同时回头,只见宁骑城一身飞鱼朝服威风凛凛地走过来,身后跟着四名校尉,他身旁站着同样威风的千户高健。
“瞧瞧,一个唱曲,一个读书,拿我诏狱当养生堂了。”宁骑城阴阳怪气地道,他站在两个牢房中间,既可以看见柳眉之又可以看见于谦,连于谦手中书目都一目了然。
“大人,这个人犯于谦已在押两月有余,却仍未认罪。依下官之意,定要让他吃些苦头,让他好知道身在何处。”一个校尉走到宁骑城面前道。
高健猛地瞪了一眼这个校尉,差点骂出口。
“高千户,瞪什么眼呀?人家校尉说得甚是有理,为何不审?还给他一盏灯,这是你安排的吧?”宁骑城斜乜着高健,依然阴阳怪气地问道。
“是这样,大人,容下官回禀。”高健脑门上开始冒汗,他语无伦次地说道,“大人,下官听说,这个于大人,不是,是于犯,是个清官,家里除了几本破书,啥也没有,你想呀,大人,咱们劳神费力审了半天,跑他家一抄家,一堆破铺子烂套子,招人笑话不是。”
那个校尉还想争辩,谁知宁骑城哈哈大笑,道:“高千户说得有理,这种人懒得搭理。”
高健愣怔着望着宁骑城,额头上汗珠掉下来,他咽了口唾液,没想到如此牵强的说辞,也能蒙混过去。不过转念一想,他刚才说得虽然直白,却正中要害。以往经手的要犯,审后抄家,哪个不是金银满屋,抄家也抄的气势,朝中落银子,他们落名声。可是面对于谦,宁骑城似乎比自己更了解,一是于谦不贪不腐正直廉洁,二是官誉良好,深受百姓爱戴,所以他宁愿置之不理,也不招惹,真是聪明之极的做法,他不得不服。
此时,宁骑城走到柳眉之的牢房前,面对着铁栏栅,他双手抱臂饶有兴致地望着面壁而坐的柳眉之。
“你的原名叫李宵石,是罪臣原工部尚书李汉江的家奴,我没说错吧?”宁骑城语调一改往日狰狞,异常温和地说道,“你是长春院的头牌,又与我们高千户熟悉,高千户素来对你有好感,是不是高千户?”宁骑城转身眼神诙谐地看着高健。
“是呀,柳兄。”高健也有心助柳眉之,忙说道,“柳兄,只要你把知道的白莲会的事说清楚,大人不会为难你,真的。”高健回头叫狱卒,“来呀,拿笔墨来。”
这时,一名狱卒端来一个木托盘,上面有一支笔、墨盒和一卷宣纸。狱卒把这些东西从铁栏栅间送进去,便退了回去。柳眉之回过头,看也不看那些东西,他面色煞白,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但是头脑还是清晰的,一旦开口,死得更快。便缓缓说道:“你们休想,得到一字。”
“不要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一个校尉在一旁吼道。
“你做为白莲会的堂主,难道不想知道是谁出卖了你吗?”宁骑城依然不急不躁地说道。
这一句话显然击中了柳眉之的痛处,他脸上的肌肉一阵颤动,眼睛通红地瞪着宁骑城,他站起身,慢慢走向铁栏栅,问道:“是谁?”
柳眉之突然冲向前,抓住栏栅,大声吼道:“谁,你告诉我……”
宁骑城一阵狞笑,并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