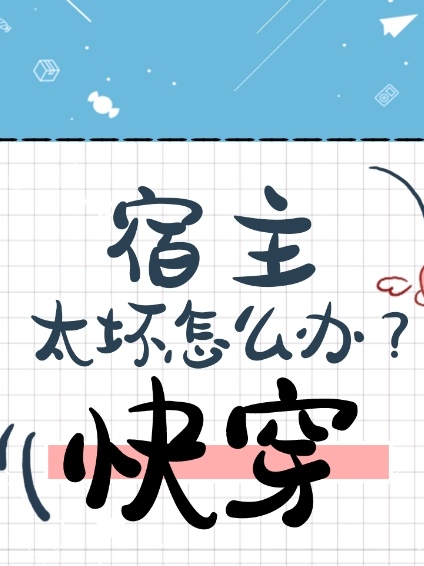第二天大家伙儿起了个大早,在大和尚的示意下从车里搬了些生活用品给西格,而后发动车子,向着碧罗雪山绝尘而去。
一路上的牧民和羊群越来越少,我们一行人望着道路两旁越发荒凉的土地心里一点儿底气没有。
这回也是走的匆忙,没有上街买些防蛇鼠的毒药,要是这会儿有一瓶,心里肯定安稳不少,倘若现在毫无对策的我们真的碰到那蚂蚁,怕是只有被追着跑的份儿。
车子行进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在江边儿上停了下来。
我盯着足有二十来米宽的江面微微愣神儿,左右顾盼之下,没船也没桥,难不成要游过去?
王修谨上前两步,往江边儿上靠了靠,那里有一丛高高的芦苇,这人犹豫都没犹豫,直接一头扎了进去。
没用多大会儿,他满身碎叶的钻了出来,对我们说道:“里面原先停过船,这会儿没了。”
大和尚点点头:“我上回来还有,怕是这帮孙子给虫子吓坏了,撤走了。”
光头一拍脑袋,质疑道:“这蚂蚁又不会划船,撤船作甚?!”
大和尚:“蚂蚁还不会吃人呢,吃了么?!”
光头不做声了,满肚子的疑问被他努努嘴憋了回去。
我:“只有这一条路么?”
大和尚的眉头皱成个八字,面色阴沉道:“这江叫独龙江,是个环儿,把独龙族驻地跟抱崽子似的抱在怀里,要想进去,必须从上面儿趟过去。”
我闻声一惊,敢情这还不是怒江,我一直以为这就是怒江之战里面的那条天险呢!
不过这也不是感叹的时候,我望了望那湍急的水面,就是个老水货也待不了几秒,压根儿不敢奢望自己的狗刨式能大放异彩。
书生点了根烟,望着芦苇丛沉吟了一下,“不然咱就自己扎个筏子好了,费点儿事儿但也比干耗着强。”
每个人的包里都有登山绳,尤其是张老七,他那儿工具齐全,大和尚看了看水流湍急的江面,当下也别无选择,只能无奈的点了点头。
黑子当即就拔出短刀钻进了芦苇丛,我和王修谨紧随其后,其余人负责将我们递上去的芦苇排列扎紧,折腾了近一个小时,这才算是有了点儿筏子的样儿。
大家合力把筏子放下水,保险起见,头一回还是没放装备,二大爷在腰间捆好安全绳儿,一个人以身犯险。
这是江流的上半段,河水湍急但却不深,二大爷撑着螺纹钢管接成的长杆左右撑水,缓缓向前。
出于承载力的考虑,筏子造的比较厚,因为大都是青芦苇,有些自重,吃水比较深,不过好处就是筏子更加稳定,加上二大爷手脚灵活,没一会儿就到了对岸。
他把腰间系着的登山绳解了下来,绕在河岸的怪石上,这么一来两岸之间就牵起了一道可以借力的绳索,这么一来,等他反身回来接我们的时候,另外的人就可以拉着绳索向前,能省不少力气。
过了江我们就到了碧罗雪山脚下,一番折腾下来大家也是耽误了不少时间,东边儿的太阳已经爬的老高,我们过江后也没了吃点儿东西的打算,就直奔着独龙族驻地而去。
应该是少有人涉足的原因,这一片儿的荒草疯长,足有半人高,草地里有些湿滑,我们的行进速度不算快,都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往里走,我心里惦记着那不知名的蚂蚁,所以走得格外小心,当草地越发泥泞,每一脚下陷得越来越深时,我是立马发现了不对头。
我把脚从泥地里拔出来,一双耐克鞋已经被黑泥完全覆盖,连商标都看不见了。
“这别是个沼泽吧!”
大和尚应该也是心存疑虑,当即就停住了,“特娘的,是这条路没错啊?!”
我撇了撇嘴:“独龙族的同胞总不能每次都趟泥出去吧,更何况你上回来都是三十年前的事儿了,三十年,村里的土路都变马路了,人家改道儿了也说不准。”
大和尚:“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一条路。”
王修谨抬头望了望不远处的雪山,指着抬起右手指了指,道:“村庄是在山前?”
大和尚顺着王修谨的眼神儿看了一眼,当即就明了了他心里的打算,“你想从山上翻过去?”
王修谨没说话,答案是肯定的。虽然要费力许多,但却能确保不会走错,虽然现在只知道大体位置,但只要我们上到山顶,肯定能发现村庄。
一直没开口的书生却摇了摇头,望向雪山的目光中满是顾虑,“翻过去起码要两天,就算从山腰绕,那也得一整天。”
六大爷的普通话一如既往的蹩脚:“上面儿不见得比地上好走。”
黑子挪到我身旁,“四哥,不然我走前面,你们用绳子拉着我,我给你们开道儿。”
我转头望望他,发现这人眼睛里似乎有着几分恳求的神色,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但是他也灵动,眼珠子左右一游,我就了然了,他这是想要在大伙儿面前表现表现。
一路上过来,除却我们小辈之间还有简短交涉,那些长辈几乎没有和黑子交流过,我明白他们对这个“外来户”存有戒心,而且还是颇重的那种。我没告诉黑子,光凭这样是没用的,想要真正的融入这个特殊群体,起码也得有过几回“同生共死”。
不过,他既然愿意表现,我也不好加以阻止,一般情况下,这种活儿都是二大爷包揽的,不过这回儿黑子主动请缨大家倒也没反对,就照着他的意思给他捆了根儿绳儿,让他上前探路。
黑子走在最前面,手里拄着螺纹钢管,腰间系着登山绳,绳子的另一头在我和王修谨手里,一点一点的往前放。
与我想象得差不多,泥地是越往里越泥泞的,绳子放到末端,黑子的小腿已经全部没入泥中,每走一步都要废很大的功夫。大部队在后面紧紧跟着,江染干脆把鞋脱了下来,晃晃荡荡的提在手里,赤脚在泥地里跋涉。
好在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度恶化,黑子在往前行进的过程中也没有继续下陷,大家的心里都安稳不少。
我拉着绳子抽空回头看了看,这里离岸边已经有了百来米的距离,倘若这湿地是因为江流灌溉,这么个距离也差不多了,然后一回头,就看见黑子一步踏下去,整个人都拔高了一截。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踩到了实地,但是这人却神色怪异的俯下身来,伸手往下掏了掏,从泥地里抠出个足球大小的泥弹子来。
黑子单手提着那泥弹子甩了甩,黑色的污泥飞溅开来,这下大家算是看清了那是个什么东西,一个人头。
黑子的两根手指就扣在人家眼眶里。
黑子明显是少见这玩意儿,吓得张手一甩,骷髅头就朝我们这边飞了过来。
那六大爷也是眼疾手快,一个欠身就把头骨接了下来。
大和尚瞟都没瞟六大爷手里的骷髅头,转脸对黑子说了句:“怕个球?就你这怂样还下墓?”
黑子这会儿还是惊魂未定,听到大和尚的话,脸上那叫一个雨雪交加。
我总感觉大和尚对黑子有些偏见,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挺正常的事儿,大和尚这么说让我有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感觉。
书生似乎也是觉得场面有些尴尬,当即给大和尚找了个动怒的理由,“黑子,逝者为大,下不为例。”
黑子听后像磕了药一般不住点头,他是知道大和尚的身份的,所以这理由找的倒也让人信服。
具体是不是,大和尚自己心里有数,应该是知道自己表现过激了一点,所以也就没再说啥,双手捧过六大爷手里的骷髅头,细细擦拭起来。
我在边儿上看着,头骨发灰,应该是埋在底下有些年头了,乍看之下到倒也没什么特殊,不过在我边儿上的王修谨却看得聚精会神。
最后,还是江染提醒我,示意我看那头骨的里面,我这才发现,在眼眶子和大张的嘴巴里面,好像有些细密的纹路,不像是汉字,也不是什么图画线条,倒像是随意而为。
二大爷也是发现了,两根奇长的手指伸进去一探,而后道:“齿痕。”
我一听,心说不会是那些蚂蚁造的吧,连忙从大和尚手里把骷髅头抢过,大和尚用一种灼人的眼神剜了我一眼,我心说差不多就行了,还真把自己当成普度众生的菩萨了。
骷髅头在手里来回反转,到最后,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除却表面,在骷髅头的内部,都是这种细密的齿痕!
这要是人体腐败以后蚂蚁进去啃食也就算了,可我这些日子以来见识的多了,就会不由自主的瞎想,这人别是被蚂蚁生吃了吧!
起初西格说过,那蚂蚁吃人,我想着茶碗大的蚂蚁顶多也就是啃啃骨间肉,可面前这人就要惨上许多,连脑子都被吃了个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