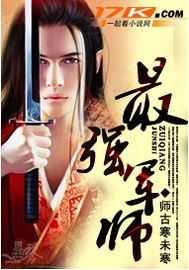一整条冗长而狭窄的东弄堂仅置了这一盏小马灯,很显然,它只能照亮全弄堂占比很小的一块区域。它被残忍地悬在一团杂乱无章地墙壁涂鸦正上方,乍眼望去,涂鸦的黑色线条与小马灯青黑的铁框相连,恍惚间竟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错觉。
微弱昏黄色的灯光忽明忽灭,伴着断断续续的穿堂风,这种莫名形成而又有失协调的节奏让燕炘宏感到很不舒服,只是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强迫症已然病入了这般田地。
燕炘宏有些后悔自己不该嘴贱,硬要和此时正走在前头领路的男同学开恶俗玩笑,不过也要怪这男生自个儿太较真,说起窑子还真就带他去逛窑子,满脑子的大条神经,让炘宏哭笑不得。他想象中闲适惬意的餐后散步就这样变了味儿。
东弄堂中段两侧开着无数个巷口,越往里走巷口越多,每个路口里几乎都透着紫红或橙红的灯光,并且不时传出女性带着浓厚方言的谈笑声,言辞中刻意的娇媚作到令炘宏阵阵反胃。
“就是这家店,我最熟,你去不去?”男同学的公鸭嗓刺耳得很,炘宏敏感地察觉到他语气里的不屑,这让他很不是滋味,于是并不抬眼看他,酝酿起和他类似的语气:
“哦?是吗?我才不信。你有种叫里头的人出来招呼你啊,我要听听她们会怎么称呼你。”他下意识地拨弄了两下刘海,扫视一番眼前这家打着“洗发店”招牌的小宾馆,翻了个白眼强装出一幅镇定并且不服的模样。
“切”男生漫不经心地吐出一个字,然而这字对于炘宏来讲,足以搅得他心神不宁,他或许说不明白这是种什么感觉,总之他的内心不断涌出糅杂着委屈、自怜与不甘的消极情绪,甚至让他窒息了片刻。
等他回过神来,男生早已把店里的“鸨妈妈”喊出来了,她看起来年龄并不大,一头炸开的棕黄色波浪卷发将她小麦色的皮肤衬得愈发暗沉,加上那身军绿色的紧身背心,单凭这上半身,炘宏就已被辣得不忍再看她半眼。
“鸨妈妈”对男生的种种言行举止已然证明了他常客的身份。炘宏没任何兴趣深究这些,只是无神地望着男生搂着“鸨妈妈”的肩,内心却五味陈杂。
他挥了挥手,又叹了口气,无奈地说:“好嘛好嘛,我服了你了。刘哥你最牛逼,行了吧。”接着还不忘嗤了一声,兴许是为了圆好这一整段表演。
“呵呵,叫你不信,怂了吧,那你来还是不来?”
“别恶心我了你,那你自己进去玩吧,好好享受,我才不陪,永别,傻逼!”炘宏就在男生的嘲笑声中用力地转过了身,为了显得更决绝。他的太阳穴嗡嗡作响,许是因为尴尬?紧张?还是别的什么。
他走出了东弄堂,身侧袭来的晚风吹乱了他刚理好的刘海,却起到了点儿提神醒脑的功效。
于是,他在这舒爽的氛围下开始了自我催眠式的反思,把内心的这份失落感,与自己初中时丢失了一支廉价钢笔时的那种失落进行了类比,最终似乎意料之外却情理之中地发现,两者貌似还挺像。
于是乎,刚才那位男同学,便成为了燕炘宏丢失的钢笔,与“主人”永别,然而“主人”也不会难过太久,至少燕炘宏是这样认为的。
侯克珏也经常这样说服自己,她发现,要是把自己每一任在心中的重量都看得很轻,这必定是最好的释怀途径。
然而,凭她这没心没肺的性子,自然是冒不出这么“高深”的思维方法。不过最起码,她身边还有这么个亦师亦友、心思缜密、堪称“大神”的最佳僚机——她的丈夫燕炘宏。
她自己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女性,结果居然还没有他一个男的懂女人心,这听起来像个段子,可事实就是如此。
侯克珏初二开始撩妹,自认为帅遍全中学,周围有一大波妹子可以左拥右抱。可谁不知道,妹子们仅是把她视作“蓝颜知己”,甚至不过是个“特殊”朋友罢了;她自己却不知道,还掏心掏肺地对她们好,骑车接送她们上学放学、主动帮她们搬书扛包裹拎袋子,无数次担下了本属于她们男友该做的事,最后不过是死皮赖脸地求抱、求亲、求甜言蜜语,说着跟玩儿似的,妹子们也就当作玩笑照做几次逗逗她,可惜她自己,每次倒都认真了。
“按你这么说,我从初二开始一直被忽悠到现在?”克珏猛然从沙发上爬起来,挠着头皱着眉问炘宏。
“你总不忽悠别人,别人不就来忽悠你吗。要怪就怪你自己没心眼,”炘宏挠了几下梨花的小肉爪子,梨花扭过头,眯着眼施舍般地瞥了炘宏一眼,接着就从他怀里跳到了地板上,一扭一扭地踱向墙角的那张猫抓板。
“这死猫!”炘宏起身骂道。
他看到克珏依旧一头雾水的模样,忍不住吐槽一句:“我总夸你单纯、天真,谁知道你是压根就没脑子。”
“我就是想不明白...她们也都对我挺好的的啊,虽然很多都拒绝了我的追求,可那并不算忽悠是我吧,而且性取向这东西我也不能强求对吧,你说......”
“别说了别说了,再听你说下去我的智商也要被拖下水。”炘宏虽说着不耐烦的话,语气却仍旧很平缓。
他走到沙发旁坐下,搭着克珏的肩膀,语重心长地教育道:“我的玉哥啊,作为你的‘谋士’以及最佳战友,我必须很负责地捍卫你的尊严,毕竟你自己完全不具备这种能力。好了,我不是说她们拒绝你的追求是忽悠你,而是想说,既然她们自己不弯并且知道你弯,还依旧要你帮她们做这做那的,这对你很不公平,我都替你不甘心,你觉得呢?”
“没呀,这又没什么,帮女孩子做点事儿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好歹我......”她顿住。
“你并不好歹,”炘宏像安抚一个孩子似的摸了摸克珏的西瓜头,“你是个吕孩子。”
克珏抿着嘴仿佛有些不情愿地用力点了点头,动作宛如一只啄米的鸡。沉默片刻,她突然坏笑了起来,而炘宏却没察觉,只是注视着电视里播放的美妆节目。
炘宏正专注着,不料左眼皮突然冒出一阵撕扯的痛楚,他“嗷嗷”地捂起眼,才发觉是克珏把他千辛万苦贴好的假睫毛连着双眼皮贴都给扯了下来。
“卧槽?!你有病吗?我他妈贴了半个小时才贴好了这一边!”
“哈哈哈哈!笑死老子了,别生气我逗你呢哈哈哈哈...只是想让你知道,你也是一个蓝孩子啊...哦不对!你现在,都应该是个蓝淫、大叔!”她感觉自己笑出了腹肌。
“妈的,”炘宏一头骂着、一头却也绷不住地笑了出来,“七日不打上房揭瓦啊,小伙子?敢造反了?”
说完,两人扭打在一起,笑声和骂声混杂交替,仿佛是一对恋人之间的亲密行为,连一旁的梨花都隐约感受到了一种被“虐喵”的错觉一样,趴在了猫抓板上,委屈地注视着沙发上厮打着的俩神经病。
至少,在他们结婚后的小半年里,两人都是真正快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