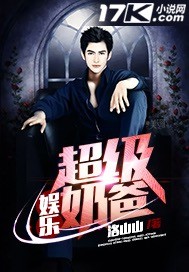卜大爷有了不祥的预感,三天来心总慌慌的。
闺女守茹出门子那日,原以为要有场痛快淋漓的哭闹,却没有,卜大爷便觉着怪。守茹走后,卜大爷要和仇三爷商量重开西城36家轿号的事,仇三爷又是一副很踌躇的样子,就更让卜大爷起疑了。他还以为仇三爷的踌躇是因信不过马二爷的承诺,便说,马二爷虽道不是东西,说话却是作数的。卜大爷要仇三爷把36家轿号的轿头管事都招来,一起合计合计,仇三爷这才说,还是先别急,待卜姑娘回门后一块合计吧!
这是啥话?卜大爷想,他的轿号和闺女有啥关系?
没想到还真有关系,且是大关系!他卜永安自己作孽,亲生闺女趁火打劫,把他这个当爹的卖了!仇三爷、麻五爷,可能还有马二爷,都参予了这场惨绝的扼杀,里里外外只瞒着挨杀的他。
回门时,院门口再次落下许多轿,有卜守茹从马家带来的,有麻五爷和麻五爷手下弟兄坐的,还有一乘八人抬的绿呢官轿,是空的——麻五爷进门就指着绿呢官轿吹:这可是好轿!连知府邓老大人都不摊坐的,他五爷一者有面子,二者又花了大价钱,才从退隐的巡抚大人府上借来了。
卜大爷问:“借来干啥?”
麻五爷大大咧咧说:“干啥?给你坐呀!你家守茹那真叫孝敬!昨儿个就和我说了,你为轿子苦了18年,身子骨全毁了,回乡咋着也得有乘风光的好轿!卜大爷,我可是真妒忌你呢,有这么好个闺女。”
卜大爷傻了眼,坐在堂屋太师椅上直着嗓子叫:“谁……谁说我要回……回乡?谁说的?”
卜守茹走到近前,冷面看着卜大爷:“爹,我说的。我还对五爷说了,你老这么累着,我做闺女的于心不忍,这西城36家轿号我就管了,你只管到乡下歇着享清福吧!”
卜大爷身子动着,手直颤:“妮儿,你……你可还是我的妮儿?”
卜守茹说:“这叫啥话?我咋不是你的妮儿呢?你对我的好处,咱石城82家轿号的人谁不知道?不因着你是我爹,对我好,我能让五爷费神弄这绿呢大轿?爹,你不是不知道,当皇上的命官也得当到五品才能坐这绿呢轿呢!”
卜大爷抓起八仙桌上的茶壶朝卜守茹摔过去:“你……你这贱货,你是要我死!”
卜守茹身子一闪,躲过了,茶壶在卜守茹脚下碎了,壶里有茶水,湿了地,也湿了卜守茹的粉红绣花鞋。卜守茹抬起脚,用绢帕揩着沾在鞋面上的茶叶片儿,又抬头瞅着卜大爷说:“爹,你真是不识好歹,你想想,我这么着不是为你好么?你今儿个败了能卖我,明儿个再败了可咋办呢?你可再没闺女卖了……”
卜大爷吼道:“老子不会再败了,不会!”
麻五爷插上来说:“卜大爷,话不好这么讲,不说你这人已是废了,不能再伺弄轿子,就算你没废,也不好说这大话的!”
卜大爷冲着麻五爷眼一瞪:“你他娘少管闲事!”
麻五爷笑了:“我可不愿管,偏是你找我管的!现在呢,你不让我管也不行了,我替卜姑娘做了主,就得管到底。我看了,你这闺女还就是比你这独眼龙强,有心计,也有能耐呢,五爷我都服气,你还不服?”
卜守茹道:“五爷,回乡下享福是好事,我爹知道的,你可别说这种话气我爹!”旋又对卜大爷说,“爹,打从我落生,你可是没回过家哩,我娘死时你没回,接我时也没回,只派了我巴哥哥和仇三爷。今儿个,你也该回了,看看我娘的坟,给我娘烧点纸,啊?”
卜大爷到这地步了,还心存妄想,恓惶地看着卜守茹说:“妮儿,我……我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我……我把轿号都给你,你别让我走,允我留在城里帮你的忙……”
卜守茹摇摇头道:“不必了,仇三爷会替我照管轿号的,他有腿,你没有,这没办法……”
卜大爷问仇三爷:“你能照看好西城36家轿号?”
仇三爷不敢看卜大爷,低着头说:“我……我不知道,卜姑娘让我管,我就得管,好歹都是你们卜家的人。”
卜大爷独眼里流出了泪:“好,好,你们早把圈套做好了,我知道。我……我不说别的了,只一条,你们让我留下来,任啥不管,让我能天天看到那些轿,成么?”
仇三爷瞥了卜守茹一眼,对卜大爷说:“这……这得问卜姑娘……”
卜大爷便对卜守茹道:“妮儿,你说句话!”
卜守茹一声不吭。
卜大爷这才知道自己完了,得带着他的一只独眼、两条断腿还乡了,他在城里18年的拼杀至此完结。而造成今日这局面的正是他自己,他生下了卜守茹这么个孽障,又把这孽障聘给了马二爷,极完整地铺排了自己的全面失败,连一点余地都没给自己留!
伴着一声绝望的嚎叫,卜大爷身子一挺,把八仙桌推开,冲着卜守茹扑了过去。
然而,今日的卜大爷已不是往日的卜大爷,那个用大脚板踩着麻石道和人拼命的卜大爷已不复存在,卜大爷的两条腿再也不能牢牢站在地上了,离开太师椅,卜大爷便轰然一声栽倒在方砖铺就的地上。
卜大爷倒在地上拖着鼻涕挂着泪骂:“卜守茹,你这个贱货!老子只要还剩一口气就……就和你没完!老子要把你,把……把……马二都宰了!都宰了……”
卜守茹不动气,看着卜大爷说:“爹,你咋骂也还是我爹,你不仁我得义;你不养我的小,我得养你的老。天不早了,咱得起轿了……”
卜大爷像没听见,直挺挺睡在地上,泼妇似地喊:“……都来看哟,都他娘来看哟,这就是养闺女的报应!闺女就是这么葬送她爹的啊……”
卜守茹这才火了,脚一跺,叫道:“你也闹得太不像话了!”转而又对麻五爷说:“五爷,快把我爹抬进轿去!”
麻五爷手一挥,院里站着的人过来两个,和麻五爷并卜守茹一起,硬把卜大爷架上了绿呢大轿。
卜大爷被扔进轿里了,还在骂,骂闺女,骂马二爷,也骂麻五爷和仇三爷。麻五爷被骂得心烦,就找了团裹脚的破布,要把卜大爷的嘴堵起来。卜守茹不让,说是挺好的事,别弄糟了。
起轿前,卜守茹张罗着一路上要带的东西——去一趟就80里地,吃的、用的都需不少,还有必不可少的盘缠。
正收拾着,卜大爷那边又出了鬼,这瘫子从轿里爬了出来,独眼亮得吓人,还狼一般地吼,说是要去见马二爷。麻五爷和仇三爷两人都按不住。
麻五爷说:“卜姑娘,得捆哩,嘴也得堵上,要不,走在路上太招眼。”
卜守茹迟疑了一下,道:“……手脖上缠点布片,别勒疼了他。还有堵嘴的物什得干净……”
麻五爷和手下的人找来麻绳和布,把卜大爷捆了,又给卜大爷堵了嘴,再次把卜大爷塞进轿里。
卜守茹待麻五爷弄好了,才撩着轿帘对卜大爷说:“爹,你可别恨我,我这也是没办法!我不能让你再呆在城里给我丢人现眼了!”
卜大爷被捆得肉粽子似的,嘴上又塞着布,啥也说不出,只能用那只独眼狠狠盯着闺女看。
卜大爷的眼光中充满疯狂和仇恨,让卜守茹至死难忘。
这时,又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
临走了,偏有人来找麻五爷,还带了个秀才模样的人来,秀才很年轻,手臂上有伤,不像跌破的,倒像洋枪打的。秀才要出城,说是绿营的官兵在追他。麻五爷便找卜守茹商量,要那秀才坐卜守茹的花轿出城。
卜守茹问:“那秀才是啥人?”
麻五爷支支吾吾不说。
卜守茹道:“你不说,咱就不带,一个爹已够我烦的了!”
麻五爷迫于无奈,才说:“这人是革命党,到咱城里运动刘协统的新军起事,被发现了,咱不救他,他就险了,闹不好得掉脑袋!”又说,“卜姑娘,你别怕,革命党的人我见得多了,并不都是奸人哩!”
卜守茹知道麻五爷的世面大,和啥人都有瓜葛,日后正好能帮她做事,便说:“我才不怕呢,举凡你五爷信得过的人,我自是信得过。”
那日是和革命党同坐着一乘四抬轿子出城的,革命党靠着轿子的左侧,卜守茹靠着轿子右侧;卜守茹盯着革命党看,革命党也盯着卜守茹看。这一来,卜守茹的心就慌慌的,不是怕被官府发现,而是怕自己会鬼使神差跟革命党走——那革命党是在官府缉拿告示上见到过,很像巴哥哥,只是比巴哥哥文气些。
革命党在轿子里说,南洋各处的革命党已纷纷起义,满人的朝廷长不了了。卜守茹点点头没作声,更没敢多打听。那当儿,卜守茹不知道这话对她未来生命的意义,只觉着这个革命党怪大胆的,敢说满人的朝廷长不了,听完也就忘了。
轿子出城二里,到了大禹山山腰上,革命党下了轿,和麻五爷拱手道别了,卜守茹才想到:她的巴哥哥哪去了?会不会也投了革命党?巴哥哥若是投革命党,是不是也要这般东躲西藏?
再上轿时,石城已被抛在身后了,回首望去一派朦胧,可卜守茹分明从那朦胧中看到了纵横交错、高高低低的麻石街路,那是父亲用血肉栽种过的庄稼地,如今轮到她来栽种了,她认定她能种好,能在那麻石街路上收获自己和父亲的双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