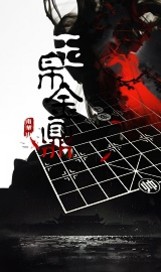南宫玄的黑暗故事讲完了。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一时之间,又没有任何人能提出异议。包括这个故事的主角梦遗大师。
梦遗大师又恢复了闭目养神的淡然模样。那副招牌苦瓜面相,与平常毫无二致。没有人知道,这个关于他自己的阴毒故事,是否在他心里激起了一丝波澜。他自始至终不说话,不知道是默认故事情节的真实性,还是根本就不屑一顾。别人甚至无从知道,他究竟有没有认真听完这个故事。
南宫玄并不是个讲故事的能手。他的天赋并不在嘴巴上。我估计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一次性说过这么多的话。他说得的点急迫,似乎怕故事像掌心的细沙一样,会在风中逐渐飘散。也许是,他害怕自己命不长久,没有足够时间说完这个时间跨度几十年的故事。
他刻意把故事埋藏了几十年,现在却惟恐故事细节不能大白于天下。
除了因为急迫而显得嗓门较高,且音调不平稳,南宫玄的遣词造句也相当零乱。上一章的故事,经过了我整理。算是间接引语,但详略和逻辑次序,基本保持了原样。当然,对在场的听众而言,不需别人刻意整理,也能基本抓住主要脉络。主要是因为,此前我说了太多的废话进行铺垫,先入为主地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故事的大致轮廓和方向。
南宫玄讲完之后,并没有去观察别人的反应。连梦遗大师脸上的表情,他也懒得去看一眼。他只是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然后也学着梦遗大师的样子,闭目养神。
少林武当的所有徒众们,不但提不出异议,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南宫玄的脸上,巴望他在换气之后,继续补充更多的八卦细节。这一刻,他们表现出难得一见的耐心,成为相当合格的倾听者。
我自己也提不出任何异议。但我不习惯于假装低眉顺眼的沉思。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良好的思考者,更多的时候,我喜欢嘈杂不休的争论。从人们急扯白脸和言不由衷的话语中,我总有本事获得一些语言之外的信息。察言观色是我的强项,过滤语言信息也是我的强项。
这一刻,我的目光游移不定。从这一群人脸上,到另一群人脸上,我看尽了人情百态。
除了我自己,还有另外一个人目光也是游移不定。此人就是无厘道长。
无厘道长的目光,从南宫玄脸上,移到梦遗大师脸上,最后在少林武当徒众脸上停留了很长时间。
李开心不假装思考。但他的目光并不游移,他只盯着梦遗大师一个人。虽然我认为,从梦遗大师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什么门道。
朱玲和叶欣不看别人,两双大眼睛一下不眨地瞪着我。很显然她们希望我说点什么,可惜的是,我让她们失望了。这一刻,我同样无话可说。
全场上百号人,就这么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寂静。场面有点滑稽,还有点恐怖。这么多人不说话,除了极少数目光的移动,大家连基本的手势都没有,看上去就是突然被施了魔法。
说真心话,我很难忍受这种人多而又无语的场景。所幸的是,寂静最终还是被一个人打破了,否则,我很可能会发疯。不发疯也会发火,乃至对在场所有人发飙。
第一个打破寂静的人就是阿红。客观地说,她才是全场最有资格对故事提出反驳的人。如果连她都以沉默认可故事的真实性,大家只好继续无话可说。
阿红没去审视讲故事的南宫玄,也没去观察故事的主角梦遗大师。她像朱玲和叶欣一样,只盯着我的脸,目光一直没离开过,似乎从我的脸上能看出几十年前的故事真相。而实际上,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
阿红摇了摇头,吃力地说出几个字:
“这不可能。”
声音不高,但大家都听到了她的反驳。同样,大家都跟我一样,感觉到了她的反驳之语是如此的软弱无力。
阿红见没人接茬,尤其是连我都不帮腔,眼睛发红,嘴巴一扁,快要哭了。她接着说:
“我娘说,她爹娘在她出生不久就死了。”
这话说服力更弱。只不过,这一回有人接茬了。
接话的人是南宫玄。无论是谁在反驳,最有资格接话的人,只能是他。他睁开双眼,并不看向阿红,目光焦点在不远处的一个火把上。
南宫玄笑了笑道:“小姑娘,你娘连你爹是谁都不向你明言,又怎么可能讲述她自己爹娘的阴毒过去?母女同时遭到父亲的杀戮,自古以来绝无仅,这对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来说,无异于到最底层最黑暗的地狱地走过一遭,没人能形容她受到什么程度的惊吓。她没有崩溃而能沉默地活着,并且后来还生下你,本身就是个奇迹。”
阿红的再次反抗有点语无伦次,声嘶力竭地喊道:
“反正,反正我不相信你的鬼话。”
南宫玄淡淡地说:“你娘左上腹,离肋骨大约三寸之处,有一道伤疤,直通后背。”
阿红终于没有忍住眼泪,依旧语无伦次:“你怎么?你怎么知道?”
南宫玄:“你娘的这道伤疤,世上除了她自己,只有你、我、上官飞鹰知道。”
他故意顿了顿才接着说:“当然,还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你的外公,少林寺得道高僧——梦遗大师。”
阿红泪流满面,已经无法可说。
我也无法可说,旁边所有人都无话可说。
当然了,所有人无话可说的境况,这次持续的时间很短。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尚未在心里完全消化南宫玄的举证,便有一个人提出质疑了。
此人就是无厘道长,他的接话,看似令人意外,因为此刻话题并未涉及他,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实际并不算意外,在场之人,头脑运转得如此之快的,并不多见,而能迅速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提出质疑的,则是绝无仅有。除无厘道长之外,没别人具备这份本事。
无厘道长冷冷地哼了一声:“二十六年前的所谓凶杀案,基本是你自说自话,举不出任何旁证,压根不可信。而这个小姑娘,几乎没人知道其来历底细,谁能排除,那不是你们事先商量好的一场双簧戏?找个陌生人混淆视听,在江湖上并不算新鲜花样。”
如果在平常,我可能会是第一个站出来,对无厘道长大加嘲讽与反击。但我此时依旧无话可说。二十多年的事情,我一无所知;阿红的家族背景,我同样一无所知。无厘道长的质疑,听起来有点强词夺理,细想似乎也不无道理。
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杀妻杀女罪行,按南宫玄的说法,现场前后总共涉及四个人,只死了一个,另外三个活着,一个是行凶者梦遗大师,一个是幸存者小女孩,最后一个是目击者南宫玄自己。现在的情况是,幸存者最有资格作证,她却并不在场,如今是否在世尚存疑;梦遗大师保持沉默,假如将沉默理解为一种反抗,那么,要认为剩下的南宫玄是自说自话,完全解释得通。
当然了,此事严格来说还涉及第五个人,上官飞鹰。但他并没见到事情的全过程,只是偶然救了那位没被杀死的小女孩。事后小女孩有没有勇气向上官飞鹰讲述前因后果,也是个问题。超过极限的伤心痛苦之事,大多数人会永久埋藏,甚至选择彻底遗忘,否则根本无法活下去。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上官飞鹰知道的,很可能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最后,即便上官飞鹰所知,与南宫玄的所述完全重合,也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前者已经死了。
再说阿红方面。南宫玄的举证是,阿红的母亲腹部有道伤疤,以此证明,其母就是当年被梦遗大师一剑刺穿未死的女儿,而阿红就是梦遗大师的外孙女。但此事同样问题重重。
所谓腹部伤疤,除了叙述者南宫玄自己,世上见过的不外乎三个人:女儿阿红,丈夫或情人上官飞鹰,当年的行凶者梦遗大师。现在上官飞鹰已死,无法作证,梦遗大师很可能继续保持沉默。最后一个阿红,如果认为她受到南宫玄的胁迫演双簧戏,那么此事就真的可以从法理上完全推翻。
再强词夺理一点,即便阿红之母身上真有伤疤,谁能证明,那就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留下的?这世上腹部有伤疤的人,并不少见。
无厘道长的质疑,连南宫玄都无法反驳,我就更无能为力了。所幸的是,周围的徒众们,没人附和他的说法。也许是,他们的情绪被南宫玄的黑暗凶杀故事所感染,一时之间无法自拔;还有可能是,他们的思维没跟上无厘道长的节奏。
南宫玄无法反驳无厘道长,于是他不反驳,转守为攻,冷笑一声道:
“牛鼻子老道,别像你那位师弟一样无聊,什么事都急于插嘴。还没轮到你呢,趁着高尚的面具还没撕下,多享受一会道德楷模的感觉吧。放心,马上就到你露出丑恶面目了。”
无厘道长努力保持淡定,此刻,他不淡定事实上也没别的办法。他刚要再次出言,另一个人抢在他前面说话了。
说话者是梦遗大师。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睁开了眼,更没人知道,他为何忽然泪流满面。皱纹还是那些皱纹,苦瓜脸还是那张苦瓜脸,只是在火光下,苦瓜脸上的皱纹里,多了很多浑浊的泪水,像有人泼了他一脸泥浆。
梦遗大师双眼无神地看着我的方向,只说了一句简短的话:
“孩子,你过来。”
这话有点莫名其妙。但我相信,在场所有人都知道,他此话是对阿红说的;在场所有人也明白,他此话算是亲口承认了许多年前的罪恶。
这一刻,针对此事所有的质疑与反驳,都失去了意义。
无厘道长正打算说出口的讥讽之语或强词夺理,只好硬生生地咽回去。南宫玄吃了一惊,转头看向 梦遗大师,似乎根本没想到对方会说出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在场所有人当中,最为惊慌失措的,莫过于阿红。她平常也算个伶牙利齿的女孩,此刻却说不了一句完整话。她不看别人,只盯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我,王大哥……我不,我?”
没人知道她想表达什么。只有我清楚,她在向我无力地求助。
我努力前倾,双手搭在她肩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去吧,此人真的是你外公。放心,没事,有我呢,听听他想说什么。”
我也失去了平时的语言强势,话说得磕磕巴巴,而且言不及义。
阿红犹豫了很久,费了很大的劲,才站起身。过程中,我的双手从她的双肩,顺着胳膊慢慢下滑,最后四只手掌分别握在一起。我最后朝她点点头,松开手,她才勉强转身,步履维艰地朝梦遗大师走去。
百十号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她身上。
阿红将头摆得很低,下巴顶在胸前,双眼盯着自己脚尖,以此躲避众人的目光。我这才看清,她穿的是一件天蓝色连体长裙,束腰,头发散开长及腰带,背影显得纤细瘦长,有一股惹人怜爱的懦弱。她双手交叉于下腹,身体移动缓慢,犹如水下行走,摇摇摆摆,力不从心。
梦遗大师的视线,一直不离阿红的脸面。也许他在寻找当年妻子和女儿的痕迹。我不知道他找到了多少。我能看到的是,整个过程中,他泪如泉涌。很难相信一个老年人会有那么多的眼泪,就像一生的泪水集中在这一刻倾泄而出。
阿红的脚步诚然很慢,最终还是到达了梦遗大师的身前两步开外。她停下来,又一次不知所措。梦遗大师仰起头,朝她惨然一笑,又伸手向她摆了摆,示意她坐到地上。
阿红犹豫了一会,慢慢放低身子坐下来,刚着地,又警惕地向后挪了半尺距离。
梦遗大师再次笑了笑,张嘴要说话,却猛然喷出一口鲜血!
鲜血像一道红色剑光,射在阿红脚尖上,染红了裙子下摆。阿红尖叫一声,身子不由自主后倒,最后终右肘撑地,呈半躺姿势。尖叫之后又没了声音,她吓懵了。
梦遗大师待鲜血喷完,再想说话时,嘴巴却无力张开。脑袋朝肩头一歪,保持着一副苦瓜笑脸,慢慢闭上了眼睛。
梦遗大师什么话都来不及说,便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