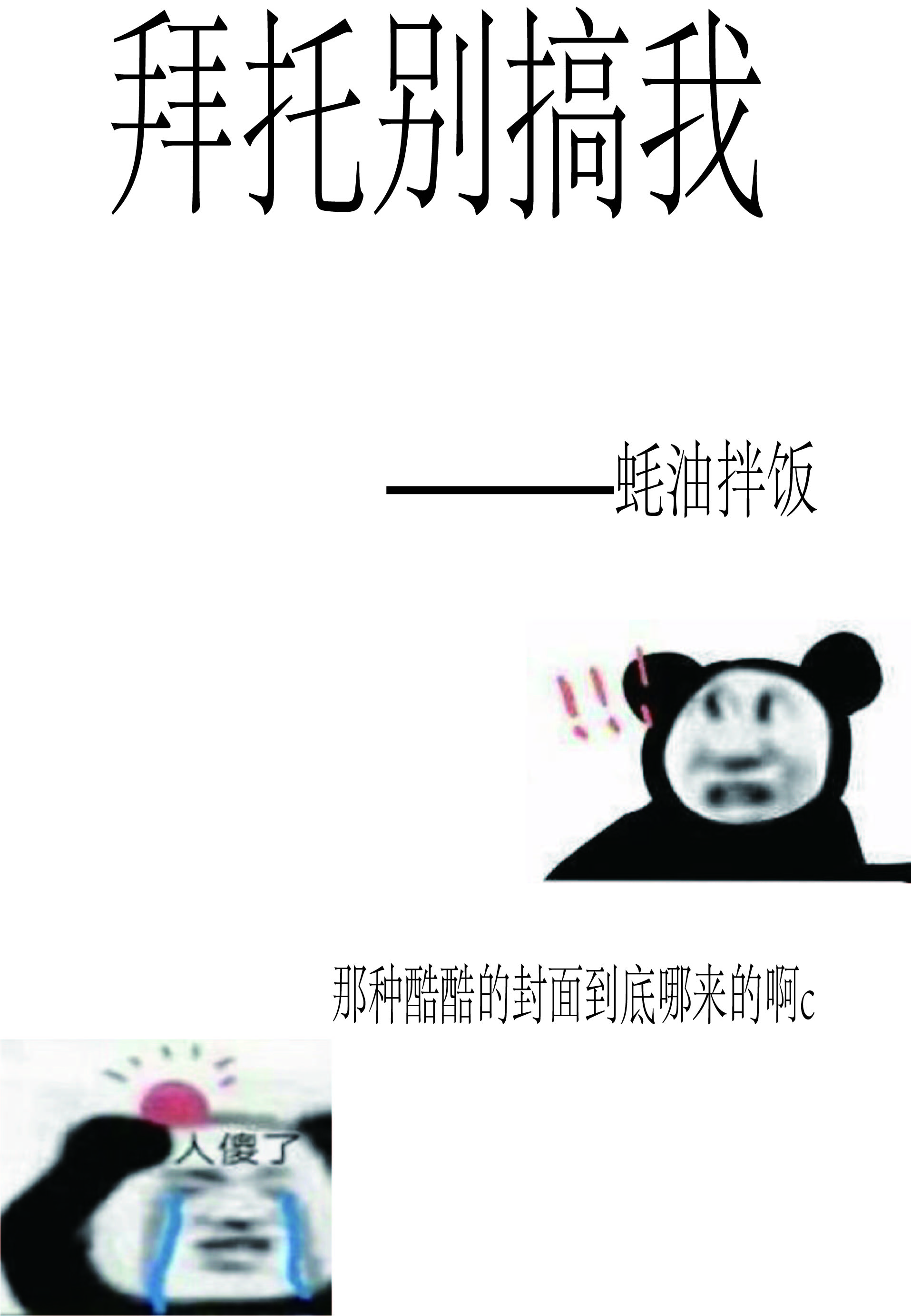这一年的六月,何夕生接了一部戏,《星野奇缘》。
为了这部戏,夕生和经纪人林双闹了不愉快。夕生不肯接,林双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直接掐了电话。
何夕生看着窗外发了会呆。傍晚,大片晚霞流连,映得天空彤红。
他不够红。完成上一部戏,夕生有三个月没进组了。林双没有明说,夕生也能猜到,他眼下接戏处境尴尬。
二十九岁的何夕生从电影学院毕业六年。六年风云变幻,上一茬是“艺术家”,下一茬是“小鲜肉”,何夕生卡在中间。
既没有代表作和含金奖项,又没人气没人捧。肯请他的戏拍了难卖,好卖的戏又不肯请他。这就是他的处境。
夕生打开橱柜拿出剩半瓶的野格酒,注进玻璃杯。他很少喝酒,除非烦透了。握着玻璃杯坐在高椅上,玻璃杯壁慢慢结了霜气,夕生喝了一口,冰得正好。
何夕生三岁上幼儿园,小朋友排队洗手,轮到他了,夕生把水凝成冰块,捧在小手里给老师看。老师吓得当场给他妈妈打电话。
妈妈何亦竹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地方戏演员。她赶到幼儿园接回夕生,抱着他呆呆看了会,红了眼眶说:“我怎么养了个小怪物。”
何亦竹没有结婚,夕生是她收养的。抱到手里时刚刚满月,长得雪白粉嫩,两只溜溜发亮的大眼睛。
何亦竹当他亲生的,尽心尽力把夕生养大。幼儿园事件之前,何亦竹已经发现他奇怪,夕生没有眼泪。
婴儿没有眼泪尚能理解。夕生三岁了,不如意了哇哇大哭,嚎得再凶,只是没有眼泪。
何亦竹嘴上不说,心里犯嘀咕,领着夕生去看医生。挂号看诊检查一天跑下来,医生慢条斯理说:“这孩子很正常啊,泪腺是通的。”
何亦竹问怎么办,医生也没办法,说:“观察观察,有情况再来吧。"最后安慰道:“除了没眼泪,别的都正常。小孩子健康就行了,不要太在意。”
何亦竹只得作罢。
可这一次,她没敢上医院,悄悄办了退园手续,不让夕生上学了。何亦竹观察良久,夕生除了凝水作冰和没有眼泪,其它和正常孩子一样,体检各项指标无异,何亦竹渐渐放了心。
她很喜欢夕生。一手带大的,就是小狗也有感情,何况夕生活泼可爱。何亦竹不敢让他上学,带着他混戏班剧院。
混到十岁,夕生能控制着不当众施展本领,何亦竹把他送进戏曲艺校,学武生。
夕生在艺校如鱼得水。俯卧撑别人做50个,他能做200个。倒立人家坚持三小时,他能坚持七小时。翻跟头更不必提了,侧手翻、空翻、转体、团身,夕生的跟头又高又飘,落地极稳,从未失过手。
夕生因此倍受喜爱,带他的张师傅当他半个儿子。磋砣到十九岁,张师傅怂恿他投考电影学院,又劝何亦竹:“孩子大了,总要谋个前程,难道在小县城窝一辈子?夕生聪明有天份,长得又好,可别耽误了他。”
何亦竹想了几天同意了。母子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除了唱戏,夕生是何亦竹唯一的寄托。她希望夕生考上,又盼着他考不上,心情复杂陪了夕生去了北京。
夕生一次中的,顺利考上了。
喜讯传到戏曲艺校,张师傅呵呵乐,有晚上喝着小酒跟人吹牛:“何夕生以后能是大明星!”酒友问为啥,张师傅神秘道:“他眼珠子是绿色的,舞台上瞧不出,镜头底下夺人!”
这话传进何亦竹耳朵里,何亦竹吓一跳。她本已安置了夕生赶回家乡,这又买了票上北京,逛了大半天王府井,买了当时刚流行的“美瞳”,选了纯黑色,巴巴赶到学校塞给夕生,叮嘱他把本事都藏好,千万别让人当怪物看。
眼下何亦竹唱不动戏了,接了张师傅的班带孩子,竟比夕生还忙碌些。夕生的片酬大半都汇给何亦竹,叫她买房买车。何亦竹吃住在艺校,哪用得上房和车。她把钱都存好,准备给夕生娶媳妇。
夕生的烦恼从不告诉她,打电话回去都是开心愉悦的。他知道妈妈不是亲生的,越这样,越是感激,不肯叫她烦心。
妈妈不在意夕生红不红,只怕他的怪本事叫人发现。每打电话必叮咛,要记得戴美瞳。
夕生总不能傻到当众表演异能,至于眼睛嘛,他自己瞧着并不发绿,因而美瞳时戴时不戴。
门铃叮里咚咙乱响。
这样敲门只有一个人。果然夕生拉开门,周泉鬼崇崇挤进来:“快让我进去,别给人看见。”
夕生让他钻进来,刚带妥门,就听着周泉大惊小怪:“野格没兑红牛啊,难喝死了,呸,呸!”夕生走去夺了杯子:“请你喝了吗?”
周泉苦着脸:“我就不明白,你干嘛喜欢这个味,跟藿香正气水似的。”夕生慢悠悠喝一口:“你懂什么,这叫药草香。”周泉把宝贝相机小心放在沙发上,开柜子找矿泉水说:“你接了星野啊?”
周泉是夕生戏曲艺校的同学,十岁起摸爬滚打有难同当。夕生上了电演学院,周泉也不甘示弱来了北京,连考三年名落孙山。
他认命不当演员,却不肯再回县城,七混八混,跟着爆料王当了狗仔。近年爆料王名声显赫,爆出的明星丑闻不计其数,周泉混得风生水起。
夕生和周泉人前装不认识,人后铁得穿一条裤子。
“你消息够快的啊,我还没签呢!”夕生瞪他一眼说。周泉笑道:“这行哪有不透风的墙。”又说:“赵梓亮是男主角,你不肯接吧。”
夕生不说话,手里的杯子又起了冰霜。他不肯接《星野奇缘》,正为了赵梓亮。
他有过大红的机会。四年前,余阳工作室投拍古装剧《莲荷曲》,选了夕生演情深不寿的男二号。《莲荷曲》大爆,夕生红遍街头巷尾,风头盖过男主赵梓亮。
余阳算得上夕生的“伯乐”。《莲荷曲》海选时,夕生毕业刚两年,没公司也没经纪人,靠着老师同学推荐,跑剧组演龙套。他投简历试男主的仆从,面试时余阳在,相中夕生演男二号。
角色火了,余阳就和夕生谈签约。夕生正在风头上,几家大公司都伸出橄榄枝,其中就有他梦寐以求的正德影业。
正德影业主攻电影市场,夕生没背景,根基浅,票房没保证,进了正德也演不了男主。一部电影几个镜头,不如电视剧攒眼缘。
夕生于是推了正德,答应签给余阳。
第二天签约,头天晚上大学同学纪若风邀他小聚。夕生欣然赴约。纪若风请了不少人,欣赏夕生的表演课老师孟铎也在座。孟铎喝多了,指了夕生道:“我早就说过,你们这一届,能出息的就是他!”
满座应和,然而笑容尴尬。校园里是同学,出了校门是同行,同行就是冤家。夕生赶紧拦着孟铎:“孟老师,您喝多了,我陪您去抽根烟?”
孟铎一推他:“别打岔!”接了又说:“夕生的古装论第二,没人敢论第一,戏曲艺校的底子搁在那!”纪若风笑道:“这是真的!外头怎么说的,说夕生的扮相神韵天成,眉目含情,是为戏而生的!”
夕生恨不能找个洞钻了。孟铎却道:“夕生的眉眼那是绝了,你们发现没,他的瞳孔是绿色的!”纪若风讶异:“我睡他上铺四年,没发现啊!”说着扑过来扒夕生的眼睛:“我看看,绿不绿,哪里绿了?”
夕生躲了又躲,一片哄闹里,他赶紧溜出包间。大厅清静多了,夕生点了烟站在门口。纪若风追出来,拍他肩道:“没事吧?”
夕生摇头递上烟,纪若风点上说:“听说你推了正德。”夕生点头:“大公司不好混。”纪若风由衷道:“我毕业就签了正德,白晾两年。应该学你,自己找机会。”
夕生笑道:“签余阳好了,他的戏热。”纪若风拐拐他道:“我可听说,余阳对男演员特别有兴趣。”
喝了酒,又是四年同窗,上下铺的兄弟,夕生就没设防,说了些业内的笑话,大多是关于余阳的,听得纪若风又笑又叹。
当晚尽兴而归。第二天,夕生按约定去签约,却找不到余阳了,签约也不再提起。夕生打听了好久,跟进签约的小金说:“何老师,您可别说是我说的,余老板生你气了。”
夕生愣道:“我做什么了?”小金道:“他说您到处乱传,说他私生活混乱。说您还没大红大紫呢,就不上路子了。”
夕生倒抽一口凉气,转脸就给纪若风打电话。纪若风也诚实,承认是他说的。夕生想这同窗情是没了。纪若风最后说:“夕生,你别怪我。赵梓亮答应我,余阳不签你,他保定了能签我。”
他后来哪家公司也没签成。流言忽然在业内传扬,说何夕生演哭戏全靠眼药水,不敬业。
夕生最后签了小经纪公司,跟了林双。四年,他总是演配角,痴情的苦情的腹黑的阴险的,他的好前程像水里肉骨头的影,一晃,踪影全无。
周泉推他道:“哎,哎,别冰了,再冰杯子碎了!”夕生恍然回过神,立即松了手。知道他有这异能的,除了何亦竹,就是周泉了。
周泉把矿泉水塞他手里:“这个,给我冰冰。”夕生没好气的丢开,周泉笑道:“我劝你接了星野吧,林双嗑这部戏不易!”夕生问:“你又知道什么?”
周泉点了根烟说:“星野未拍先热,女主角是欧小山,选秀出道的那个,眼下火得一塌糊涂。导演卓妙不必说了,有才华。出品方鼎星传媒,电视台买片首选他家!”
夕生道:“这样的好戏能轮上我?”周泉笑道:“正常是轮不上的。我听说啊,鼎星有一部青春题材,想请英寒!”
英寒是林双用综艺带红的“小鲜肉”,不是科班,也谈不上会演戏,就是红,莫明其妙的红。
周泉道:“鼎星找上门谈英寒,林双开了个天价,鼎星当然不干,林双就把价压了,但是提了条件,要给你上一部戏,要求不高,主演就行!”
夕生一笑,周泉急道:“你别不信啊!鼎星给出星野,是因为卓妙!”“卓妙?”“卓妙的才华出了名,臭脾气也出了名。男女主角他要听资方的,可男二号挑花眼都定不下来!鼎星把烫山芋丢给林双,能搞定让她搞,搞不定是卓妙难缠,和鼎星无关!”
夕生静听着,周泉神秘道:“我总觉得啊,你这人命不一样,你是不是什么,什么东西下凡啊,总比凡人运气好些?”
夕生踹他道:“接着说啊!”周泉嘿嘿笑道:“你的照片送过去,卓导瞄一眼就定下了,就是你了!”夕生呆了呆:“我没上过他的戏啊。”
周泉嘬着烟说:“所以说你运气好。这都是江哥告诉我的,他跟这个组。”
他说的江哥是江栋,做执行导演,也做演员导演。周泉在横店误打误撞拍着个男艺人约炮粉丝,江栋受托公关,找到周泉。
周泉忍着不上独家,一分钱没要,替他给瞒了。
从此江栋认周泉是兄弟,无话不谈。
夕生不说话,把杯里的野格一饮而尽。周泉戳他道:“签了吧,林姐对你是真没话说。赵梓亮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啊?”
夕生冷笑道:“他比老虎阴损多了。”周泉做个手势:“你冰他啊!”夕生被逗得笑了,周泉道:“剧组设在丽江,都集结了,我也要去呢。”
夕生侧脸问:“你去干嘛!哦,赵梓亮和欧小山!”周泉满意点头:“对头!”夕生道:“他俩真在一起啊?”
周泉笑道:“五分真五分假,谁知道呢。总之是放出来的消息,他们不给料,我们上哪拍去。”
他掐灭烟头道:“这戏真不错,自带热度。你上去咔咔一演,没准跟四年前似的,又红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