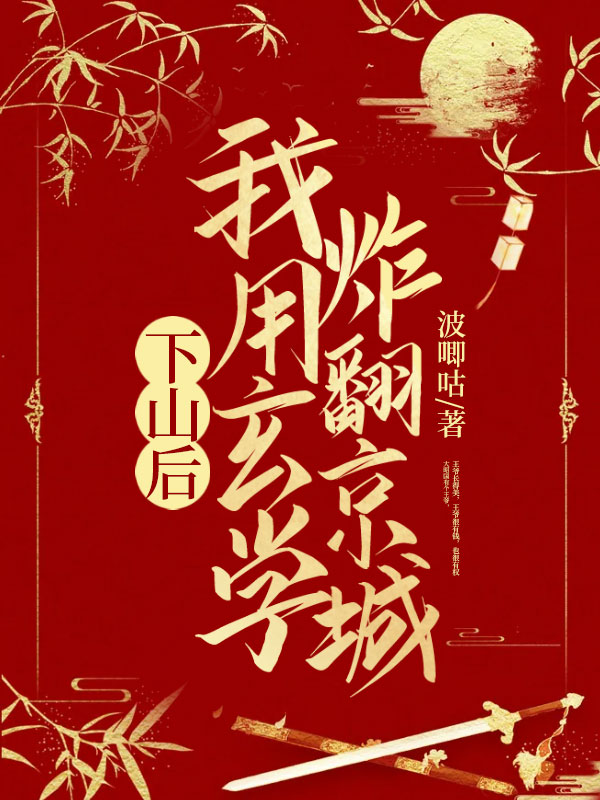众人各归其所,一时相安无事。刘鼎、黄贞在一起相叙兄妹别后重逢之情,黄巢便引了王荆畅谈。
黄巢的房间就在大将军行辕东面的地方。黄巢似乎是接风宴上没有来得及痛饮,便在房间里又摆上了一桌。桌前只有黄巢、王荆他们两个,分宾主坐下。
黄巢先开口道:“当年老夫尚且年幼,曾与令师敬囊青先生有些渊源。我总共去过两趟五禽谷,上一次去时距今已有二十年了。那一次便见着了你,才不过七八岁而已。如今老夫举兵反唐,战事一起,枪箭无眼,军中若没有神医圣手,麾下子弟怕是死伤难防,这才劳烦王贤侄走这一遭。”
王荆道:“师父倒是常提到黄公之名,他知道如今天下大乱,便让我出谷救世。既然黄公屈尊来请,侄儿又安敢不从?”
黄巢听得这话,自然大喜。
两人边谈便饮,酒过三巡,黄巢想起西楚霸王,触及心事,便拉着王荆的手,感慨道:“想当年项籍带了三千江东子弟,横扫天下,何等威风?可最后竟无一生还,又何其悲哉?老夫这八千曹州儿郎,以后还要全赖贤侄保全。”
王荆听了这话,也不禁动容,郑重回道:“侄儿自当尽力。”
黄巢才送走王荆,夜已深沉。此时又一人来访,竟是沙陀李克用。
李克用进得门来,先一礼道:“沙陀李克用深夜前来叨扰黄公,万望勿怪。”
黄巢不知这‘李鸦儿’半夜寻他,所为何事,笑道:“李留后肯来此地,自该远迎,倒是老夫失了礼数。”
两人坐下复饮。李克用不肯直言来意,他要试一试黄巢的胸襟抱负,便问道:“黄公以为孙仲谋比其父兄如何?”
黄巢生性洒脱,不耻孙权为人,便冷笑道:“人皆道孙仲谋乱世英雄,老夫却深不以为然。其比父兄逊色多矣,虽守成有余,然开拓不足。”
李克用闻此乖论僻说,心底吃惊,面上却不动声色,又问道:“哦,何以见得?”
黄巢杯酒下肚,畅然回道:“昔日关云长以半州之力,围困襄樊,水淹七军,致使于禁被擒,曹仁几近弃城而逃。那于禁、曹仁是何等人物?于禁乃是曹孟德麾下五子之首,外姓的第一将;曹仁更是有着‘天人之勇’的名头。这俩人都为关云长所败,使得曹孟德震恐非常,几欲迁都以避其锋芒。后来曹孟德被司马仲达劝下,便先后派遣徐晃、徐商、吕建、张辽诸将驰援,自己又亲率大军出兵洛阳。如此一来,曹魏东边防线便无比空虚。那孙权曾多次打不下合肥,得此良机,他竟不取合肥,直上青、徐,辄取兖、冀。若如此,无论曹刘胜负,他便可得一半天下。只可惜孙权、吕蒙鼠目寸光,只想着荆州半郡之地。纵然后来得了荆州,却无力抵抗曹军,任其冲突,委实可笑至极!”
黄巢一口气说了许多,批判古人,激扬战事,把他心中见地都表了出来。
李克用听罢早已在心中掀起轩然巨波,拍掌大笑道:“黄公果是大豪杰、大英雄,远非寻常之人可比。世间对孙权多有褒论,一个个谈古评今,笔舌生花,称其能胜过父兄,可媲美曹刘。所谓高见,不过尔尔。那见识哪里比得上黄公毫厘?在下斗胆,也与黄公所见略同。孙权如得东面半壁江山,尚能与曹刘一决雌雄。当时曹刘必然两败俱伤,他本可坐收渔翁之利。可笑他只想三分天下,苟全于东南,却是平白糟践了鲁子敬的《榻上策》。”
两人志趣相投,言酒两欢。李克用忽正色道:“若黄公有孙权那等机会,该当如何?”
黄巢一杯饮尽,豪气陡生,笑道:“自然是先取了那一半江山。”
李克用叹道:“黄公有此胸襟志向,李某钦佩。只可惜王大将军要做那孙权哩!”
黄巢疑惑道:“此话怎讲?”
李克用便道:“我此番远奔曹州,便是为了与草军结盟。希望草军挥师南下,侵扰李唐半壁江山,在下却耀兵西北,令其不能兼顾。不料王大将军无意江南,只想着做那齐桓公。”
黄巢听罢,心中已然十分震惊,“虽然沙陀乃是外族,他李家父子又素有反心,可如今毕竟还是朝廷之臣。这‘李鸦儿’竟然这般就寻草军结盟来了,到底是狼子野心。”黄巢如此想着,口中却言道:“如今是李唐一家江山,并非当年周天子失了‘天下共主’之时,欲效春秋齐桓争霸之事,谈何容易?”
李克用喜道:“正是如此,李唐在齐鲁之地便有二三十万的军马。一旦使一名将,统镇数州之兵,届时草军便将进退失据。可江南与之大有不同,其地广袤,其兵力薄弱而且分散,难抵草军冲击,而淮北诸州又救援不及。草军若入江南,驰骋纵横,谁能挡之?再者,李某到时候兵出幽州,直指关内,李唐又怎敢南顾?”
黄巢却皱眉道:“虽是如此,若王将军执意向东,老夫也无可奈何。”
李克用拍案而起,言道:“王大将军若是向东,必败无疑。到时候黄公自可招兵买马,带兵南下。黄公乃是不世之雄,又何须居人之下?李某愿与黄公歃血起誓,结为盟友。你我一南一北,通有无,同进退,共取李唐江山。黄公意下如何?”
黄巢听了这话,心道,“这李鸦儿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见识,万不可小觑,将来或是我之敌手。只不过,眼下先灭李唐要紧。”
这一夜,英雄话尽,天已微亮。
河南道。陈州。宛丘。
摩尼教的地下总坛里,一声长啸,如同山崩雷震。
总坛里所有教众都听得这一声长啸,非但不慌不乱,反而个个面露喜色。一个五六十岁的白袍老者,头戴蓝色之巾,正是三老之一的天老。他闻得这一声长啸,那张从不波动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一丝惊喜之容。他低声自语:“方教主,你终于出关了……”
教中教众,六旗四象,连同天地人三老,阴阳两界主,都来道贺。宫殿之中,圣火教众沿途唱起了《叹明界文》,这是摩尼教教义所在:
光明普遍皆清净,常乐寂灭无动诅。
彼受欢乐无烦恼,若言有苦无是处。
常受快乐光明中,若言有病无是处。
如有得住彼国者,究竟普会无忧愁。
处所庄yán皆清净,诸恶不净彼元无。
快乐充遍常宽泰,言有相陵无是处。
这教众万音合一,响彻坛中。其声颇为庄yán神圣,哪有一丝猥亵淫邪?其貌也极尽虔诚恭敬,又何来一分凶残嗜杀?以致于教中隐隐有火光闪烁,佛乐齐鸣,这一幕与江湖口中的“魔教”二字,太过不同。
一个中年汉子,看起来只有四十岁左右。这人披散着头发,脸上消瘦见骨,而双目却光彩熠熠。他额头之上缠着一条黑白参半的头巾,身上着了一件白色长袍,那胸口处,赫然印着九朵赤色火焰,正是摩尼教这一代的教主方驳。
方驳自上一次闭关,至今已有三年。现在他终于突破桎梏,练到了《二宗法》第五重境界。这一步,让他真正到了武功通玄的境界。
底下教众俱是身着白袍,额有头巾,都聚在这底下宫殿之中,只见一片白茫茫,可不有上万人?
忽然那教众之中,有数列人跑动,排成阵势,其中十杆大旗摇动,上面分别写着“甲”、“乙”、“丙”等字样,这些人排作十个方位后,个个单膝着地,齐声高呼道:“十方旗参见教主!”
继而又是数列人跑动,有九杆大旗摇动,上面却是写着“天任”、“天冲”、“天英”等字样,这些人也跪下行礼,高呼道:“九星旗参见教主!”
如此数番,十方旗、九星旗、八门旗、七辰旗、六合旗、五行旗这总共六旗教众分别行礼完毕。到了四象坛,虽然四象坛主此刻俱不在教中,可他们的礼数却不可少。只见四尊巨大的铜像赫然而来,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神兽的样子。这四个铜像,足有一丈来高,都由八个教众扛在肩上。这些教众依然行礼山呼,就连扛着神兽的三十二个教众,也都齐刷刷地单膝着地,而那肩上铜像,却不颤动分毫。
方驳站在大殿之上,气机震荡,如沐圣光,好似天神临凡一般。教众尽皆膜拜,口中齐声喊道:
聚散何悲,生死何欢。
焚我成灰,圣火如莲。
以我之躯,成光之燃。
以我之血,成明之源。
光明慈父,恩泽万物。
唯我明尊,神力如故。
众生疾苦,其心可诉。
天下是非,消弭无处。
在他们众人眼中,这教主便是明尊、明父临凡之人。这不仅是武力上的震服,更是心灵之上的拜倒。
方驳开口,如有魔力:“吾之兄弟,吾之姊妹,明尊有旨传来。”
底下教众山呼:“教主洪福,摩尼万岁!”
方驳接着言道:“摩尼一教,历千难经万险,自当百折不回。天下有光明之处,便有光明之人。今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吾等须以残躯祭圣火,与众生除苦难。”
总坛之中,火焰迭起。教众膜拜,声势浩大。
阴阳两界主就站在方驳的左右两侧,那阳界主转向方驳,开口道:“禀教主,武林已组成同盟之师,正奔向曹州与绿林势力厮杀。”
方驳问道:“以阳界主之见,武林同盟几时可破曹州,得到太湖盐帮总舵?”
阳界主略一沉吟,道:“据那人所言,不过旬月便可破曹州绿林,直抵太湖。”
方驳点头,笑道:“三大派出手之际,便是我摩尼教扬威之时。”说罢,便令教众准备一切征战杀伐之物,都须于旬月之内完成,有延误者,处以火刑。
底下群情激荡,各去准备。天老忽而向前,言道:“教主……少教主他……被人杀了。”
方驳忽然闻得独子已死,心底骤然吃痛。可他如今武功通玄,心境上更是不易动情。所以他面上不动分毫,就连声音都没有一丝变化:“是何人杀了我摩尼少教主?”他甚至不言方连鹤之名,只与寻常教众等同视之。
天老听到方驳如此讲话,知道他已心如铁石,不由得暗叹一声,回道:“相州魏尺木。”
方驳沉吟道:“魏尺木?江湖里几时出来了这么个人物?此人如今是死是活?”
人老便向前,跪于地上,请罪道:“属下无能,一连几番被他逃脱,最后还为其所败,请教主赐罪。”
方驳淡然道:“人老几番失手,却该重罚。不过他既能杀了少教主,自非庸才,你一人不能将之擒杀,倒也有情可原。如今大计当前,且免此罪,留诸后用。起来吧。”
天老又问道:“那魏尺木……”
方驳挥手道:“先不管他,大计为要。”
待天老、人老退下,阳界主又道:“教主,就在几日前,属下探得四象坛主所为可疑,似是搜集教中隐秘。如今青龙、朱雀、玄武三人已不知所踪,只有白虎还在掌控之内。”
方驳皱眉道:“当年青龙四人反出茅山,投我摩尼,本就可疑,我便令你和少教主多方留看,不料还是出了问题。此事关乎教中隐秘,还须从速处理。就有劳阳界主亲自安排了。”
阳界主领命,与阴界主一齐退下。至此,大殿之中便只剩下方驳一人,他喃喃自语:“这天下,终究还是摩尼教的天下。只是,这摩尼教是中土之教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