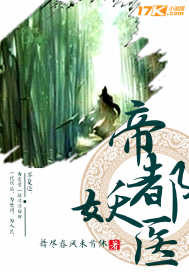魏尺木从纵博赌坊出来,一身血污,其迹淋淋,像极了刚从地狱里走出来的恶鬼。魏尺木信手牵了赌坊外的一匹快马,趁着夜色便往长洲县城的另一头狂奔而去。因为在长洲县城的另一头,有一处奢华院子,是城里最有名寻花问柳之地。在魏尺木看来,色字头上一把刀,那溺色之人比之嗜赌之人还要可恶,自然也是该杀。
魏尺木一边催马而奔,一边把从纵博赌坊里裹来的钱帛丢在路上,他马到城西,银子正好散完。魏尺木虽然杀人成瘾,一连杀了一百多人,可他心里还是存有正邪之分。他不禁思道,“这般杀人散财,可算得上劫富济贫?可担得起‘大侠’二字?”
魏尺木一念未息,已瞧见前面一幢亮堂堂的院子。那院子外头挂满了红色的长灯笼,照得路前亮同白昼。非但如此,那窗前还有潺潺溪水,那门外还有依依杨柳,只可惜时值深秋之际,那溪水是将干未干,那杨柳是不残也残——可在魏尺木看来,这涸水残枝,却别有一番风趣。
那院子的门楣之上,写的是“藏衣楼”三个飞字,门前则有几个浓妆艳抹的娇滴女子,正卖弄着风骚,招揽来往的行客,其间莺声燕语,滑骨润肌,有十分香艳。
魏尺木下了马,仗刀直入。那门外的姑娘见他满身血污,面目狰狞,俱是吓得花容失色,直往院子里躲去。魏尺木闯将进去,却是逢人便杀——当然,只杀男子。
青楼里乱成一片,姑娘们惊恐非常,尽藏作了桌底惴兽;男客们避无可避,都沦为了刀下之魂。魏尺木屠杀正酣时,忽有一声大喊,飞来一把钢刀架住了魏尺木手中的“雁尾”墨刀。
魏尺木运力震开钢刀,凝目看去,但见那人青衣黑靴,约莫三十来岁,生的是圆头尖颔,铁眉钢须,身子十分矫健,那双臂犹长。
魏尺木不由问道:“你是谁来?”
那中年汉子高声回道:“老子褚豹,你是谁,敢这般撒野!”
“褚豹、安良……除暴安良?”魏尺木口里咀嚼着这两个名字,又问道:“那安良是你什么人?”
褚豹见魏尺木提到安良,不禁收回了钢刀,回道:“他是我二弟,你认得他?”
魏尺木听罢,心里觉得好笑,这兄弟二人名为“除暴安良”,干的却是赌馆妓院的勾当,当下便笑道:“哦,我和他赌过一场,侥幸赢下了他的脑袋。”
褚豹惊怒道:“你……杀了他?”
魏尺木却是摇了摇头:“不,是赢下了他的脑袋。”
褚豹听了更是暴跳如雷,恼道:“我二弟赌技出神入化,怎会输给你?分明是你杀了他!”言毕,又是一刀劈来,刀锋颤颤,力道非凡。
魏尺木接过这一刀,心道,“这褚豹的武功倒是远在那安良之上。”
两人才过了三招,忽听得楼上有人沉声喝道:“何人在此聒噪!”其声威严十足!
魏尺木抬头看去,见是楼上栅栏边立着一个身穿圆领绸衣的男子,约莫四五十岁,面相温和而不失一丝刚毅,倒像个有正气的读书人,此时正从楼上看向魏尺木。
魏尺木试问道:“你是这里的主子?”
那人并不隐瞒,实言道:“不错,我乃长洲县令,也是这‘藏衣楼’之主。”
魏尺木听得这话倒是微微吃惊,虽说官员养妓狎妓乃是本朝风尚,世人皆知,只是这官员暗开妓院倒是十分少见。
魏尺木忽而笑道:“你既然在这里,倒是省却我去县衙里寻你去了。”
那长洲县令眉头微皱,问道“你寻我有何事?若有冤屈,本县自会为你主持公道。”
魏尺木道:“啧,有人设赌馆、开妓院,碍着了魏某的双眼,县令大人可能替我主持公道?”
那长洲县令听了这番说辞,微恼道:“别人设赌馆开妓院自有营生,你不爱去就不去,如何碍着你了?”
魏尺木故意皱眉道:“如此说来,县令大人是不管了?”
长洲县令拂袖怒道:“本县管不了!”
魏尺木却诡邪一笑:“那魏某只好自己管了。”话音未落,忽然使出一招“知小忘大”,劈向不远处的褚豹。
那褚豹正在一旁听着魏尺木与县令相谈,忽见魏尺木一刀劈来,顿时惊怒交加,举刀相迎。只是那褚豹仓促举刀,其力难以尽发,而魏尺木那一刀却是刀芒暴涨,只听得“咔嚓”两声,褚豹手中的钢刀断为三截,掉落地上,那刀势犹自不减,正劈在褚豹的面门之上。褚豹双目惊恐,犹自不信,可身子却轰然倒地,一命呜呼。魏尺木一刀杀死褚豹,并不耽搁片刻,而是一举跃到楼上,再起一刀,想要劈了长洲县令。
长洲县令见魏尺木先杀褚豹,再跃楼阁,大惊道:“你敢刺杀朝廷官员!”
魏尺木不闻不问,只管出刀,眼见“雁尾”墨刀就要劈在长洲县令的身上,忽然从绣阁里窜出一个身影,护在了长洲县令身前,使得魏尺木不得不收了刀。
那护在长洲县令身前的人是个身穿绿衣、脚踩碧鞋的美貌姑娘。这女子芳名儿唤作绿丝,是这“藏衣楼”里的头牌,生的是娥眉杏目,婀娜多姿,有花月之容,鱼雁之态,又习得书画音律,可谓是色艺俱佳,更兼烈性如火,凡夫难近,即便是在整个苏州也是难得一见的尤物。
这“藏衣楼”的名字自然出自长洲县令之手,乃是取“女子如衣,藏之高楼”之意。长洲县令是个读书人,这里的姑娘俱得他一一赐名,各有出处。这“绿丝”二字便是出自《诗经·绿衣》中“绿兮丝兮,女所治兮”一句。
魏尺木见这绿衣女子奋不顾身,怡然不惧,咦道:“你愿替他而死?”
绿丝眉头轻拧,坚决道:“不错。”
魏尺木疑道:“他待你始终如一?”
绿丝眉头不拧反锁,上有一丝哀怨,轻声道:“没有。”
魏尺木得了这两个字,忽而展开身形,一手分开绿丝,一刀挥向那长洲县令。须臾间,那长洲县令的头颅已被割了下来,滚落楼下!
魏尺木身法刀法俱是奇快无比,众人眨眼之间,他已杀了县令,朝众人喝道:“县令已死,这里便是无主之地,你们皆得自由之身,都去罢!”
一声毕,便听得寥寥的窸窣之声,只有几个女子逃也似的离了这家青楼,而其余多数女子都立在原处,惶恐不安,不知所措。
魏尺木见状,又呼道:“你们尽可放心离去!”
那姑娘们之中便有人言道:“我们常年住在这里,也算衣食无忧,而今又去的到哪里!”
魏尺木听了这话,心中不由叹道,“鱼儿困在缸里久了,便不晓得河川之大,江海之广,何其悲哉!”
魏尺木正要再劝,忽感身后一道凛冽,令他心中不禁一寒。他转身看去,只见绿丝姑娘,圆睁着双目,盯着自己,眼神十分冷冽,其中有哀、有怒、还有恨——似是无休无止!
那绿丝姑娘终于开口,寒声道:“我自为娼,我自为妓,又与你何干?你凭什么在此杀人!”
魏尺木被这绿衣姑娘指责,心生不快,随口回道:“如此糟践良家,死有余辜!”
绿丝忽然双目泪下如泉涌,犹自冷声道:“我等虽沦为娼妓,受尽轻薄,可县令大人待我等恩若父女,这‘藏衣楼’更是我等安身立命之所,而今你杀人父,毁人家,可还要我等感激你么?”
魏尺木只觉得这绿衣姑娘蠢不可及,这县令不过是拿她们取乐卖钱,纵有小恩小惠,哪里及的上其罪恶之万一?如此心智,却是可惜了一副好皮囊。魏尺木自讨个没趣,但觉羞愤不已,正欲离去,却不料那绿丝姑娘忽然纵身而下,竟朝着那县令的人头处从楼上跳了下去!
绿丝虽死,仍目视长洲县令之头,以此明志。
魏尺木正无措间,又听得门口处一声喊:“魏尺木,你还要杀多少人!你杀净了纵博赌坊里的一百多人,还要杀净这里么!”
来人正是韦治亡,他怕魏尺木继续杀人,便沿路追寻而去,却总是迟了一步。韦治亡从纵博赌坊追到藏衣楼时,正听见绿丝言讫坠楼,他又见满地尸骸,心中悲愤,因而发声。
韦治亡这话一出,楼里的姑娘们更是惶恐不安,原来这执刀杀人的黑衣少年不是什么救苦救难的菩萨,而是杀人越货的歹人。
魏尺木自打那绿丝坠楼开始,心中便是冰凉一片,而今听见韦治亡呵斥,更是烦不可耐。他本以为自己虽然大开杀戒,做的却是惩恶扬善之事,哪里能料到今日竟是这般局面?
魏尺木本是天性善良悲悯之人,他因在洞庭山上受人陷害、遭人围杀而变得孤愤难平;因宽宥恶人以致低眉父女惨死,而变得不再仁慈;现在他又因以恶制恶、杀凶救良,反被人指责,便开始渐渐变得冷漠起来。
魏尺木心中茫然一片,愈发冰凉,索性撞开韦治亡,夺路而去,只身离了“藏衣楼”。
魏尺木虽离了藏衣楼,可苏州境内仍是惶惶不可终日,以致于昼无行人夜闭门,连着天色,萧索一片。那巷里坊间开始传出有一个使刀的杀人魔头,唤作魏尺木,背地里都唤作“刀屠”。
魏尺木并不知道自己一夜之间竟得了这么一个诨号,他如今已不再强行杀人,因为他不知道杀人是对是错,他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自从离了藏衣楼,魏尺木便整日里浑浑噩噩,不知所往,不知所终,不分南北,不辨寒暑,饥则食,乏则寝,只不过是风餐露宿,随行随止,以致于多日下来把自己弄了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
魏尺木曾又路过松江岸上那葬了低眉父女之处,那晚他独坐江畔,望着茫茫江水,忽听得江中响起了琵琶之声,有人唱道:
公子本是多情人,风过幽谷香行云。
一朝不慎遭人陷,多少无辜变鬼魂?
其声明净,如倾如诉,那口吻似时常规劝,又似临行嘱托。魏尺木听了这歌声,不由得又想起了低眉,心中便生出一段酸楚,他喃喃道,“低眉,你也觉得我错了么?”
……
这一日,魏尺木总算出了山野,来到了大道之上。那道旁设有一家简易的茶铺,里面坐了几个歇脚的行人。魏尺木进去坐下,那卖茶的是一对儿上了年纪的翁媪,并不嫌隙他一身酸臭。
“呵,苏州这些日子是怎么了,竟一连出了两个阎罗!”
“是哪两个?”
“你不知道?一个是‘刀屠’魏尺木,他可是一夜之间连杀了几百人,眼也不眨!”
“那可真是个杀人魔头,另一个是谁?”
“另一个却有几分神秘,凡是落在他手中的俱难活命,因此没人知道他的音容。不过他每杀一人便会留下一个名号——唤作‘画伤谷主’!”
“画伤谷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