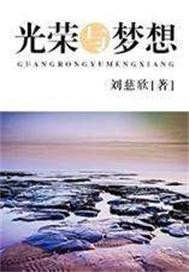周身空气似乎凝固了起来,云惊澜一颗心砰砰直跳,那双眼睛熠熠生辉,宛如夜空中最亮的星辰。
“不妥,皇后赏赐之物理应好好供存着才是,这次宴会非同小可,不能失了分寸让人笑话,虽然时间紧迫,但好好赶制还是行得通的。”
楚慕寒眉眼带笑,唇角勾起恰到好处的弧度,眼神里满是宠溺。
瞧这架势,理应是非作不可了,云惊澜嗟叹一声,满脸黑线,突然间似想起什么一般,圆溜溜的眼珠子转了转,又即刻换了一副眉眼,莞尔一笑道:
“既然王爷心意已决,贱妾也不好拂了您的兴致,这次便算作最后一次,日后不必再这样,如何?”
云惊澜咽了口唾沫,暗暗骂了自己一句,本来想问他脸上的印痕是怎样消失的,但看着他深邃乌黑的眼眸,不知怎么的竟转了话锋。
“不妥,王妃眼光太差,白瞎了这副姣好容颜,本王实在不放心,况且再过几日便要迎接南浔使团,倘若门面不应景,丢的可是我启月国的脸!”
说来说去就是嫌弃她太土喽!
云惊澜一张老脸瞬间变黑,倘若没有听错的话,不远处站立着的那几个看似一脸冷漠实则已经笑掉大牙的的丫头此时此刻再也无法忍受,皆嗤嗤笑出声来。
这裁缝果然名不虚传,挑剔程度一点也不比从前那个民间专为有缘人裁剪衣物的老者低,云惊澜畏畏缩缩的僵直着身体,任凭他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好在她身量高挑纤瘦,作起衣物来也较为容易,师傅忙活了一阵便收了工具,转而又问了云惊澜几个问题,挑了些许花样便不再搭理她。
楚慕寒近几天着实忙碌的很,就刚刚那会儿空也是他忙里偷闲偷出的,短短一盏茶时间过后便又没了踪影,云惊澜纳闷的很,不仅楚慕寒找不见,就连时常在府内照应的清风也没不见人影,一件几天时间都是如此,算算日子,离使团到来的时间也就七八日了。
皇帝将接见使团的事宜交托给楚慕寒和楚景铄两人,其实这些天两人各怀心事忙碌着直到前几日才开始准备,为保证安全起见,楚慕寒将驿馆安排在帝都最为繁华的成京路,周围大都是些寻常富商府邸,避免了无事生非的人前去滋扰。
弟兄两人绝口不提之前的事情,默契是有的,奈何心里的结同样深深种下,纵使前尘往事已然被风吹散,那些曾经温暖过彼此的岁月依旧停留心底,许久乃至永远都不会轻易被抹去。
楚景铄自小便跟在楚慕寒身边共事,做事风格也颇与他相似,雷厉风行又不失细致精益求精,两人配合也出奇的默契,原本需要许久才能搞定的繁琐事务,两人经手之下不过成十天便已经差不多。
八月二日,南浔使团便会进入帝都宫城,到时候太子殿下会同百官一起迎接,待跪拜过皇帝之后,便由楚景铄亲自带领他们,并将其安置在事先预备好的驿馆,吃穿用度全都有专人打理,一切照着他们在南浔的规程制度来,隔日,宫城之中将会举行盛大的接风仪式。
南浔国虽为附属小国,但经过近几年励精图治已经壮大了许多,启月国自然应该以更好更高的礼仪进行欢迎,以促进两国长久的友好关系。
关于使臣迎接待客这件事,承启帝曾经特意召弟兄二人商议过,楚景铄主张以大国之礼进行,而楚慕寒则持相反的意见,南浔虽日益强大,但究其根本也是启月国的附庸,倘若礼数太过,难保他们不会因此而心生他意,弄不好会弄巧成拙,反倒不美。
承启帝也更加赞同楚慕寒的观点一些,帝王心深不可测,也许三两句话的事情便会将其惹恼,再想赢回荣宠便不会那么容易,楚慕寒自然知晓这个道理,从前湘王爷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可不少,会做事,会说话方能使得龙心大悦,楚慕寒这方面功夫还有待改进,不过目前这种样子已然很好。
迎接礼仪之后,使团会在帝都停留一月,进行各方面的交流,南风曾通信给楚慕寒,告知他国主本意想为南峥公主挑选中意的驸马,这件事只有楚慕寒一人知晓,所以这引荐人才的重任便交托给他了,楚慕寒自然未曾推脱,将此事揽下。
自从那日在沉香榭稍坐片刻之后,楚慕寒再也没有出现在云惊澜面前过,也不知到底在忙些什么。
七月二十六日清晨,云惊澜正晨起梳妆,对镜描眉十分惬意,身旁阿悄闷着脑袋为她梳理青丝,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暖风自门外吹来,悠悠的兰花香弥漫,云惊澜心情舒爽,带着几个丫头去看了看新衣服的进展状况,多加赞叹了一番后又出了府门直奔兰若轩而去。
纵然那兰若轩为湘王旗下产业,但之前出了那么一档子事后,那些奴才便不敢再为难她们,每次前去必然恭谦有礼,云惊澜倒是不在意那些虚的,她是要去寻药的。
阳光正好,虽然微微有些燥热,好在乘着轿子徐缓前行,也没有那么浓烈的热意,正是日上三竿的时辰,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瞧见如此气派的马车,自然纷纷避让,宽阔道路上车马缓行,整个街头熹微闪现很是惬意。
兰若轩就在前方街口,转个弯便到了,云惊澜寻了个不大明显的位置命车夫停下车马,又戴上青白面纱将一张俊脸挡了大半,这才带着几个丫头进了药坊。
上次那件事以后,景瑞雪便被尚书大人关在府里愣是闷了十几天,虽说她心绪不佳也不想出门晃悠,但天性乖张的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这般待遇,这几日实在心烦意乱,便偷偷摸摸乔装打扮翻出了府门溜达,一来二去便被景嵩发现,好生责备了一番以后便不再搭理,只叫她收敛些动作,莫要再做出些糊涂事来。
景瑞雪自然知晓父亲的意思,楚景铄的那这话已经如同尖利的刺一样深深扎进她的心口,这些日子她勉力将自己的心绪打理收拾,奈何情根深种难以自拔,除了借酒浇愁以外似乎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法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