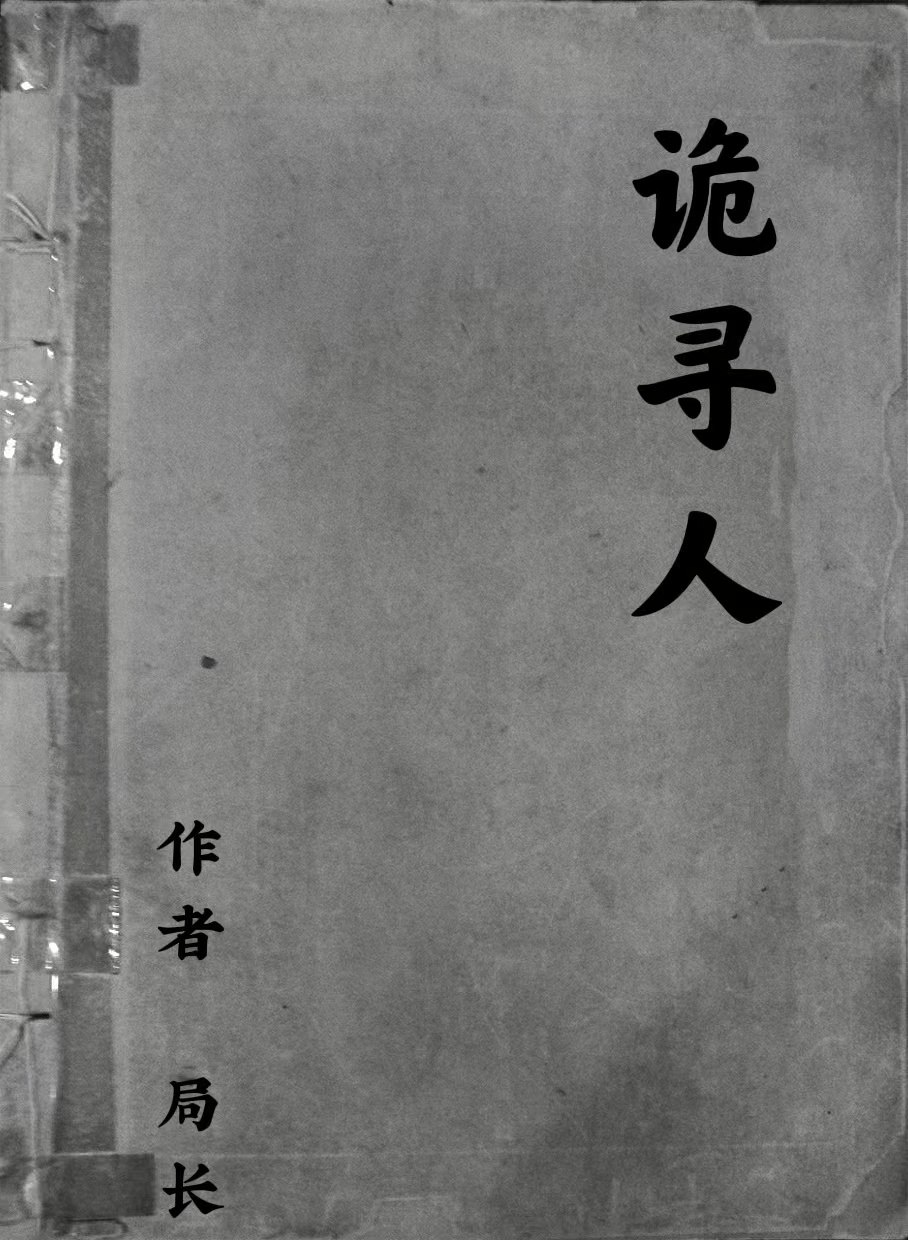棺材上铺着单薄的小甲被,孩子们应该就是在这上面睡着觉,现在正是十一月份严寒时节,兰芽不由眼睛发涩。
自己家虽然穿的不是上等绫罗,但却是最暖、最舒服的;
自己家虽然住的不是广厦楼阁,但却是最亮、最温馨的。
兰芽深呼了一口气,对结巴少年道:“怎么这么多的孩子,你和他们的家人呢?”
结巴少年对鹦鹉使了个眼色,鹦鹉会意,即快又急的说道:“吉良是南川人,五年前爹被抓兵丁,再也未归。叔叔欺负孤儿寡母,占田产,霸房子,陷害娘亲,来北川找爹,娘病死,流落至此。”
兰芽同情的看了一眼结巴少年,又对鹦鹉道:“别光说别人了,你呢?”
鹦鹉一脸红润道:“俺娘是个妓子,生下俺便扔在郊外了,是一个老乞丐收留的俺。老乞丐没了后,我便跟着吉良大哥了。”
兰芽神情一蕴,心里堵得难受。
原来,这些孩子,都曾经被一个老乞丐收养,老乞丐死了后,结巴少年做为年纪最大的,便挑起了重任,组织孩子们满大街当乞丐。
后逢灾年,要饭也是上顿没下顿,结巴心一横,便组织孩子们坑、蒙、拐、骗、偷,好在他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权贵不惹,穷贫不欺,专挑中等之家下手,而且只取钱财,从来不伤人命,几年下来,竟也相安无事。
很不幸,兰芽母女几个就是他们所说的“不富贵、不贫穷”的猎物。
只是任他们也没想到,一个丫头片子,竟然身藏利刃,说下手就下手,说见血就见血,分毫不含糊。
走到最尽头的棺材上,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儿,躺在两个合在一起的棺材板上,身上盖满了各色补丁的破衣裳、破被子。
男孩儿的脸色苍白,眼窝深陷,嘴唇干裂,气若游丝,这样的场景,让兰芽不由得想起在现代时看到的一张战区黑人男孩儿的照片,一样的枯瘦,一样的绝望,一样的心酸。
兰芽探了探男孩儿的额头,额头出奇的烫。
兰芽忙让兰朵打盆水来,又叫了兰丫进来。
兰丫似模似样的摸了摸男孩儿的脉膊,又挑了挑男孩儿的眼睑,男孩儿半梦半醒间,看了眼模糊的兰丫一眼,随即又昏睡过去。
兰丫忧心道:“三姐,他烧的时间太久了,我身上只有自己研制的暂时退烧的药,不知功效如何,也去不得病之根本,你看能用吗?”
兰芽点了点头道:“他的身子像火碳一样热,再不治就要烧成脑膜炎了,先降一降烧再说,效果不大也总比什么也不做来得好。剩下的只能寄希望于白郎中了。”
将水递给兰丫道:“这是你的第一个病人,你要好好给医治。”
兰丫小脸肃然的自怀中掏出来一个小盒来,里面不同大小的药丸三颗,有红色的、黑色的、绿色的。
拿出其中一颗绿色的药丸,兰丫直接递到小男孩儿的嘴边,药丸却是比小男孩儿的樱桃嘴还要大。
兰丫不禁脸色一窘,将药丸放在手心,一顿搓圆揉扁,揉成了无数颗小细丸子,小心的放在男孩儿口中,随即喂了一勺水。
小男孩儿已经没有直觉,水与药丸混在一处,顺着嘴角,流到脸旁一侧。
兰丫急得小手慌乱,重新试了一遍,仍是如此,不如焦急的看向兰芽。
兰芽脸色肃然道:“兰丫,虽然你刚刚学习医术,但你要永远记住一点,就是胸怀仁心,心无旁鹜,方是医之大者。不要因为遇到阻力就退缩。”
兰丫小脸一赦,看着还在流出的药丸和药水,轻闭了闭眼,兰芽心中略觉安慰,小丫头终于能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了,而不是一味的依赖她。
兰芽还没有老怀安慰完,只见小丫头将药丸塞到自己口中,随即喝了一口水,在众人目瞪口呆之时,口对着口,将药和水都灌入了小男孩儿的口中。
静,针落可闻的静!!!
兰芽吓得忘了呼吸,众人眼瞪得似铜铃。
见众人皆莫名其妙的表情,兰丫紧张的问兰芽道:“三姐,这个方法不对吗?”
兰芽轻咳的两声,讪笑道:“医者父母心,无性别之分,你的思想是对的,但是,兰丫,你身为医者,不知道风寒之类的病症会传染吗?”
兰丫的小脸登时垮了下来,委屈道:“可是,怎么样才能让他吃药啊?总不能见死不救,我即使被传染了,我可以回去赖上师傅,完全不会有生命危险啊。”
兰芽将剩下的几颗小药丸塞到男孩子儿嘴里,手下一用力,男孩儿忍不住轻咳了一声,药丸登时借势进了咽喉,被灌了下去。
兰芽肃然道:“丫丫,方法有很多种。你用的方法虽然温柔,却是最不利人利己。病症有很多种,表面上看是风寒的,未必是风寒,也可能是不治之症,甚至是瘟疫绝症,你这样做,失了专业态度。以后还是多多向明神医学习吧。”
见兰芽态度严厉,兰丫登时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倔强的抿着唇,看了看小男孩儿,喃喃道:“三姐,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知道错了。”
兰芽摸了摸兰丫的小脑袋,轻声安慰道:“没关系,错误不可怕,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去改正,现在,你去车厢里取了给爹打的酒,用帕子蘸了帮小哥哥擦额头和腋窝降温。”
兰丫小小的身子飞快的跑了出去,取了白酒,用自己小小的帕子帮着小哥哥降温,最后将湿帕子掖在小少年的腋下。
又过了一会儿,白郎中被结巴少年扯得跌跌撞撞的进了屋内,摸了摸小少年的额头,惊疑道:“烧竟然退了好多,神算子的风寒还在其次,主要是身子亏空得太久了,所以病来如山倒,病去则如抽丝,以后要好好将养着,最起码要养上半年,别累着,别饿着,也别冻着。”
抬眼看了看海氏道:“如果有善人买了去做小厮也不见得是坏事。”
白郎中又将药箱里的两包药递给结巴少年道:“吉良,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这次就再发回善心,舍你两天药,多的我真承受不了了。”
兰芽倒是意外的看着白郎中,没想到他还是有些善心的,从怀里掏出五两银子递给郎中道:“白郎中,这是药钱,多余的您再劳烦您给开些补药 。”
白郎中点了点头,眼睛一润,对海氏道:“对这孩子好点儿。”
兰芽面色一窘,赶情好,白郎中以为于家花五两银子来买小男孩了。
也不多做解释,笑道:“劳烦白郎中再帮我看看这个小哥。”
将小胖堆牵到白郎中身前,白郎中眉头皱了又皱道:“准子应该是肾脏受损,只能开些养护之药,同神算子一样,需要静养,不能劳碌奔波,不能做粗活。”
说完,似想到了什么,白郎中不自觉住了口。
兰芽岂会不明白白郎中的担心,笑道:“无碍,白郎中只管开药便是。”
兰芽又从身上掏出五两银子递给白郎中。
白郎中脸色发窘道:“用不了这么多的。”
兰芽淡然道:“多的就当谢谢白郎中以前照拂之恩。明日劳烦白郎中到仁德街王家复诊。”
白郎中不由心下黯然,同时又很是庆幸,黯然的是,这两个孩子到底还是卖了身;庆幸的是,主家没有因两个孩子有病而放弃他们。
兰芽哪里顾得上白郎中的想法,送走了郎中,将吉良叫到一侧道:“吉良大哥,现在时值隆冬,你们住在这里,到寒冬腊月是要冻死人的。我倒是有一个主意,能帮你和孩子们安然度过冬天。”
吉良不好意思道:“太、太麻烦于、于姑娘了,只要、不冻死,不伤、伤天害理、你,你说咋办就咋办。”
兰芽想了想道:“我家在仁德街有套宅子,是给我姐做陪嫁的。我姐还没有定亲,一时半会儿成不上亲。我本来想买一户人家看宅子,你们既然没有地方住,不如去帮我看宅子,我省了买人的钱,你们也有个落脚的地儿。”
吉良哪里不明白兰芽的谦词,眼圈一红,叫过来鹦鹉一顿比划,鹦鹉眼睛不由一润道:“感谢您的大恩大德,我替所有的弟弟、妹妹们感谢你,一日三遍香为于家祈福。”
兰芽摇了摇头,吉良招呼着孩子们圈在一起,只见孩子们各个喜形于色,如蜂般的去收拾东西,紧紧的跟在车厢的后面,回了宅子。
兰芽将所有的孩子们集在一处,肃然道:“我想,吉良哥哥已经将我的意思告诉你们了,我现在再重申一遍。”
“第一,我是雇佣你们,不是施舍,更不会同情,你们做不好活计,我可以辞退你们;同样,你们找到更好的去处,也可以随时离开。”
“第二,在我这里做活,我和你们是平等的关系,你们可以有个性,但不可以随性,要各司其职,不可以推讳扯皮,更不可以再做那些坑蒙拐骗偷的行当。”
“第三,我家不是大富之家,一些不切实际攀附大户的想法不要有,此外,我家没有那么多的活计,一会儿,我会按你们的特长进行分类,帮助你们寻找合适的活计。”
将所有的孩子们安排在了二进院子的两间偏房内,让孩子们自己烧了水洗了澡。
老陶则是跑了好几间绸緞庄子,买了现成的被褥和成衣,每人先对付着发了一套,又买了些布匹,分给其中五个十二三岁的少女,被海氏带着赶做出合体的衣裳出来。
于家宅子,整整忙到了后半夜,灯火才熄灭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