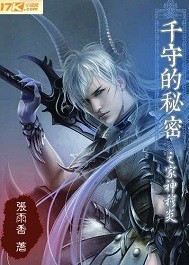白跃海听了双目一垂,满面的哀色,不禁喃喃自问道:“难道为了富贵、为了金银,就必须舍弃自己心爱的人吗?”
“想开些吧,”金石叹着,已缓缓地撑地而起,站了起来,“你如今已然拥有金银与富贵,娶妻又有何难,你想要什么样的女子,岂不都是随心所欲之事,又有什么是钱办不到的呢?”
“那你呢?”白跃海冷笑着问,“你为何会对那仙子这般痴迷,以至于还来干涉她的来生?既然你觉得金银能解决任何的事情,那就该忘了她,去寻找新欢啊!”
“我和你不一样!”金石当即便是重重一驳。
“有什么不一样!”白跃海底气丝毫不输于金石,“难道你与你那仙子的爱是爱,我和翠翠的爱便不是爱吗?!”
金石一时被问得哑口无言。是啊,这世间的情情爱爱,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他为了自己与玉瑶的来生,不惜牺牲别人的爱为代价,这在他自己看来,确切太过自私了。他心中自然也生愧疚与自责,可是为了达成所愿,他宁愿将自己变成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物,宁愿背上跨越百年的骂名。——因为这,是支持撑他唯一活下去的信念与意义。
他低下头,又转过身,沉默,不敢再面对白跃海。
白跃海这时忽地咬着牙,撑起一身的疲软无力,硬生生地站了起来,却当下扭过身,直朝李翠翠家行去了。
金石闻声忙一转身,当即一声喝问:“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向翠翠解释清楚!”
“站住!”金石随即将白跃海叫止住了,上前几步道,“你以为,她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我不管!”白跃海只撂下这三字,当即又略带迟钝地朝前而去了。
金石见此一急,霎时化作一道金光,直飞到了白跃海跟前,将他拦住,“你去不得!”
白跃海面肌一横,双手猛地一下紧紧抓住了金石胸口上的衣服,咬牙道:“你这秃驴,快给我滚开,不然,我非要了你的老命不可!”
金石面不改色,当下一只手重重一挥,却见得其跟前霎时光芒一闪,白跃海竟被那光束击退三四步,最后由于失衡,重重地摔倒在地。接着面露苦色,发出阵阵哀泣来。
金石指着白跃海,一脸肃然地道:“你可别忘了,你当初答应过我什么,你若再这般执迷不悟,休要怪我不客气了!”待定定地看了白跃海片时,见他似乎确已没了要去向李翠翠解释的心,方才袖手一挥,顿时化作一道光飞向了天际,未几方消失在半空之中。
※∽※∽※∽※
这日的李翠翠是一路抹着泪回家的,待回到家中,便直接奔进了自己的闺房,一把掩上了门,躲在门后哭泣。
“翠翠,你怎么了?”堂屋里的张氏即李翠翠的母亲见状,忙放下手头的活,奔至女儿闺房门前焦急地敲起了房门,“你怎么了翠翠,发生什么事了?”
然而呼喊了半日,又敲了半日的门,仍不见门开,只听得屋内抽抽搭搭的啜泣声,不由愈发焦急。正在这时,却又忽地听见门外传来几声男子的呼喊。
张氏暂时也顾不得女儿,便忙转身出门去看,却见是同村的殳鹤来了,忙一面上前一面挤出笑容迎道:“原来是鹤娃,你怎么来了?”
“哦,”殳鹤笑了笑,“昨天啊我家那锄头的把子突然断了,这不,今天想上山砍点木头,做个把子,所以想你家的斧头用一用。”
“原来是这事,好说,好说。”张氏一语爽快地答应毕,忙又带恳求道,“不过啊,有件事你得先帮帮我。”
“什么事啊?”
“这不是翠翠吗,”张氏说着目色指了指李翠翠的闺房,“她下午被海娃叫了出去,谁知刚刚一回来便躲在屋头哭泣,敲了半天门也不肯开,问她怎么回事她也不说。你从小不是就和她玩得好吗,不如……你帮我劝一劝她?”
“竟有这等事?”殳鹤听了焦态顿现,“快带我去看看。”
“哎!”张氏一声应道,方忙转过身,领着殳鹤促步朝屋内而去了。
待至了闺房门前,仍听得从房间内发出的清晰啜泣声,张氏方指了指那门,对殳鹤示了一番意。
殳鹤这便行至门前,徐徐伸起了一只手,在半空中犹豫片时,方才敲响了房门,呼了声:“翠翠。”然这般默了良久,却听得屋内啜泣声丝毫未减。
“翠翠,你怎么了?”殳鹤又敲响了房门,温声问道,然结果仍是一样。只两眼焦焦地看了张氏一眼,方又唤道:“翠翠,你快开门啊,你娘都急坏了,有什么事你不妨给我说,我啊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话毕,这方听得屋内啜泣声稍微减轻了些,这般片时,才见门缓缓地开了,——但见李翠翠低着头,擦着两颊的泪水,两眼已有些微微泛肿。
“我的翠翠诶,你终于肯出来了。”张氏这方忙奔至李翠翠跟前,抚握着她的手臂,一面又轻轻将她往桌旁拽去,“别急啊,有什么事咱们坐着慢慢说,你看你鹤子哥也在这儿,他一定会想法帮你的。”
既见李翠翠被张氏拽至桌旁坐下,殳鹤便亦于另一方坐下了,这方小心翼翼地问道:“翠翠,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啊?”
此言一出,李翠翠泣声又现,只哭诉道:“跃海哥……跃海哥他不要我了……”
“不要你了?”殳鹤与张氏互相一对视,一时皆诧异不已,后者忙问:“他为什么不要你了啊?”
李翠翠只像一个孩童般“啊啊”哭着,泪水流了满面,却是不答。
“不可能啊,”殳鹤对此丝毫不愿相信,“我和海娃从小玩到大,他的性情我自然再了解不过,哪里是那种朝三暮四、说变就变的人,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哪有什么误会!”李翠翠满口委屈,“他今下午将我叫至村头,亲口给我说不想再娶我,当时他说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殳鹤看看张氏,又看看李翠翠,不知再找个什么说法来为白跃海解释、安慰李翠翠的心,面色纠结不堪。
“这个天杀的海娃,咋说变就变呢!”张氏当下忍不住一句怒斥,又略带哀色推测道,“难道他当真是有了钱,富贵了,看不上咱穷人家了不成?”
殳鹤见此方对二人安慰道:“张婶,翠翠,你们也莫急,我想海娃定是受了什么打击,脑袋糊涂了,待会我便去找他,跟他说说,兴许这真是个误会呢?”
李翠翠听着,只垂着目,默而不语。她自然希望这一切都只是个误会,因为白跃海不仅是她目前的恋人,更是与她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可谓是青梅竹马,感情深厚自不必说,要说忘记哪有那般容易。
而此刻的张氏自然也希望这只是个误会,当下看了看李翠翠的脸色,方勉强地答应殳鹤道:“那……就照你说的,你先去找海娃好生问问,务必问清楚,说说好话,可不能再让翠翠伤心了呀!”
“放心吧张婶,这事我知道该怎么做的。那我现在便去,也好早些来给你们答复。”白跃海说着便已起了身。既又得张氏点头答应,方才简单辞别了娘俩,去白跃海家里了。
“跃海!跃海!”这日殳鹤方才进入白跃海家的院坝,便是朗声呼喊了起来。片刻,方见得白跃海出现在门口,伸长了脖子往屋外来看。
殳鹤见状方停住了,只朝白跃海勾手示了示意,“跃海,你出来,我有话要对你说。”
白跃海见殳鹤面色带肃,便猜到他定是为了李翠翠的事情而来,心中此刻竟觉得有些难以面对眼前这个从小与自己形影不离的好友。然而事已至此,又岂能不面对。故是微垂着头,缓缓地朝殳鹤走去。
“跃海,你和翠翠之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殳鹤皱眉又带几分小心问道。
白跃海低头默了良久,方才淡淡地说了两个字:“分了。”
“分了?!”殳鹤惊中带疑,“为什么?”
白跃海又默片刻,方徐徐道:“门不当,户不对。”
“门不当,户不对?”殳鹤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跃海!你什么时候有这般荒唐门第之念?那不是别人,那是与你从小玩到大、并且与你相恋了好几年的翠翠啊!你忘记你们这些年走过的时光了?你忘记当初对她发过的誓了?”
白跃海听了这番话,一时竟忍不住面露苦色,低头闭目良久,方转过身,扶着殳鹤的双臂哀声道:“鹤娃,并不是兄弟有了钱便变了心,而是兄弟有说不出的苦衷啊……”
“什么苦衷?”殳鹤忙不解地问。
白跃海却是双目一垂,摆了摆手道:“说不得,也说不了啊,他时刻都在看着我呢!”
殳鹤当即四顾一番,满口的诧异:“看着你?谁啊?”
白跃海只苦苦地摇着头,不答一字,却是忽地目色一定,转身扶着殳鹤的双臂带着几分气喘道:“鹤娃,你听我说,我和翠翠之间这辈子是不可能在一起了。你……你一定要帮我,帮我好好照顾她,照顾她一辈子,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