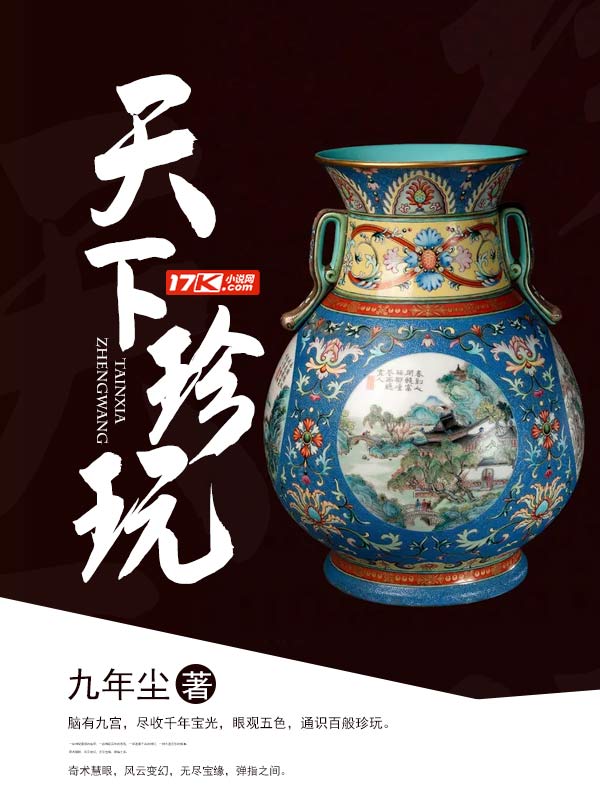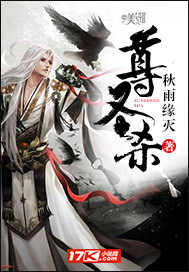正于这时,但见殳鹤、李氏以及曾宏宇亦闻声匆匆来了,见长风果然苏醒,皆是喜极欲泣,便围在长风身边,一面问他情况如何,一面又察其脸色体态。既知他已然无事,方才心安。
“我究竟发生何事了?”长风不禁试着去回忆昏死前的事,竟顿感头疼欲裂,忙双手捂着脑袋,阵阵哀吟。
“快莫想了!快莫想了!”四人连忙劝道。
李氏因念长风重伤初醒,自需静养,便叫他好生歇息,莫再多说多想。当下命人前去请大夫来察看长风身子状况,自己又亲自去厨房,为长风做些滋补疗养之饮食。便只余殳鹤、若柳及曾宏宇陪伴着长风。
曾宏宇见长风迫切想知事情来去,便将他昏迷的前前后后尽与他说了一番。长风听说了那日军营白须僧一事,不禁觉得诧异之至,直惊道:“世间竟有如此怪异的僧人,莫不是天上神仙!”乍又想到自己梦中所历之事,便更觉奇异,遂又忍不住将那梦对三人细说了一番。曾宏宇听罢却道:“凡人都会做梦,你陷入昏迷,做梦亦是极为正常之事,又有什么奇怪的?”
长风语色汲汲地道:“你们不知,我这梦非比寻常。梦中所见所历竟出奇真切,出奇细致,真切得好似在现实中亲身经历一般,细致处可至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全然无在梦中之感。”
曾宏宇却笑道:“梦有多种,有的朦胧模糊,有的清楚明晰,都是有的事。你如此念梦,想必是你入梦时间过于长久,受梦中浓郁情绪影响过深,然而不必久久去想,渐渐地也就不会在意了。”
长风听了却是无话可说,只轻叹一气,垂目皱容,片刻方问:“我这是昏迷了多久?”
曾宏宇听了细细一思,道:“仔细算来,已是一年有余啊。”
“一年!”长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昏迷了一年?这怎么可能?现在是何年何月?”
“现已是绍兴十一年十月了。”
“绍兴十一年……”长风念着,乍又一想到宋金战事,忙又问:“对了,现下战事如何了?”
“唉!”曾宏宇仰头闭目长叹一气,“张、韩、岳三军班师后,高宗一心求和,未果。谁料今年正月,完颜巫术再度领兵南下,高宗心存一丝恐惧,便于二月再命岳将军驰援淮西,可不久又将其召了回来。更令人费解的是,高宗竟然在此时解除张、韩、岳三将兵权,命其到临安枢密院任职。然而,岳将军受到的迫害却不仅仅止于此,秦桧等奸人接连诬陷岳将军有谋反之意,只欲以此为借口除掉岳将军……便在前几日,岳将军被关进了大理寺狱中……”
“什么!岳将军入狱了!不行!我要向皇上求情!”长风说着便要起身,却被若柳连忙止住道:“老爷不可,你才刚刚醒来,身子又这般虚弱,怎可出行?待你身子好一点再去吧……”
“是啊,”殳鹤亦劝道,“有什么事能比身子更重要呢!此事便是再缓个几日,待将身体养好了再去吧!”
曾宏宇道:“贤弟,请听我一言。如今的皇帝已经被秦桧等人左右了,你便是去了也无用。况且你仅是一个小小的侍御史,位卑职轻,他又怎会听从于你。反而你这一去,极有可能触惹到秦桧那帮人,到时,他们难免不会加害于你呀!”
长风听了两眼烁烁地看着曾宏宇道:“身为大宋臣子,眼见忠良入狱、奸臣得志,却是不管不顾、袖手旁观,如此于心何忍!曾兄你也曾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须为此刻当为之事,不去思结果如何。而我眼下如果因害怕被迫害,便任由这伤天害理之事继续发展,那我还算上什么大丈夫!”
若柳见长风这般,竟是忍不住啜泣,道:“老爷,若柳知道你心里难过,可你知道,自你昏迷以来,太老爷和太夫人过得是何等悲苦。太夫人终日以泪洗面,茶不思,饭亦不想,如此一来人自是憔悴消瘦。如今见你终于醒来,太夫人竟忽地如换了一人般,欣喜得泪流不止,又亲自去为你准备饮食。你即便不为自己着想,也要想想太老爷和太夫人,你不能再出什么乱子了。”
“是啊,”殳鹤亦附和道,“你说你好不容易醒来,若再出点什么乱子,我和你娘可怎么活啊!”
长风听此自是有所触动,便只得暂时将心中激愤收起,淡淡应了。
这时仆人所请大夫亦来,既为长风做了简单诊断,便说长风已然无事,遂开了些疗养的方子,嘱咐三两句,方才离去。
自此长风便在家中静养,未曾出门,却一直打听关心着岳飞之事,仍想着待自己身体痊愈后去面见高宗,亲自为岳飞申冤。
另一事,对于曾宏宇口中所说的白须僧及自己所做的那怪梦,长风亦一直念念未忘,竟觉得二事许有些联系,便欲探究。然因无人知晓那白须僧到底何名、从哪里来,自不知去何处找寻,只得从梦着手。遂一日夜里在房间内点上了浓香,手中紧握琵琶玉石放于胸前,心中不止念道“梦中显灵”,覆被睡了。未几果然入梦——
朦朦胧胧中,长风竟见得一白须僧人迎面行来,近了方道:“皆是虚景虚象,何必过于痴迷。你既是迫切想知,我便让你看个清楚。”说罢袖手一挥,长风眼前霎时一白,换了时空——
空旷的林子里,金石默默地跪坐在地上,怀中紧紧抱着玉石琵琶,悲痛不堪。此刻的他几乎已然心如死灰,因为玉瑶的琵琶弦已被王母断去,便意味着永远不可能再复活来。
他默默伤痛了许久,泪几乎已干涸,最后方才缓缓地撑地而起,有气无力地朝林子一方踉踉跄跄地行去了。
这日,王氏正呆呆地在坐在院坝里,没精打采地思着事,耳边却忽地传来脚步声,忙扭头一看,却见是金石抱着一把玉石制成的琵琶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石儿!”王氏方忙起身,前去迎着金石,待至了他跟前,却不见玉瑶影子,方焦急问:“玉瑶呢?”
“玉瑶她……她死了……”
此话一出,王氏心中顿时一个晴天霹雳,腿脚不禁一软,直向后连退三四步,最后一个趔趄,便重重摔倒在了地上,不省了人事。
“娘!”金石惊天一唤,当下忙跑至王氏跟前,既将玉石琵琶放于地上,方才将王氏扶起,连连重唤三两声,然却见王氏此刻已丝毫没了知觉,跟个活死人一般。
于是当下忙将其抱至了房间里,又将那玉石琵琶收捡到屋内,方跑去请大夫去了。
这般半日,方才请了一大夫回来。大夫既为王氏一诊脉,却是骤然一惊,当下忙又观其双目,摸其颈脉,一时惧色尽显。
“怎么了?”一旁的金石焦急地问。
大夫皱眉垂目,片刻方徐徐地摇了摇头。
“到底怎么了?”金石当下提了声音问。
大夫犹豫片时,方淡淡道:“年轻人,请节哀……”
金石顿时霹雳震惊,当下便朝王氏身上扑去,一面不止地哀声呼“娘”,一面失声痛哭,不能自已。
大夫见此,亦觉甚哀,只默了片刻,连出诊费都没忍心去要,便背上诊箱,悄悄地离开金石家了。
经历过妻子之死、母亲之逝后的金石,宛如一具空空的尸骸,整日怀中抱着那玉石琵琶,守在王氏尸体旁边,目光深垂地发着呆,茶饭不思,胡子长了一嘴,对外界万物已丝毫不敏感。
既将王氏葬后,他的这种状态也未见得有丝毫好转。
这般直至半月过去了,他方才决定出家为僧。
这日,他坐于家中榻上,对着丝线尽断的玉石琵琶,手握玉瑶赠与他的琵琶形玉石,泪流不止。
待将那玉石收入怀中,便手挥臂移,光凝气聚,二指朝琵琶一指,一道金光直注入其中。
这般许久,琵琶方渐渐发出微弱光芒,待光至浓时,却是骤然一闪,变化成一枚小小玉石——竟与他怀中那枚琵琶玉有些一模一样的外形。
既将眼前的这枚琵琶玉也收入了怀中,他便从塌上起了身,而后带些不舍地锁上房门,离开了家,去了灵净寺——当地一有名的佛寺。
灵净寺的大殿内,殿前佛像金光闪闪,空中香雾淼绕迷漫。面色淡然的金石垂目合掌跪于一圆垫上,全身静如止水。
在他跟前,一位年迈的僧人正手持一剃刀,为他削下青丝。这位老僧法号普云,乃是灵净寺的主持。
待剃度罢,老僧方才徐徐道:“汝今已然剃度,始遁入空门,贫僧便依本寺法序,赐汝法号子虚。”
“谢大师。”金石微微点头道。
“子虚,”老僧唤了一声,接又道,“请听受沙弥戒——”
“弟子听戒。”
老僧方问:“第一,尽形寿不杀生,汝能持否?”
金石未加思索,便回道:“能持。”
老僧又问:“第二,尽形寿不偷盗,汝能持否?”
金石又是毫不犹豫地回道:“能持。”
老僧又问:“第三,尽形寿不淫欲,汝能持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