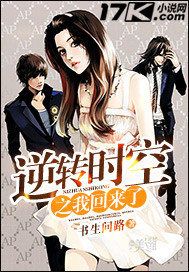话不能这么说。
那件衣服的价值可不能跟一般的衣服相比,我虽然有主意,但不是决策人,所以,我跟阿辉说的目的是希望他将这个问题反映给阿秀或者阿力,让他们来处理。
可是,阿辉对他姐姐的事情太过介怀,是有意要搅局:“这件事你别管了,我会跟姐姐说的。”
他的眼神里还喷着一股气,分明在提醒我他不会跟他姐姐说。
退货事件,时间就是金钱。
但我一个哑巴,除了依赖站在面前的两人,我根本做不成别的事情,就连打电话告诉他们都不能,阿秀和阿力用的聊天工具是MSN,恰好我没用过那种工具。
一整个下午我都显得心不在焉。
脑子里全是那个空盒子的事情。
顾客那里,怎么给对方交待,我看着闪烁不停的头像,都没有勇气点开,这种纠结将我的气焰拉向了低谷。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闷闷地扒拉着碗里的饭粒,现在,阿秀的家又成了我们三人共处的局面。他们依旧甜蜜,而我,依旧是几千瓦特的电灯炮。
电话铃声响了,阿辉去接电话,关于接电话这件事,卢安安懒得起来坐着没动,我站起来接是多此一举,多半时候都是他接。
“喂。”
对方说着什么,他应道:“她不方便接电话,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吧。”
那边没了动静。
我能判断出对方没说话,也是有原因的,阿辉从那句话之后一直在重复一句话:“喂,你还在吗?喂!”他自言自语:“怎么没声音了?”
卢安安不紧不慢的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淡淡地问:“你不会在外边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吧。麻烦都找到家里来了。”
不该惹的人。
我暂时能想到的有奇葩女,花木楠三姐妹,假如连那老先生也算进来,那么,他也是不该惹的人,但我又想,奇葩女的脑子有病,她不太可能追到广州来。花木楠三姐妹的作风是不会那么客气的跟你打招呼的,永远是不请自来,她们若要来找我,直接就掀屋子掀瓦来到阿秀家里。那个老先生,目前为止最大的嫌疑是他,据阿秀说他果真发了悬赏令,高价寻找撞到他哥哥的人。
会不会是那个大叔?
找不到我,他自己应该会回老家的吧。
假如,他实在不愿意回去,一根筋的非要找到我,就认定了我这个人。那我也不会生出多余的同情心,这原就是同事之间开的一个玩笑,如何当得了真?
他的电话挂了以后没多久,电话又响了起来,还是阿辉接的电话。
“喂!”
可能还是刚才同样的话。
阿辉也用刚才的话重复回答。
他回答以后,那边又是静默,阿辉的涵养还算不错,听到对方没动静,默默地挂了电话。但是,当第三次响起来时,阿辉换了一种说话:“她是哑巴,说不了话,你找她有什么事情吗?我可以代为转达。”对方又不说话了,从阿辉的神情就能看出来。
到第六次电话铃声响起来时,他并没有急着站起来,而是跟我聊起了天,卢安安嚷道:“把电话线扯掉吧,快要烦死了。”
阿辉安慰她:“你先进房间吧。”
“不去。”
“电话线不能拔,万一姐姐打电话回来怎么办,还有我爸妈,他们找我时只会打这里的座机号,万一回到老家的他们打电话过来打不通,他们会着急。”他一条一条地分析给卢安安听。
卢安安努着嘴:“让我回房间也可以,你陪我一块。”
“妙妙这里不是应付不过来吗?”
“那是她的事情,林玉辉我警告你,你别太过分了,我才是你老婆,他只是你们家请的一个员工,分清轻重。”她的话铿锵有力。
让阿辉无话可说。
在他们站起来之前,我已经抢先一步比他们先起来了,我得工作了,那个退货事件能拖一时是一时,可早晚还是要解决的。
他们是拔电话线,还是听之任之,我不管。
只要做好我的份内事,即可。
“你瞧她,那德性。我们倒成了帮她打工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哑巴。”卢安安也不急着走了,坐在椅子上等那个骚扰电话再次打过来。
第七次响起来的时候,她接了。
“喂,找那个哑巴是吧,她死了。”
切,平白无故的诅咒我!
就不怕诅咒反噬。
“啊,不是不是,秀姐,我哪知道是你啊,还以为是找阿秀的骚扰电话呢!这一个晚上一直响个不停的,都快把我们给烦死了。”卢安安向电话里抱怨起来。
“报警,这个不必要了吧。反正她也不出门。”
“回老家,秀姐,我现在还不想回去。”
“嗯嗯,我知道了。”
卢安安挂了电话向阿辉抱怨:“你姐可真啰嗦,也不逮个重点讲,东一句西一句的,真不知道她那个业务经理是怎么混上去的。她让我们报警,我不想惹那个麻烦事,真要报也得让那个哑巴去报,凭什么她的事情都让我们替她担着。”
“哎哟,说了好一会子话,我也乏了,我先进去休息了。有事没事都别来打扰我。”卢安安似乎特别容易累,这也能够理解,有些孕妇很不容易,孕期要应付各种生理心理的不适应,嗜睡,容易累已经是最正常的。我曾见过有孕妇从怀孕开始到生产那一天,连着呕九个月的,也有从第一天开始到生的那天都只能待在床上安静养胎的。
做女人着实不易。
生完孩子身材走形,曾经漂亮的裙子只能成为藏品,带孩子后迅速衰老,产假休完,像个钢铁战士一般一头扎进工作。甚至任何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成为一个母亲后都变成可能了。为母则刚,她的诸多不快我都能理解。
阿辉将碗筷收了,将他的笔记本电脑挪了出来,他又要玩游戏了。虚拟的世界能够支撑一个人膨胀的权欲,肥皂泡沫能够让人能够慰藉人的心灵,给人一些美好的启发,就像我看的动漫,它们能够燃起我对未来的希望。
好困。
最近是怎么了,坐在电脑旁多待一会,下一秒就会倒在电脑桌前似的。我努力的支撑着,眼前出现幻影了,突然,头一栽,我倒在了键盘上。
这种感觉不太好。
刚刚才睡了一觉,怎么还是想要睡过去。
“妙妙,你怎么趴在键盘上睡觉啊,实在太累就请个假吧。”有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我回头,是阿辉,我拍着额头,脚下软软的站立不稳,我用一只手撑着桌子。
“妙妙!”
“怎么搞的?”
卢安安也在说话:“喊你姐回来吧,她这个状态还怎么工作,让你姐另外招人。”
“招其它的人过来你就不烦了,只怕见了会更烦。”
“我烦可都是因为你,你干嘛对她比对我还好?说啊,是不是暗恋人家,你要是暗恋人家趁我们还没结婚你赶紧下手,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咱们结了婚你敢这么着,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阿辉还是嘻皮笑脸的:“打断了你可得照顾我一辈子。”
“想得美,打断了我赶紧拿着你的钱跑路。”
阿辉苦着脸:“好吧好吧,我的钱都给你,也没多少啊。不够你下半辈子养老。”
“那你现在要多加努力啊,以后的责任重大,知道吗?”卢安安的声音变得柔软。
“电话,那个电话又响了。”阿辉已听到电话铃响。
卢安安站了起来:“我去接吧。”
“喂,找谁?”
“又是你?”
“我是刘妙,说吧,你找我什么事?”
“什么,你说我不是。”
“刚才,刚才不是跟你开了一个玩笑吗?我就是刘妙。”卢安安冒充我跟对方聊了起来,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我能听清她的谈话。我以为听清楚了,其实没有,我只是听到她说她是我,后来说了什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醒来之后已是第二天了。
手上有扎针的痕迹,不管自己有多不愿意承认,那些扎针的痕迹还是原封不动的回到了我的手臂上。我睁开眼睛看着周围的环境,还在阿秀的家里。
阿辉端着一杯开水,手里拿着药给我送过来:“好些了吗?昨天你发烧,烧到41度,可把我们吓坏了,带你去医院扎针,一直吊了五瓶都没见你哼一声,可把我们给吓坏了,医生说要送你去重症监护室,我们也不是你的家属,谁都没有权利签字。后来,是那天在庆功晏上的一人男人帮忙签字才送去重症监护室,谁知到了那边,你醒过来了。”
“妙妙,你说了一句话,你记得吗?你说,好困!有没有印象?”
“你不是天生的哑巴,以前你会说话的,对吗?”他显得很激动,好像家长对孩子的莫大肯定,为了证实自家孩子是优秀的,费心费力的折腾。他对我的态度,可能源于阿秀和他的母子即视感。于是,他与我之间也是那种奇怪感觉。
“我们带你找了最权威的医生,他们检查之后说你恢复的希望很大,妙妙,你有救了。谢天谢地。”他又一个人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大堆。
她说,我能够开口了。
我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费力的转动着眼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