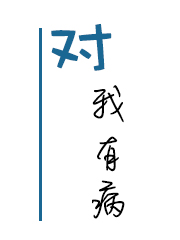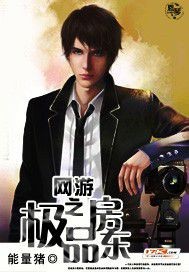难道是我搞错了。
其实这就是去安徽的车,如果是这样,我得想办法下车,跟着去了安徽那一切可都由不得我了,武功盖世的人还害怕寡不敌众,更何况是大叔的地盘。
火车已经在行进途中。
跳车是不可能了,只能等到了中途靠站时再想办法,那两个人站了起来给我和大叔让座,大叔出于好心,给其中一个人腾出半个位置来:“小老弟,你们将就着坐,凑合凑和很快就能到站。”
他们当中的一个满嘴谢意地坐了下来,而另一个一直憋着笑,可能最后实在憋不住了,这时他指着坐下来的那位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你还有脸坐。”
坐着那位一本正经地问他:“怎么就没脸坐了。”
这两个怪异的人再次吸引了大叔的注意力,大叔一脸迷惑地看着那个大笑不止的人,估计他是头一次见到搭错火车还这样心情愉快的怪人。
换成别人愁都得愁死了。
“佩服我的演技吧,快点佩服我吧。”坐在座位上的男人跳了起来,他向大叔鞠了一躬:“对不起,大叔,是我们在捉弄你,其实我们没有搭错车,真正搭错车的是你们。”
简直神助攻啊,我的心情瞬间愉快了。
现在,换成大叔一脸错愕。
他也就愣了那么三、四秒,接着他跳了起来指着两个年轻人大骂:“你们怎么能这样捉弄一个老人家呢,啊,你们吃饱了撑的吧,啊,你们脑子有毛病吧,要是早点告诉我,我们还可以下车去找那趟去福建的车啊。”
他站在那里,口水唾沫横飞的指着两个淘气的年轻人连吼带骂的骂到几乎要吐白沫,也是,正常人的心理都这样,如是别人犯错,一脸尴尬我们可能有心情去宽慰他人,而自己犯了这种愚蠢的错误,对别人的那些宽慰全都成了讽刺,跳转到自己身上成了对上苍的怨恨,怨恨老天不长眼,没让自己顺顺利利。
两个年轻人刚开始还一个劲地赔不是,解释说他们俩是表演专业的学生,刚才两人也就是相互使眼色准备演上一段,在他们听大叔说安徽离福建也不远,可以转乘巴士的情况下才来这么一段事融入群众的演出,没料到大叔的反应这么大。可是,那些道歉的话大叔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反而越骂越起劲,把其中一个给骂火了。
猛地一拍桌子:“不就是为了一点子钱吗?我们赔给你。”
“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道德败坏。”大叔给两人讲起了人生哲理。
我扬着眼睛看了他一眼,果然人不可貌相,您跟他们讲人生道德,那您的道德在哪里?您还打算把我拐了给您做媳妇呢,请问您这么做的时候,可想过道德两个字。
“我们知道错了,已经向您道歉了,也愿意赔偿您的损失,您还想怎么样嘛?”年轻人,通常也不喜欢别人啰嗦,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情绝不分成十句来说。
大叔瞪了他们半天,最后恶恶地说了一句:“赔钱。”
其实还是要钱。
那两个人相互看了对方一眼,又开始翻背包,背包里的东西大概从来没有整理过,袜子和内裤都被带出来两三件,无情地缠绕在一起。好似还有一股恶心的臭味,我下意识地偏了一下头,这一偏头竟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路牌。
是的,下一站就是那个站点,一辆往东,一辆往南的火车会同时在那个站台停留十分钟。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我抬起头看了一眼背包和行李箱。行李箱里装的都是换洗衣服,那个背包,背包里还有一张工资卡,经理承诺过会给一些分红转账到这张卡里,所幸背包的重量远比箱子轻。
背包可以带走。
但是,身份证,大叔到底会将我的身份证放在什么地方?我仔细地打量着他,刚才那两个年轻人给他钱的时候,他接过来直接塞在裤子口袋里的。有些人没有使用皮夹和包包的习惯,也就是有可能我的那张身份证跟他兜里的现金混在一起。
我的目光有意无意地看向他身上的口袋,其中他的外衣口袋有四个,裤子口袋有两个,时间越来越紧迫,广播已经在提醒,还有几分钟到站。我心下一横,要不要直接将他打晕,再搜身?但是,很快我又否认了这个想法,这是在列车上,列车上只要有异动,热心的乘客都会拨打列警的电话,有嘴的都说不清,何况我这没嘴的。
这时,火车上的售货员推着小车过来了,一路走一路吆喝。
大叔要买水,冲着售货员小姐一招呼,她将小车停了下来,这个时机刚刚好,坐在大叔左手边的我在他站起来那一瞬间手指已快速查探过他右边的三个口袋,三个口袋我都找过,没有卡片之类的东西在他身上。他买好水坐了下来,我却站了起来,一伸手将售货员给拦了下来。
“小妹,要点什么?”
我跨出一步站到大叔的右手边来,他右手边的这三个口袋我没找过。我随手拿了一瓶饮料坐了下来,售货员小姐嚷嚷起来:“妹子,五块钱。”
我只管拧开瓶盖喝起饮料来,她说的话我根本不理会。
这时,大叔又站了起来,同样在他站起来的一瞬间我又将他左边的三个口袋查探过了,依旧没有卡片之类的东西在他身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衣服里边还有隐藏的口袋。火车晃晃悠悠地停了下来,此刻的我是心急如焚的,多耽误一秒,前途多一分危机。
一直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个戴眼镜的男士突然开口说话了,不说他说话的对象是大叔:“大哥,出门在外的,财务要保管好。”他说得很含蓄,大叔没听懂他的意思,直点头:“说得是,说得是。”
这位绅士见大叔的榆木脑袋不开窍,不免替他急,一急之下直白地点了出来:“你旁边的小妹妹一直在翻你的口袋。”
已经到这份上,不用说得更明白了吧。
大叔那黑黢黢的脸变了,好似要将我给吃了似的放出恶光来,他往怀里一掏,拿出我的身份证亮在我眼前,我一伸手要去抢,他却比我更快一步地将身份证从窗口扔了出去,我跳起来,将架子上的背包拿了下来,两根带子往背后一穿,吊背在背上。大叔的脸涨得红通通的,嘴里颤抖着朝车厢里喊:“来人啦,我媳妇要跑啦!”
“咦,这好新鲜。”那两个淘气的年轻人原来一直没走远,听见他的呼喊第一个凑了过来,我左右一挥肘勾住他二人的下巴直接将两人放倒了。
“哎哟哟,大叔,你这找的不是媳妇吧,好像是个练家子,是不是在哪买的媳妇,又叫人给坑骗了吧,哎哟,你说你何苦呢,留着钱自己一个人乐呵乐呵的吃光花光不是更好,都丢给人贩子,不划算哟。”
另一个人喝道:“这叫啥,这叫啥嘛,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那两人被伤了下巴,还不忘挣扎着爬起来一唱一喝的调侃大叔。在他们卖力调侃的时候,我已经用最快的速度下了火车,下了车的我一直在周边找大叔扔下来的身份证。很奇怪,刚才他扔的明明是这个方向,怎么找不着。
这时,那边的火车已经开始动了。
哎,算了。
看来这是天意,历史当中,我曾掉过一次身份证,很巧不巧的,恰好就在2008年,我快跑几步追上了已经慢慢挪动的往南行进的火车。车门是紧闭的,我扶着车把手,在寒风中熬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火车到下一站时,才趁着夜色混了进去。
混进南下火车的我待在一个车厢里站着,此时已是下半夜,天气越发寒冷,我又是跺脚又是撮手,艰难地熬着每一分每一秒,又过了一站,有人下车,他将我叫到一边指着他的位置:“坐这边。”
我点头。
一挨着座位我经不住困,趴在桌子上睡了起来。
可这样的天气,这种老式火车只能是越睡越冷,即使冷我也不想爬起来睁着眼睛到天亮,在我不停地跺脚的时候,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往我身上盖,轻飘飘的,我稍微一动,那东西掉下来了,接着,又有人将那轻飘飘的东西盖在我身上。
当我听到哗啦啦的声响时,我明白了,那是报纸。
是谁往我身上盖报纸?
动作和方向来自我的左手边,我没抬头,眼睛瞟向旁边的一双鞋,那双鞋子是工地上的工人常穿的劳工牌的鞋,可能人家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吧。
在一堆报纸的覆盖下,我一直趴到天亮。
这么着趴了一夜更觉得疲惫不堪,天亮了,应该离广州不远了,按理说我应该高兴,可我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身份证没了,钱也没了,除了背包里那几件无关紧要的东西,我几乎一无所有。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待会,我怎么出站,出站是要检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