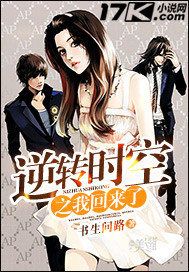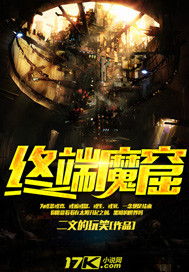胖子那边收工了,她躺在一堆报表,账目中睡着了。
睡着的她显得很疲惫。
所以说,有谁认为做老板是最轻松的?
可是,既然选了,总归是跟这一行有缘的吧。
我默默地收拾散乱一块地文件,靠坐在沙发边一闭眼睛便也睡着了。梦里,梦见一座奇怪的房子,房子里的摆设看起来很简单,安分。
司马舜意走了过来,他的手里提着一个大木头箱子。我很好奇他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我便问他:“可不可以让我看看箱子。”
他说不可以。
并解释说,箱子是他女朋友的。
我突然醒了过来。
明知道将来是这样一种结局,何必还要作践自己。
我坐在电脑桌前,茫然地看着键盘,这时候的电视剧堪称最为辉煌的年代,很荣幸,不看脸不看CP,立求精益求精,例如印象中某江湖中数一数二的高手有一个兵器库,到那个镜头时,还真的出现了一个奇怪房间里陈列的各式各样的兵器。人物,性格,事件环环相扣,哪怕穿的衣服是冷色调,背景并不华丽,我们总会被莫明地吸引进去。各种题材的影视剧那时都能名噪一时。
从小,我就喜欢看港台古装剧。
打打杀杀的,很快意恩仇,我握着鼠标点了浏览器。挑了一部看过很多遍的电视,双音听得很费劲,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地饿。
我在屋子里找了一圈也没找着吃的东西。
向来不嫌麻烦的我,可以为了一小块点心跑上几里路。
巷子口的南瓜饼,闻着空气里的阴冷,我带了一把伞出了门,可能这种清冷的天气,路上行人不多,走着走着就觉得周身莫明地涌上一股寒气,我加快脚步直奔那个巷子。巷子口卖饼的阿婆每天晚上都在那个位置摆摊。阿婆的饼做得香甜松软却不油腻,前来买饼的人都是闻香而来,她用的油是自己种的花生榨的花生油。
五毛钱一个的南瓜饼,用花生油。
怎么算都是奢侈。
“阿婆,我要三个南瓜饼。”
“好,好。”阿婆颤抖着手帮我装饼。
“阿婆,还有多少饼没卖完?”
“不,不多了。”仍旧是颤抖着。
“都拿给我吧!”
其实也不过是多了一个,总共四个南瓜饼,于我们而言,只是几口填肚子的粮食,阿婆却要忙活很长时间,我见过奶奶做类似的饼,所有的过程我都清楚,只不过我总是嫌太麻烦很少自己动手。
“阿婆,收摊回家吧!”
我不知道她家还有几个人,是不是只有她一个人待在家里,我从来没问过她,也没跟其它同样买饼的人打听过。
其实,只有一个人在家也许更好。
不然呢,这么大年纪的人还在外边奔波劳累,而家中的人只怕还会嫌弃老人家,不管做多少事都得听那些闲言碎语不是更可怜。
我拎起一块饼往嘴里塞,这会吃得高兴倒忘了看电视剧那个事了。
天空飘起雨来。
横着飞,撑着伞都没意义。
一头一脸的水雾。
我小心地护着南瓜饼,一向不喜欢浪费粮食的我,宁可淋湿了头发和衣服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粮食被糟蹋,最后不得不扔进垃圾桶。那会让我很不自在。
“哎,你怎么在这?”
我将伞移开,眼睛看向说话的人。
他站在我的对面,眼睛又黑又亮,炯炯有神地望着我,我不说话,他看着我手里拿着的南瓜饼,很自然地走到我面前,从袋子里拿出一个饼很优雅地吃起来。所谓地优雅,我不知道是不是天生,可是连吃东西的时候气质都还区别于其它人,只能说优雅了吧。
我怔在那,半晌。
反应过来,他的喜好,性格与我有90%的相似,我喜欢吃的饼恰好他也喜欢吃,就像眼前这南瓜饼,他吃完一个赞不绝口。
以前,我跟他一起在外边散步,看到小吃摊总会忍不住停下来,他老是一本正经的说什么不卫生,没有营业执照,不知道是不是黑作坊搞出来的。说完之后,却跑去隔壁的摊子上狂吃麻辣烫。我忍不住怼他:“这不是小黑作坊做出来的?”
“当然不是,现煮现卖的。”他一边吃还一边朝我嘻嘻笑。
狡辩!
我懒得跟他浪费唇舌,他可以吃麻辣烫,那我也能吃的吧!
他瞧着我龙卷的速度终于停了下来:“别别,你胃不太好,还是吃些好消化的吧!”说着将我手里的东西给全抢了去。
两只竹签单调地悬在半空中,特么尴尬。
“那个阿婆,还在那边吗?”
“她回家了。”看样子,他也常来,按年龄推断,他这个时候还在学校念书,可他说有自己的公司。我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仔细一想,有没有公司的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还想多买几个呢。”他仰头看着天空,这是他的习惯,老喜欢抬头望天,曾经我还取笑过他,“天上有什么好看的?”
“没什么好看的。”他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可是说话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抬头看着天空。
我撇嘴,这样还能愉快地聊天吗?我也学着他看天空,可是天空上能有什么啊,蓝天,白云,我别过头气哼哼地:“那你一直看天。”
“我看会不会下雨啊!”
这算冷笑话吗?如果算,那他司马舜意也是冷笑话的鼻祖啊,绝对比那什么卫视的冷笑话大王还鼻祖。
“不如用鼻子嗅一嗅,动物都是用鼻子来闻天气的。”我也调侃他。
他撇着嘴,哼出一声:“你来嗅一嗅。”
“你来。”
“你来啊,这主意是你出的。”
这算欺负人吗?我摇头。
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我们那么幼稚,可是幼稚的人总是会成长的,等到成长以后,关心的就不是天空中的蓝天白云了。
而是生存。
“你没吃晚饭?”话一出口我又后悔,我这是在干什么,关心他,他值得我关心吗?话说,我不是应该抽脚就走人吗?
他半张着嘴,眼神里闪出一丝柔光。
“要不,你请我。”
说完之后又补充:“开玩笑的啦,要请也是我请你,想吃什么。”
“不用了,我是下来替我朋友买的。”
他的脸色闪过一丝不自然:“是男朋友吗?”
司马舜意总是这样,假如我说我跟朋友一块,他会脸色很不友善地自以为是男生,不管解释还是不解释,他误认为是就是,我很佩服他的揣测能力,于是我点头。
他半咬着唇定定地看着我,说的却是另一个人:“那他可真是不称职,这样的晚上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出来。”
“是我自己要出来的。”所谓的不忍心,不放心只发生在两个人初相识,初相恋时吧,多走几步怕累着,不管走到哪里都要陪着,即使不陪着也时时叮嘱。
“到了那边要报个平安。”
不再爱时,多看一眼都嫌晦气。
这就是人性。
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堵得慌。
“你跟他感情很好吗?”他倒是不看脸色。
他,我未来的丈夫吗,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吧,中规中矩,不会花心思,也不会欺凌弱小,会讲道理,论外形,谈吐和气质是比不上他的。
“挺好的。”
“我送你回去吧!”
我想拒绝,他却不由分说的撑起了伞,只不过,我在伞下,他在雨中,果然,还是老样子,他的脚步放得很慢,好像是故意放慢的。我知道,其实他走路是很快的,恨不得飞起来那种,然而快而稳,从不莽撞。
两个人并肩走着。
因为住得不远,很快就到楼下了。
“你住的地方还不错啊。”
“朋友的租的房子。”这算不错吗?楼层与楼层之间相隔的间隙不够宽,碰上阴雨天气,一到三楼有如乌云压顶,原本,胖子是想将售楼部那边空置的楼层装修一下再入住,是我说怕坏了规矩,所以才在外边租房子的。
其实,胖子可以买房子。
她怕我一个人孤伶伶的没个人陪,所以才租了这套房,还好我们住得比较高,楼上空气好,视野也好。
“哦!”他目送着我上楼,仍旧站在下面望着。
胖子已经醒来了,她瞧我站在窗帘边上看下面,探着个脑袋看过去,“哇,是司马舜间这个大帅哥。”她跳了起来。
她的记性倒是好,我退回到桌子边坐着,不咸不淡地挖苦道:“不管长得多帅,再过几十年都是糟老头。”
“哎呀,你好扫兴,长得帅看着赏心悦目,心情愉快。”她恨恨地。
“能当饭吃?”也许我曾经也是这样的审美观,挑男朋友一定要长得赏心悦目的,后来,才发现,不能光看脸,性格脾气和容人之量才是最重要的。
“嗯。”她点头。
我差点吐了。
“没想你还挺招桃花的嘛,加油,看好你。”她拍着我的肩膀。
我白了她一眼:“你那边整理得怎么样了,肖音可是随时准备踢馆的。”
“别提了,要整理好这一堆东西至少也得一个星期。”她叉着腰环视着这一屋子的各种表格,又摸着额头叹气,顺势倒在我的肩膀上:“帮帮忙,别催我,行吗?”
我斜着眼睛瞧她:“行,我不催,别跟我撒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