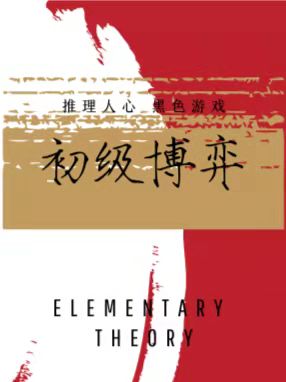宴绝跟妘夭两人连夜骑马从百越赶赴就近港口,一刻不曾停留,只因暗桩传来消息,千阖离世了。
妘夭对这位师祖没什么感情,只知道他平日都是不苟言笑,自从宴绝坐上少城主的位置,又加上扶窨在旁辅佐,没什么大事千阖基本都在天海城闭关,不见世人。在她眼里,千阖很强大又很神秘,就像传闻一样,等同于神的存在,一直支撑着整个天目峰。而如今,这个神明,竟然离世了。
就算她再怎么无感,也知道天目峰这个担子的沉重。夜色里,狂奔不止的马匹终于在港口停下来。那里早有暗桩等待,见两人下马立刻迎上来,“少主,船只已备好,随时起帆。”
宴绝快步不停,“出发。”
“是。”
两人路过码头告示栏时,妘夭无意一瞟,单就这么一眼,便瞪大了眼睛。告示栏上贴着的赫然是一纸婚书,这般昭告天下,实在叫人羡慕这男女主角,只是那署名刺眼,妘夭停下脚步,只以为是眼花。
行远的宴绝停下脚步,回头唤她,“还不快跟上。”
妘夭傻愣愣哦了声,“来了。”怀着沉重心情快步离去。只是那三字署名深深烙印在心上,叫脚步难起。
告示书:靖将耶古嵘与沣辛郡主于冬月初七日在爻城举办定亲宴。
***
一个月前,沣辛轻潭马场。
这是一块很广阔的平地,几乎可以说是一眼望不到边,这个马场在沣辛很有名,历来是为战士们培养战马的地方,可以说是皇家马场。
平日也有贵族富商来买马或者打打马球,但今日这般人仰马翻倒是头一次。
耶古嵘抱着手臂靠在围栏后,远远的见一堆人围着个蓝衣女子,“这烈马很是倔,郡主千金之躯,还是不要去冒险的好。”
辛留襄气道:“父亲寿辰眼看就要到了,我画没拿到,还能怎么办!”说罢不顾阻拦抓了马鞭翻身而上,这才刚坐上去,面前黑马就开始嘶鸣,伴着大弧度的甩动、蹦跳,只想把背上的人撂下来。
“郡主小心!”众人围着马又不敢靠近,只能在一旁手足无措。
耶古嵘嘴角一咧,眼里透出赞赏。这女子看起来柔柔弱弱,性子却极倔强,一双小手被绳子勒得通红也不放手,不顾安危,一心只想着驯服野马。
几番来回,马上女子显然是累了,熬不过这烈马,额角汗水四溢。突然间黑马前蹄高抬,抓准机会,甩下背上的人。辛留襄手快,抓紧了绳子没被摔下,倒是侧挂在马腹上,马儿一路疾驰,她双手哪敢放开。
一群人跟在马后干着急。
耶古嵘见势,飞身跃上一匹马急追上去,手里抓起一根套马杆,跑得近了,冲着马头一套,跃下地去,死命拽住。一时间马鸣声不断,废了番力道,竟将那马勒住了。
身后一群人赶紧上去,拉马扶人,控制场面。
见情形稳定下来,耶古嵘松开套马杆,拍了拍衣摆上沾染的灰尘,转身就要离开。
“等等!”辛留襄好歹站好了身形,没在外人面前失了她一城郡主的面子。“多谢侠士相救,不知可否告知姓名,也好改日致谢。”
耶古嵘道:“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在下还有要事在身,不多耽搁。”耶古嵘抱拳一揖,“姑娘,告辞。”
“诶……”辛留襄欲言又止。眼见着他出了马场,低头对身边丫头道:“此人身手不凡,看样子不像普通人,如今天下局势紧张,以防万一,知心,你派人去查查什么来头。”
丫头应了,“是,郡主。”
这边耶古嵘才刚离开马场,两个兄弟已经左右围上来,面相俊朗长相汉人一点的男人道:“大哥,你怎么突然收手了?”
耶古嵘道:“这个郡主聪明得很,弄不好会搞砸。”
另一胡子拉碴一看就是异域人,语气都明显野性些:“搞砸就搞砸,不就是个滴点小的封王嘛,看老子不一锤让他见阎王。”
耶古嵘停下脚步,叹了口气:“四弟,你能不能收收你这性子,我们是来结盟不是来攻城的!”
步陵昭噗嗤笑出声,“四哥,你可真是我见过的最爷们的人了,佩服。”说罢还抱拳作了一揖。
牧恪然一挥手,“去你的。”转而道:“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步陵昭想了想,道:“大哥既认为亲自送画给那郡主不会得到青睐,反而容易弄巧成拙,那接下来就只能亲自将画送给爻城主了。”
一开始想的确实是先引诱这个郡主,可一看到手中的画又忍不住想起那个白衣女子,自己堂堂三尺男儿已经为了一幅画去骗取女子信任,今日又怎么下得了决心再去利用女人来达到目的。心中这么想,话自然不能这么说,他点点头,“这个留襄郡主费尽心思画都没到手,若我们今日堂而皇之地拿去献给她,不是明摆着惹她生疑,还是老五说得对,送去爻城主那,我们直明来意。”
九月二十三,爻城城主辛远晁五十岁生辰。
此前三日,城中就已经热闹非凡,因城主开明,统领有道,百姓十分爱戴,这次整寿诞,自然与民同乐。
隔间宴席上,辛远晁看着辛留襄,恨铁不成钢,“听说你从月前就开始忙碌,怎么最后也没见画送来。”
辛留襄心有不甘,委屈道:“是女儿没用。”
他伸手,旁边侍女立刻递上一卷卷轴。将卷轴往她面前一放,面无表情道:“你看这是什么。”
辛留襄打开一瞧,正是自己费尽心思也没得到的潇湘图,“父亲,这是……”这画明明是被那白衣女子带走,怎的会出现在他手里。
辛远晁起身踱步道:“这是耶古嵘送来的。”
“耶古嵘?”辛留襄疑惑:“父亲是说靖远中将耶古嵘。”奇怪,他怎么会有这画,送这画来又是有何用意。辛留襄不解。
辛远晁背着手望着楼阁下的大街,眼神里有着盘算,“他送画贺寿表明来意,说愿与我国结盟,共伐沅康。”
辛留襄站起来,“父亲您答应他了?”
辛远晁没有立刻回答。他有自己的考量,也坚信自己看人的眼光。“你还记得岳升吗?”
辛留襄点头,“父亲说过,沅康大将岳升是我辛家一辈子的敌人。”
辛远晁握起拳头,狠狠道:“当年他断我一指,此仇总是要报的。”
半个时辰前,内阁。
辛远晁坐在主位上,看着面前三人,沉着道:“耶古将军不请自来,不知有何用意?”
耶古嵘坐在下首,面对辛远晁压迫感十足的气场没有丝毫怯懦,反而谈笑风生,挥挥手,让步陵昭承上礼盒,“听闻郡丞五十寿辰,自然是来贺喜。”
看着桌上的礼盒,辛远晁没有多余动作,“我是个直爽的人,有什么事大可说来不必弯弯绕绕。”
“如此!”耶古嵘耸耸眉,起身抱拳道:“请恕晚辈无礼。当下沅沣起战,边城已经数次战火,百姓苦不堪言,贵国虽没有败,但也绝没有全胜。”辛远晁面无表情继续听他道:“我想此时,如果有人助贵国一臂之力,那形势就截然不同。”
辛远晁挑眉,“你的意思是要助我?”
耶古嵘道:“不是助郡丞,是互惠互利。我今日前来,是为我主陛下向贵国结盟,他日攻下沅康,土地你我各半。”
辛远晁冷笑,“你倒是好大的口气,不怕噎着。”
耶古嵘也笑,“郡丞是聪明人。我主是第一个向贵国伸以援手的人,不该拒绝,毕竟时间一久,难保不会有第二个相助沅康的朋友,到那时……”
辛远晁猛地一拍桌子,“你是在威胁我!”
耶古嵘笑,“不敢,晚辈只是在说实话而已。乱世已起,当今八国无一能除外,即便各国互不相干,贵国赢得胜利,郡丞敢说沣辛得两国土地,兵力减退下还能护国无虞?”
谁也不是傻子,谁都想着钱财土地势力,更何况八国主君,都是踩着血肉上去的魔鬼,没有人是善良的。
“郡丞可再想想,他日想通了,可来信靖国找我。”说罢,作揖准备离去。
临出门时,“等等!”
耶古嵘回头看他。
辛远晁起身将礼盒掀开,笑了笑,“结盟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你可愿表明诚意?”
“哦?郡丞请讲。”
“我要你去杀一个人,将他的手指送来。”
“何人?”
“沅康大将,岳升。”
***
宴绝走后,墨叔若并没有受影响,反而愈加斗志昂扬。从信陵墓室带回来的黏土,她观察后,心里似乎已经有了大概的结论。次日禀告百越侯,带了几个人便直接去了陵墓地面查证。
信陵宏伟,地表虽然只耸立着几十座金殿,地下却四通八达,弯弯绕绕上百座陵寝,再加上耳室、殉葬坑,规模可说史上第一,没有哪个朝代能及得上。
而如今眼前所见,空旷无人,如常的荒山野地。项景佾看了她一眼,又去打量四周,确定安全。十来个人站在山坡上,只静静等着墨叔若差遣。
她俯视着眼前的景象,静静思考着什么。
眼前荒地杂草丛生,远处又是几座相连的深山老林。她不太懂风水,但实在不明白荒地上为何积水成沼泽了都。照理说,陵寝地表是不可能修成碗状。无论哪个朝代,皇家陵寝都会很注重排水系统。这么奇怪的景象,不让人怀疑都很难。
冷风呼啸,她回过神,手指习惯性地敲了敲腰间竹筒。“文书大人,这里以前就是这样的湿地吗?”
一个长者回话道:“以前不是这样的,但最近也不知怎的就积了水。”
“最近?”
“是的。出事前最后一次巡查是半年前。”他递了张图纸给她,“图上画的是如今的积水区域。”
项景佾凑过来看了,分析道:“只有少部分地区积水,而且还是容易改变的边缘地区。这可不像天然而成,有选择性的,看起来更像是人为。”
墨叔若没有否认,继续问:“地宫排水系统可还在?”
“排水系统还是好的,只是成片的水域存在,时间一久,总会下漏。”
墨叔若咬着食指,她一想事情就喜欢咬手指头。
莫非真是这水有问题?
疑上心头,招呼众人小心靠近湿地。
远处树林白雾蒙蒙,偶有野鸟从高空飞过,呱呱乱叫。她弯下身子就着面前的水坑细看,那水呈黑色,偶尔还会从水下鼓出几个泡,从水中拔出一根枯萎的杂草,见其根部漆黑一片已经完全腐烂。
项景佾不确定道:“这水是否有问题?”
墨叔若点点头,扔掉杂草后,随手用身上的小瓷瓶装了些湿泥,“墓室里漏下的水应该就是这种。”她站起来对身旁的侍卫首领道:“这水怕是有毒,以防万一,多派些人把这里围起来,最好让侯爷颁布禁止令,不要让人踏入这里。”
“是。”
她一边往回走,一边继续吩咐:“还有,派些人就方圆百里之地的墓地看看,是否也有这种黑水的出现。一经发现也最好派兵守着。”
“属下定照办,墨姑娘请放心。”
回到百越府,墨叔若将两种土质一相比较,立刻就证实了心中所想。
土质中含有一种肉眼不能看到的细小蛊虫,且数量大得惊人。她记得曾经在天目峰蛊书上看到过这种蛊虫的记载,学名唤作食尸蛊,顾名思义,也就是遇到尸体以后,会吃掉脑内残余组织,特别之处在于,这些微小蛊虫团结在一起,却能令死尸神经组织再次发育,并能控制死尸像正常人一样进行活动;恐怖之处在于,因为蛊虫需要鲜血维持生命,死尸是会咬食活物以汲取养分。
尸体本身不会动,可世上有一些恐怖的人创造了让尸体动起来的方法。
“叔若。”木门被轻叩两声,传来项景佾的声音。
她从思绪中回神,收好桌子上的湿土,起身去开门,“有事吗师兄?”
项景佾拽住她就往外走,一边神秘兮兮道:“我带你去见个人。”
她脸唰一红,竟然立刻想到了宴绝,随后暗骂自己一声疯了,弱弱问:“谁啊?”
“见到你就知道了。”
怀着一肚子疑问被项景佾拉到大堂,那堂里有数人站着,上位处有两位老人正在拉家常,谈的不亦乐乎。
墨叔若大眼一睁,瞬间停在门口,下一刻突然一声惊叫:“爷爷!”
墨公回头一看,笑道:“叔若来了。”
她大步走进去,看向墨公身边的墨守政时老实喊了声,“大伯。”那中年男子点了点头,算彼此礼貌问候过,她这才对墨公道:“爷爷怎么来了?”
墨公道:“我一把老骨头窝在家里不舒坦,趁还能动,就想多跟你百越伯伯说说话。”
墨叔若一脸怀疑:“是吗?”
她正待唠叨两句,墨公仿佛知道似的,忙看向一旁的百越侯,“老古,你看起来身体还好得很嘛!”
百越侯道:“那是当然,我可没有你能耐,日理万机啊!”
墨叔若鼓了鼓腮帮子,长辈讲话她插不上嘴,奈何又有大伯在侧不能随意使小性子,一时气得大眼直发亮。
夜幕降临,墨公临睡时墨叔若突然蹿进房门瞪着两只盘子似的大眼莫不作声盯着他看。墨公咳咳两声,吩咐收拾洗脚水的侍者:“你下去吧。”
“是。”
待侍者低眉关门出去了,墨叔若嘴角一牵,立马从桌子边蹭到床边上去,嘿嘿笑道:“爷爷,您是不是把我给卖了!!”
墨公眉头一挑,看向一边,虚心道:“什么卖不卖,爷爷记性不好,忘了告诉你嘛。”
墨叔若咬牙道:“爷爷你怎么可以这样!婚姻大事,说给活人就算了,你却给答应个冥婚,这是想气死我啊!”
墨公道:“也没人勉强你,况且又不是马上就嫁。”
墨叔若无语,静了下心,想到他千里迢迢赶过来,又满腔心疼,“这边案子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您干嘛还亲自跑一趟,这么远的路程,马车颠簸您身体受得住嘛!”
墨公拍了拍她的手,笑道:“你不用担心,爷爷这把老骨头还没那么弱。”转而问:“倒是你,伤口怎么样,还疼不疼?”
她抱着他半边手臂,靠着他的肩膀摇头笑:“不疼,都好了。”嘿嘿一笑:“爷爷,我好想你哦。”
他笑着拍拍她的手背:“傻丫头。”
她望着桌上的蜡烛,呆呆道:“爷爷啊,我这辈子都不嫁人了,就陪着您好不好。”
“嗯?”墨公伸手把她撑起来,“说什么傻话。”
墨叔若道:“我说真的。”
墨公打量她神色,仿佛看出什么来,“我家叔若是不是看上什么人了?”
被他一语戳中,墨叔若眨巴着大眼,吞吞吐吐反驳:“爷爷你瞎说什么!我、我只是想陪着你嘛!”
墨公摸着胡须,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让爷爷猜猜那个人是谁。就最近接触的人……嗯,景佾?他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一表人才,心地也不错……”
墨叔若羞得一脸通红,“爷爷!你不要乱说!”
看她反应激烈,墨公道:“难道不是么?那再让我猜猜……”
墨叔若捂着耳朵直跺脚,“啊啊啊啊!!我不要听不要听!!!”
“哈哈哈哈哈……”墨公大笑不止,终是不再逗弄她。
两人说了一会子话,等墨公睡了,她才轻声关门离开,回到自己房里的时候忍不住泪水盈盈,因为觉得自己有这样爱她的爷爷,她觉得很满足,即使父母早逝,她却还是很幸福。深吸一口气,振作起精神,迈步去桌边点灯,烛台才刚拿到手中,后脑勺突然一麻,整个人就不自主地双眼一闭,往后倒去。
烛台铛啷一声掉落在地,一个黑影扛着她迅速从窗口跃出。
黑夜风声不断,摇得满院常青树哗哗作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