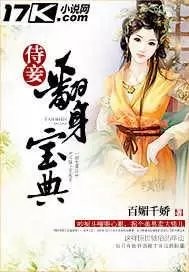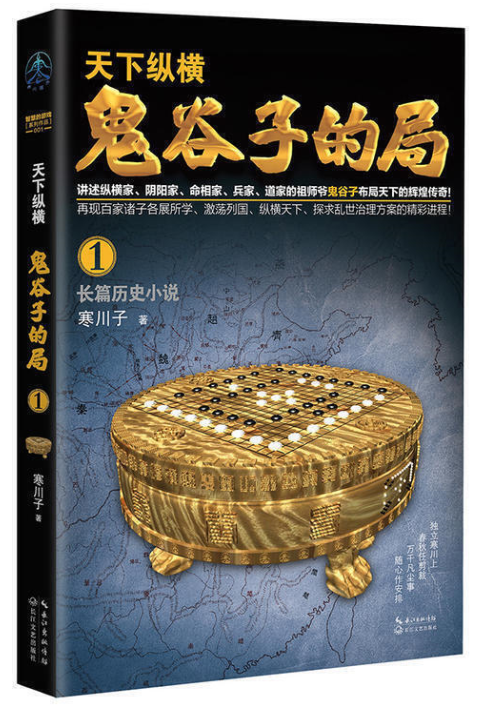按子素以往理智沉着的气性,定要给三喜解释为何去北府。
三喜一根筋,爱憎分明,只想到北府有意害她姑娘,不曾想子素去找猪,并非真找猪,而是找菊儿说的潲水解毒偏方。
子素没给三喜说明,有意让三喜跟自己一样憎恨北府 。
两人就此出院门。没跟慧缘打招呼。
出了镜花谢,才走到中府外头那棵槐树,远远见几个人从西府道上走过来。她们也不仔细去张望,只快步走向北府那道上。两人走远,自西府而来的人到了槐树下,望住三喜和子素。
这几人便是关先生、阿玉、瓜子还有庄璞、湘莲。
关先生身子依旧不大见好,入京以来受些寒气,如今行动还拿着手绢捂嘴咳嗽。只见关先生穿一件深青袍子,外罩一件黑面白里子的披风,披风拖及在地。出来时,庄璞特地让湘莲回去取给他的。阿玉随常穿戴,头上点了两支绿翠,一身鹅黄通身袍裙,比先前看起来略端庄几分,手中托个布包。瓜子在身后则抱那口小古筝。
几人站在槐树下看子素远去。庄璞笑对关先生道:“关兄请。”
庄璞引请,关先生才移回目光,跟在庄璞边上走,直进中府。
进中府大门,看到几个丫头子在晾晒衣物被褥,梅儿坐在廊下嗑瓜子,其他角落处或有丫头三五一堆低声说笑,或有婆子在打盹。
梅儿见人进来,连忙把手中的瓜子撒开,手急急抹在裙子后头,笑盈盈迈开碎步走下台阶,迎到庄璞跟前,深端一回礼,笑道:“二爷。”
庄璞用眼神勾望住梅儿,道:“老太太午睡呢?”
梅儿笑道:“是呢!他们都偷懒打盹去了,叫我守着看。我怕自己走眼了,这一帮没眼色跟着偷懒。二爷怎么来了?”
庄璞看了一眼关先生,继续笑道:“来看看老太太,顺道瞧瞧你。”
梅儿心中一阵欢愉,脸色立马绯红起来。站在庄璞跟旁的湘莲轻轻咳了两声,梅儿听到忽然不好意思,又侧身对关先生端了一回礼。
湘莲才道:“关先生要出去了,想过来给老太太告个别。听说琂姑娘身子不好,顺便来瞧瞧。二爷说瞧你,你还信了。可见你也是没眼色。”
梅儿嗔怪地朝湘莲奴嘴,道:“如今可不也顺道了,湘莲姐姐的嘴巴整日是裹蜜儿似的的,今儿竟说这话。”扭身便回廊上去,不愿再搭理庄璞等人。
关先生、阿玉忍住不笑,见梅儿走,关先生才对寿中居打了个躬。完毕,庄璞伸手往镜花谢那方引请。
进镜花谢院门。
众人一眼见到院中花草如茵,栽种丰茂,围院檐上,秋枝萧条,几只鸟雀扑哧飞跳,地上淡淡散散一层枯叶。
因这般寂静,湘莲道:“平日她们都在院子里头。姑娘身子不好,兴许都在里头。我先去应个声。”遂先身去。
关先生和阿玉知礼仪,停住,等湘莲去招呼一声,他们便在院子小站,欣赏周围。庄璞不好让人站着,就请关先生到石桌凳子坐,才刚举步走,湘莲和慧缘从里头迎出来。
湘莲笑道:“姑娘原睡了,才醒。”
慧缘给诸位端过礼,道:“姑娘说客人来,她身子不适,不便来迎。让我请客人进去。”
关先生和阿玉分别给慧缘回了礼,之后跟慧缘进里间。
从厅穿过,所见布置,素雅墨气,点缀之物不如西府那么华丽气派,随意抬眼看到,是些石头盆景,或是瓶子摆设,画轴林树,只有帘子那些花色珠子有些夺目,其余确过于暗淡,不似女子闺中院舍。到里间,稍比外头好些,布幔纱窗色彩淡雅,那窗上倒挂有翠色鹦鹉,窗边有一桌,桌上整齐摆设些书籍,还有各色墨台笔号,桌子后头墙上挂一幅《步撵图》,靠近墙角立一口大花瓶,瓶上只插一干形态曲折的枯枝,枝上开着些白花,甚是别致,仔细一瞧,并非真花,乃是用棉花揉出来的朵儿,粘在枯枝上。
阿玉看到那墙角的摆设,心中奇怪,禁不住望了关先生一样,会心笑了。
关先生没敢走眼四处看,徐徐向炕上的庒琂施礼。
庒琂因听到有客人来,开先从卧内出来,如今躺在炕上,盖着老太太给的那床鹅绒雪被,笑向关先生等颔礼,伸手请坐。
庒琂道:“二哥哥怎么忽然跟先生和姐姐们来了,提早给我们说一声,我也好准备茶点。”
庄璞让湘莲挪过椅子,请关先生坐,自己在炕另一头坐下,才回庒琂道:“妹妹不用客气。关先生原是要走了,因听三弟说妹妹身子不好,才过来看看你。”
庒琂看到瓜子抱那把筝,心中有一半知晓那关先生和阿玉并非无情之人,可庄璞也没明说两人来的真目的。
当下,慧缘端来茶水,逐一捧献。
庄璞环一眼屋子,叹息一声道:“这许久我也没来瞧妹妹,这会子算是来了。看妹妹这屋里清淡些,如不然给添置点什么。”
庒琂感激道:“二哥哥有心了。我院里人少,也没什么人爱走动,不用太奢华。虽说二哥哥没常来,心意总是来的。”故笑看一眼湘莲。
湘莲低头笑道:“可不是了,二爷那次还说让我多谢姑娘。”
那次,就是湘莲被郡主罚的那次,还有庄璞偷玉如意,庒琂解围那次。
庄璞显得有些囧态,笑了笑道:“自然的,妹妹这里与别的地方不一样。”便不说了,引请关先生用茶。
庒琂心中默默笑,把眼从庄璞脸上移开。
见各自不说话,气氛有些冷,湘莲道:“姑娘身子可好些了?”
庒琂轻手捂那伤口外出,疲倦道:“用了老太太和诸位太太给的药,又有大夫诊治,好些了。”
湘莲点头,故向阿玉那方道:“先生和阿玉姑娘都要走了,临上马车,阿玉姑娘还是说不放心想来瞧瞧。”
庒琂含笑对阿玉端礼,感激道:“多谢玉姑娘。”
阿玉回礼,道:“左不过服侍一个久病之人,看不得有伤痛的。心里总想个个都康健如常,我自己也心里安乐。”
庒琂客气道:“那是玉姑娘心地好,先生有姑娘在身边,那是人间大美之事。”
阿玉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这才想起手中拿的布包,打开来,从里头取出一个精致陶罐子,罐盖顶了木还包有布,她正要拧开罐盖,拧几下没动,关先生伸手接去,拧开了。
关先生将罐子递向庒琂,道:“蜀地热气重,我们时长都带这些败火降毒的药。听说姑娘体内发热,想着姑娘用得着。”
慧缘接去给庒琂,到手中一看,罐子里头余有小半罐白色颗粒丸子,抖一粒出来,猛然闻到一阵清香。
庒琂十分感激,再三言谢,道:“这药儿看着不寻常,应是十分贵重。舍我几粒便好了。”
阿玉道:“蜀中家里还有,才分了些路上备着。这些姑娘就留下。也不是十分贵重,用了徽地白凤花瓣做成的,在我哪儿常见,只里头包那些药难得,若不是先生在蜀中拿得到,炮制合成,世上也无这药丸。”
湘莲听着奇怪,过去接过庒琂的药丸,看看,闻闻,眉开眼笑道:“有一股清甜的味道,跟薄荷蜜饯果儿一般。这可怎么做的?”
阿玉看了关先生一样,有不太想说的意思。
关先生只笑,不答言,庄璞垂眉喝茶,一副悠然。
见都不说话,庒琂接湘莲的话问:“是呢!如何做的?我也好奇。”
阿玉叹息道:“若说这药,比那古书里头说的海上方略容易些,东西极低贱。制成它,需耗费些时间心力。姑娘看到外头是白色的,那便是白凤花掺蜜汁炼成的,里头比外头的复杂多了,俱是黑色物儿,要说那物儿都有哪些。说起来费神,听完姑娘你就不愿吃了。”
庒琂道:“凡奇物皆有奇相,玉姑娘愿分享与我们听,我们也长见识。但说,不愿吃,那就折费姑娘和先生的心意了。”
阿玉推不过,只好说:“蜀中巴山林木居多,又是高山。古有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见奇物必在青天之间了。姑娘可知奇毒无比的蛇?其中的药引就是用毒蛇的胆汁来做,又有青城山毒青峰尾尖,加上生长在毒菌上的红蚂蚁,再者便是千足地龙。”
慧缘惊讶道:“那此药不是奇毒无比的药了?蛇胆祛毒消热不假,可那青峰毒是要命的,即便不蛰,它停在人身上都会中毒,听说那红蚂蚁更是厉害,凡有生灵物长在周围,红蚂蚁爬过皆不能活,而千足地龙不就是……”
庒琂笑道:“《古博经注》记载说,蜀地有千足地龙,每百年长一足,能见一只便是千年的动物了。那地龙就是蜈蚣。是么?玉姑娘。”
阿玉赞叹眼色笑对庒琂道:“姑娘博览,见识过人。所以能制出这药的人不寻常。”
庄璞被激起兴致了,问道:“是何人制这药的?”疑惑看了关先生,“莫非是关……”
关先生摆摆手:“必是高人,我也亏得高人赐药才保得住现下的命。”
阿玉脸面稍侧去,有些不忍提及。庒琂看到阿玉的神情,又看关先生关切望阿玉,心中有几分想到,制药之人应是阿玉心中重要之人。
阿玉嘴尖挂笑,眼中已是有了泪花,轻轻擦了擦,道:“把这些毒物集好,凡是毒汁,须和上灵芝草浸泡,埋于山涧石下半年,取出来后再用枇杷膏汁勾兑,放入适量米酒,调好成糊状,入罐子密封严实,放入粪池内十二个月,待次年头春取出来。这还不完的,取出来开封,看里头的糊状化水没有?若没有再泡入粪池一年。等化了水,又用麻椒树根榨出汁水调进去,灌入蜂蜜,再密封,放入深井浸泡四十九日。此外,将毒尾和地龙晒干,捣碎,研成沫。等深井里的罐子出来,将汁水掺上那些沫子,揉成药心。外头包上白凤,再浇盖蜜蜡就成了。只是,需得高山毒日头连晒四十九日才能吃得。”
听完,众人唏嘘。
庄璞叹道:“这药比那古书上记的海上方还要复杂。万一蜀地没有四十九日毒日头,不白费了?”
阿玉笑道:“就正好制得一坛子。”若有所思起来,她的眼睛更加雪亮,默默道:“有话说,有得就有失。能制得好药的人,未必人人称他为好人。有些病症,外白里黑,看着白未必是白,有些毒,终究敌毒不过人心。所以,这药便叫‘黑心毒’。但愿没吓着姑娘和二爷。”
庄璞连忙摆手,甘心拜服之状。欲求一枚来尝尝,好是湘莲制止了。
正此时,外头传来三喜骂骂咧咧的声音,慧缘主觉的退出去,想让她们注重些,毕竟这里有客人。
可谁知,三喜与子素一路骂进来,是因在北府遭遇奇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