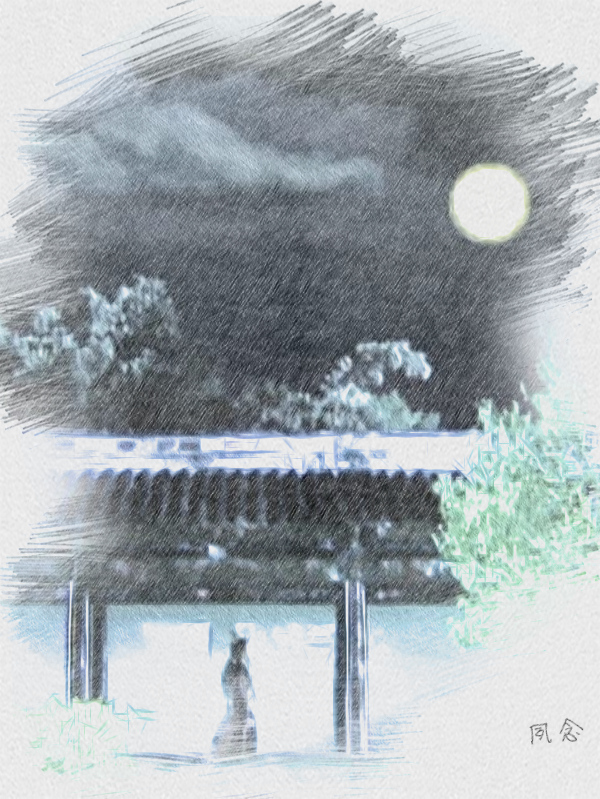庄玝此间屋院死过人,是事实。
庄璞安抚众位弟弟妹妹,又说不能往这儿呆着,得赶紧搬离。头先,他母亲郡主让搬去她那边去。庄璞倒觉得麻烦,不如往自己那院屋去的好。
因事发突然,又见庒琂擦眼流泪,故无人去问她发生了何事,如今,来龙去脉无人知晓。大约等有一会子,庄璞让有力气的丫头来,说将庄玝背上,好出门。
庄玳气呼呼的,说:“且慢着。”
谁想不到庄玳说完这句,便往门外去了。
肃远担心他出去会跟意玲珑发生矛盾,遂而跟出。
二人一前一后到外头。
果然,庄玳一近门外,就指着意玲珑道:“我们要去我哥哥屋里,我来跟你说一声,你是要跟过去,还是永永远远留在这儿守着?无论你跟与留,今夜之事,我们与你不得罢休。”
意玲珑怒目对庄玳,“你”出一连叠,不成语。
肃远将庄玳拉住,尽力往屋里推,道:“不须说的。”
是呢,庄玳乃是庄府堂堂正正的三少爷呢,却给一个看家守院的女“土匪”报备说话,传出去岂不叫人笑掉大牙?
意玲珑道:“我把贼绑来问话,贼自己磕头磕死了,这可赖不得我。我行直影正,走到哪儿都是一条女汉子!要去就去,啰嗦什么。”
原本被肃远拉进去了,庄玳听闻她这般说,又挣扎出来,眼红脖子粗地道:“是了,你是女汉子,如此以往,我们天天祝祷你能赶紧嫁出去!好找个男娇娥过舒心日子!”
意玲珑冷笑,道:“不用三爷费心!好歹我不赖着你,不用你这般惦记。”
眼看二人要吵起来了,屋里的人坐不住,都往外出。
半时,曹营官和张郎帮肃远拉住庄玳,庄瑛、锦书来劝停。
庄琻没出来,则在屋里冷热嘲讽说道:“有些人口里说不用惦记,怕是你惦记我们三爷呢!北府的事儿,你净往西府拉来做什么?不说倒还好,一说我还真明白你心里怎么想的。如今说这样的话,不怕人笑死。”
意玲珑听见庄琻的声音,她想冲进去,可门口堆一拨人在那儿,她不好进,便转身往窗边去,隔窗户,先向庄琻吐一泡口水,之后,道:“这么好的爷,你们自个儿留呗!我也稀罕这个!”
其实,二人也就隔离一墙窗,庄琻听了,恼怒地拍打窗户反击,道:“不要嘴脸的东西,活该你是我们家做守门看院的母狗!也配跟我言语。我呸!”
庄琻越说越气,越气越口无遮拦。
锦书和庄瑛放开庄玳,又往里头劝庄琻。
正闹得不可开交,庒琂走过来,眼目湿润,先对庄琻道:“让姐姐委屈了。”又走出来对庄玳道:“让哥哥生气了,请哥哥息怒。”也不等庄玳等人反应,最后走出门口,往意玲珑边上去,深深给她端了一回礼,道:“姑娘对我不满,对我辱骂任何,我不还口便是。请姑娘休口与我哥哥、姐姐们对骂。”
意玲珑白了庒琂几眼,之后,道:“我站在这儿半日,说过一句半句没?不是你们一个个来惹我的?如今倒成我的不是!话说,你不也是外头来的么?跟我有何不同了,沾亲带故的来指责我,你也配得!”
庒琂听了,脸色急剧涨红,羞耻难耐。
肃远走出来,将庒琂拉住,让她往自己身后站,这才对意玲珑道:“姑娘,你家三爷只来给你说一声,我们要转屋子了。你愿意跟就跟,不愿意跟留下或回你屋去。就这事儿,有什么好吵闹的。再说了,人家再如何,身份地位也是你能比的?到底,你是庄府的什么人?”顿了一会儿,又道:“我是个外人,不合适说这些。可我瞧着实在难以服气,不说不快了。又说好男不跟女斗,这会子我跟你说道理,没与斗气。你们三爷是被你气极了才说这些,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该收住嘴巴声音,以免往下发生更多的不快。”
一口气说那么多,完毕,拉住庒琂进屋。
在门口,肃远对屋里人道:“此处不必留了。”又对庄璞作揖道:“表哥,我们过去吧!往你院里去。”
肃远毕竟是客,能说这样的话,实属难得;又见他血性之气,侠义心肠,不由地,庒琂痴愣看他一会子。
不止庒琂痴愣看肃远,子素也这般。
连屋里站着生气的庄琻也站不住了,稍稍走出来,眼睛里开了情花一般,心神欢喜看他,同时,也是布满了嫉妒。她想,肃远怎对庒琂那样好?要是哪一日,他能对自己这样,自己死也心满意足了。
庄琻因有这样的想法,心中暗暗计划,好歹自己也要吵闹委屈一会子,让肃远替自己出出气。
可惜,没等庄琻计划出些言语敌对意玲珑,庄璞已招呼众人出发,往自己院里走。
众人与意玲珑擦肩而过,都没正眼看她,也没再说什么。
出了庄玝的院子,七拐八弯到了庄璞的院里。
才刚把庄玝放在炕上,外头的人来说,篱竹园的那些人跟来了,坐在院门口台阶下。
庄璞听毕,道:“由得她!”
庄璞院里的大丫头湘莲听小丫头子们报说,便出来看,一看,果然是。因今日有事,湘莲没去庄玝那边伺候,这会子依稀听闻事件经过,有些担忧,她出来看意玲珑,是想确认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再者,想好声劝说,让意玲珑先回去。
院门外。
意玲珑坐在台阶上,离她不远的外头稀稀拉拉站着几个丫头婆子,俱是篱竹园的人。
湘莲不敢轻步出来,隔一道门,笑对意玲珑,道:“哟,大晚上的,姑娘怎往这儿坐呢!”
意玲珑不理。
湘莲暗羞,摇头。想着:这人与府中人真是不同,还是不要招惹她为好。
故而,湘莲进屋去了。
到了里头,湘莲没提及自己出去见意玲珑的事,倒是安排人传茶倒水,又不忘记让人去拿醒酒汤。因不放心别人去,她自己又去了。此处拿醒酒汤,得出院门往大厨房走才能拿得。
再一次与意玲珑碰见,湘莲稍稍停下脚步,对她说:“姑娘,夜晚蚊子多,你不嫌弃我们这儿地方小,可往里头坐去。在门口坐,不雅看。让太太老爷见到,我们又得挨骂了。”
意玲珑还是没搭理。
湘莲见是这样,心想这人是执拗之人,劝不得的了。
等湘莲从厨房那边拿回醒酒汤,经过院门时,不见意玲珑等人的身影。湘莲奇怪呢,左顾右看,也没见,速步往里头看,也没见,心想她们走了。
回到屋里,将醒酒汤端给庄玝的丫头敷儿,让她勺给她吃。随后,湘莲走到庄璞跟前,轻轻拉住他,示意他往里头说话。
到了里头,低声给庄璞说:“怎把篱竹园的人引到我们院里来了?”
庄璞眉宇紧皱,意欲发作生气,湘莲连忙改口,笑脸拂春,道:“我才刚去给五姑娘拿醒酒汤,出门口还见着,回来不见了。想是他们走了呢!”
庄璞紧皱的眉头立即展开,不大相信地道:“这头犟驴子狗还敢溜?”
说罢,满怀得意,撩起袍子往外走。
湘莲后悔极了,追出来,道:“二爷去哪儿?”
庄璞没回答。
正在此时,庄玝吃了醒酒汤,呜啦啦的呕吐不止。屋里的人紧急得不成样,丫头们更是忙得手忙脚乱。湘莲怕吐出来的东西浸脏了炕面,便急转身回来,对丫头们说:“去拿痰盅来!”
一时,拿痰盅的,拿水的,拿热毛巾的,川流不息。当下看着,庄玝俨然是豪门富贵人家的大小姐,跟旁那些人俱是下人。
妥当之后。
庄琻有些怨言了,道:“不能吃吃那么多做什么。好歹清醒些过来,跟我对付外头那没嘴脸的东西才好。偏偏又这样醉迷了。”
说话刚停,庄玝睁开眼睛,醉意朦胧,笑道:“姐姐,没嘴脸的那头是何物?”
众人听闻,忍俊不禁,都笑了。
庒琂很是无奈,直直看炕上的庄玝,心里很是羡慕:要是自己能像她这样就好了,一醉全不知。
可是,庄玝起先不也醒着的么?怎忘记得如此快?西府的果子酒,还有抹去记忆的效能?顷刻之间,庒琂心中满是期待:我好歹也讨几杯果子酒来吃。
大约过一会子,庄璞气煞煞地回来,进门就扯开嗓子道:“人是没走,从门口赖上树了。辛苦她们篱竹园那些小腿脚的跟着喂蚊子。一圈的围在树子底下呢。”
庄玳道:“哥哥还留她们做什么,早些轰开。”
庄璞道:“得了吧!难得纠缠。这女人纠缠不得,真纠缠起来,亏的还是你我。都别说了。”
到此,算是平静了。
平静过后,庄玳满目担忧看着庒琂,几欲开口跟她说话,但是,满腹言语,不知从何出口。想关心她,怕她多想,想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怕引她不安。思来想去,只好痴痴望住她,唉声叹气。
天时直至深晚,湘莲忽然想起几位客人还在,便再一次将庄璞拉去一边,提示他,该叫车送客了。所谓送客,无非是肃远和锦书兄妹。
庄璞得了湘莲的指示,过去对锦书兄妹作揖抱歉,道:“这也晚了,你们不必回去了吧!我让人给你们收拾两间屋子住下。”
湘莲听庄璞这样说,惊愕不已,不是让送客么?怎留人了呢。心里疑惑,幽怨,却也淡淡相笑,没表现什么来。
锦书看到湘莲的脸色,知她有不快,便道:“是呢,也很晚了,要不,我跟我哥哥先回去。改日我再来瞧五姑娘。”
锦书说着,手去拉她哥哥张郎。
张郎不愿走,道:“金纸醉没吃完呢,我不走。我要留下跟璞二爷吃酒。”
锦书嗔道:“哥哥混闹!”便脸红地环望众人。
不管怎么说,张郎铁定不走。于是,锦书无奈地对庄璞等人道:“我哥哥不走,那我先回去。请二爷替我亮把灯来,我们自个出去就行。”
庄璞摇头,招呼旺五和财童进来,吩咐他们送锦书姑娘出去,就张府的车送到府上。锦书不好推辞,顺了庄璞的意思。没一会儿,锦书走了。
锦书一走,肃远也要走,庄琻见状,挽留道:“小王爷走了,谁给我们主持公道?我提议,小王爷不能走。”
再有庄玳、张郎、曹营官等人说话挽留,肃远才勉强留下。
没多久,外头有人来传话,说太太们回来了。听到报说,众人振奋。
可庒琂听闻,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反而加重忧虑。
庒琂想:今夜,必定是不眠之夜了,不知太太们要怎么处置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