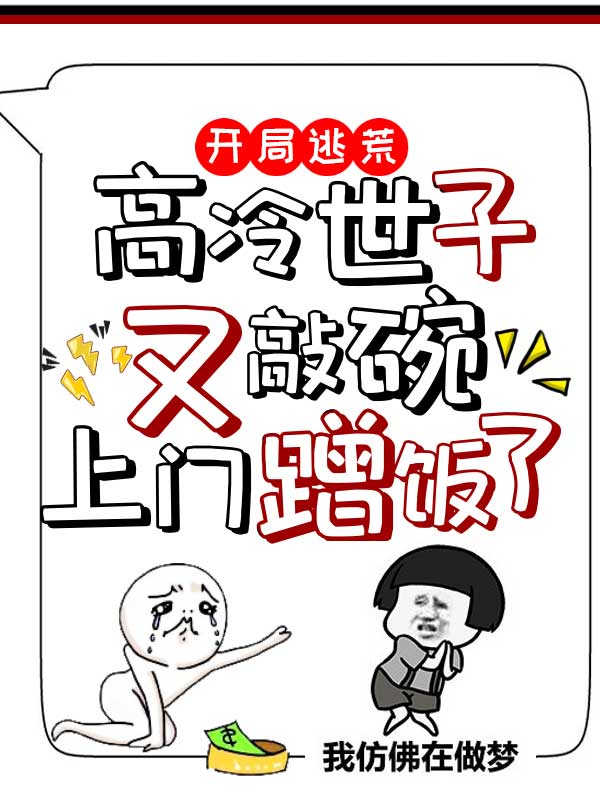“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就在李深海为他的事业构思蓝图时,张进山开口说道。“苏家是无辜的,为苏大人留下一线血脉。也不枉你我与他同窗十年,苦为寒子。”
“好,我同意张大人的提意!”李深海毫不犹豫的答应道。
虎门大牢。
苏元昏昏沉沉的从茅草铺就的秸秆上醒来,他的四周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与其他牢房不同的是,这间牢房似乎是为他一个人特意准备的,四面的墙壁上虽然不是很干净,却极为光滑,远远看去泛着青绿色的光亮。
环顾一周,发现三面是墙,一面是隔着拳头大缝隙的铁质栏杆。在看脚上,被一块黑铁牢牢的铐住足有手臂粗细。
望着头顶滴水的牢房,苏元猜测或许这就是别人常说的天牢吧,关进了天牢就等于把命交给了阎王。
难道我苏元就这么死在天牢里?
“吃饭了,吃饭了......”狱卒扯着嗓子用铁棍敲打着牢门,生怕苏元没听到错过了用餐时间。
苏元回过神来的时候,狱卒已经将二个馒头和一碗稀粥摆在了铁门口。
馒头?竟然让本少吃馒头,还有这个破碗装着的稀粥,这怎么吃?从未受过一天苦的苏元哪里知道即使是馒头和稀粥都是朝中大臣为了照顾他而特意开的后门。
虽然极度不平衡,但苏元还是吃了。这么长时间的颠沛流离已经将他身上的大少爷脾气抹灭的一干二净。
受些苦,是好事。
苏元心里这么想着,当一个人因为一口吃的而去杀人时,那才是最痛苦的。
很快,二个馒头一碗稀粥滑进了苏元的肚子里。
突然,肚中一阵翻江倒海,剧烈疼痛的肚子将刚才吃下去的馒头全都吐了出来,当吐无可吐,胃里翻滚着粘稠的酸液被强行挤压出喉咙时,苏元发誓一定要将周天搬运功法学会,他要将这种痛苦毫不保留的施加在害他之人的身上。
终于,几番挣扎后,苏元晕死了过去。
“曹大哥,那小子好像死了。”狱卒打开牢房冲着他身后跟来的曹大毛说道。
“死了就对了,不死还得再给他灌一壶毒酒,死了好,死了省事。一会叫几个麻利的兄弟把这小子丢到乱葬岗的天坑里,然后你们几个领了赏钱有多远走多远,明白了没有?”说话的曹大毛正是在小河边用迷药将苏元迷晕的兵头。
“明白。”
乱葬岗位于汴京城西北五十里处,但凡在狱中病死亦或是老死的犯人都会被丢弃在这里,遇到心地好的狱卒挖个浅坑给埋了,心地不善的随便一丢。
赤条条来,灰溜溜去。
总之到了乱葬岗,阎王也难找。远远望去,密密麻麻,加之大雪刚过,根本分不清哪里是白骨,哪里是白雪,远远的就能察觉到有阵阵阴风吹拂。
但凡路过此地的人们,都会不知觉的快走几步,生怕被孤魂野鬼给盯上。
苏元面朝白雪,背朝青天,被几个假狱卒丢进了深达三十多米的天坑中。传说,这里原本是一片清澈的湖泊,后来不知怎么的湖水渐渐干枯便成了乱葬岗最为隐蔽的藏尸处。
冬日刚过,春风又来。
尽管大地回春,万物苏醒,但天坑中的气候依旧寒冷,下了几个月的大雪此时尚未溶化,在那背阴处却是神奇的长了一棵枣子树。
苏元被抛下时,正巧落到了枣树上,在抵消了大半力量后这才滚落到阳面的雪堆里。
雪堆旁蜷缩着一个衣衫破烂的男子,这个男子约莫四十多岁,两眼浑浊满脸污垢,蓬松的头发上沾满了尘土,被突如其来的声响惊醒之后,两眼中迸射出一抺病态的欣喜。
没人知道这人为何会在这天坑里,也没人知道他是如何活下来的。
苏元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浑身上下已经被人剥了个精光,就连红色的大裤衩也没有给他留下。当他迷迷糊糊抬头看到一个疯子穿着他衣服对着他呵呵傻笑的时候,苏元像见了鬼似的再次吓晕了过去。
寒风吹袭,没多久,晕死过去的苏元再次醒来。
此时已是黄昏,天坑三十米处已然黝黑一片,只能依稀看到有个形体枯瘦,蓬头灰脸的人蜷缩在树根下瑟瑟发抖。
苏元已经被冻的神智不清,不论是坐着还是站着,他的四周全是雪。全身的皮肤如冬日里的石榴发着病态的嫩红。
“冷。。。”
倒在雪地里颤抖的苏元,用微弱的声音向蜷缩在枣树下的男子求救。
只是那人并不理会,用一双看待死人的眼睛,时不时斜视着。
没过多久,苏元停止了抖动,气息消散。
满脸污垢的疯子陡然睁开他那双腥红的眼睛。
夜很黑,只能看到头顶少许的繁星。
但这个疯子一样的男子就像是见到许久未见的大餐一般,张开恶臭的大嘴朝着苏元扑了过去。
气若游丝的苏元灵台一片空寂,他觉得自己飘荡在虚空,周边漂浮着一团团迷雾般的白云,就这么慢无目的的漂荡着。
直到撞上了一根写满奇怪文字的通心柱上。
通心柱,通体红色,粗三米有余,高耸云霄。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文字。
“咦,这不是周天搬运功法吗?这是何人所刻,竟然被写在了这根石柱上。”苏元的意识随着周天搬动功法开始运转起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突然感到手臂刺痛,睁眼之际,一个身影从他身旁一闪而过,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男子的惨叫与骨头被折断的声音。
稍微回神,苏元这才发现是自己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将什么东西给甩了出去。
可自己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大力气,而且,不是那么冷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修炼了周天搬运功法,所以才变的厉害了?
一定是。
从雪地上坐起,苏元凭着感觉慢慢的走向刚才被他抛飞的物体旁。
由于夜色太黑,苏元无法看清究竟是什么东西,但他猜测除了白天扒他衣服将他丢到阳雪堆里自生自灭的疯子外,不会再有别人。
他的猜测是正确的,第二天清晨,苏元从树洞里爬出来的时候,昨晚被他甩出去的蓬面男子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再看自己手臂上,一块模糊的血肉只剩下一块嫩皮耷拉在上面。
苏元大怒,抬起右脚在死去的疯子身上用力的残踏着。
望着僵硬的尸体,苏元的怒火依旧没有熄灭。在疯狂的扒下疯子从他身上抢去的衣物后,苏元总算是得到了一丝安慰。
衣不遮体非公子。
整理好衣物,辰时已过。
久违的阳光终于沿着天坑的峭壁慢慢洒向阳面的雪堆。雪堆也不知经历了多少年月的积累,在阳光的直射下发出淡淡的银晕,如一座遗失在地下的银山令苏元一阵头晕眼花。
打量着方圆不到三十平米的天坑底部,阴面的那棵老树令苏元产生了疑惑。阳生阴死,是自然规律,奈何这棵枣树却违背常理硬是生在了阴寒刺骨的天坑阴面。
阴面,阴风刺骨因无法承接阳光的照射,所有极为寒冷。能在此恶劣环境下生存的树种绝非凡物。
面对十多米高的枣树,将其细细打量一番,苏元并没有发现有何不同。与外面生长的枣树属于同一品种,如果一定要分辨,或许树叶要比外界的小上不少。
一声鸟鸣打破了苏元的思考,苏元抬头只见白灼的日光下有几只乌鸦在头顶盘旋,哇哇乱叫不由的令苏元头皮发麻。
疯子的尸体已经僵硬,与周边的白雪紧挨一处,从苏元站着的角度看去倒也凄美。
几只乌鸦从天坑洞口飞过,怪叫之后拍打着翅膀消失在苏元的视线内,三十多米的深坑就连乌鸦都不肯长时间停留,生怕一个不小心折了翅膀掉下来摔成一滩肉泥。
仰视上方巴掌大的天空,苏元一阵惆怅,自己该如何逃出升天?
寒风凛冽,不知何时天空中下起雨来,饥寒交迫的苏元不由的再次裹紧身上的衣物。单薄的囚服即使有周天功法护体也难免蜷缩成一团。
空旷的洞底唯一能避雨的只有枣树下那个之前由疯子开凿的树洞。昨夜迷糊之际自己就是在此洞中过的夜。
春雨比不得秋雨,却也掺杂着冰冷的凉意!
钻进树洞,苏元开始思考脱离困境的方法。
枣树主干部位高达十多米,天坑深约三十多米,即使爬上树顶也不可能一跃跳上十多米的坑沿。即使可以,坑沿四周没有草木,常年累月覆盖了一层薄冰,依旧无法借力攀爬。
加之天坑呈倒斗形状,上窄底阔,无法依靠攀岩之力徒手攀爬,更何况四周空无一物……
留给苏元的只有一块巨石,一棵枣树,一具冰冷的尸体,除此以外是阴面堆着的终年不化的积雪。
如何脱困?
腹中咕咕,脑力不支。体力的消耗使得苏元难以继续思考。尽管强行调息,体表的寒气依旧令他忍不住打起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