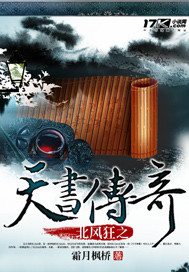面前的女子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的模样,梳着一个大发髻,用碧绿簪子将秀发拢起来,简单随意。肤光胜雪,皓腕若霜,灵秀双眼如璞玉般清亮明澈,眼角微微上翘,勾出几分雅致灵韵。
淡紫色绸衣衬得她的身段愈发修长了,裙裾上束束皱褶有若那开得正艳的紫云英,纤细如柳的腰间束一条云锦缎带,精致古雅,袅袅婷婷,周身隐隐有光芒笼罩。
她就是昨夜的女子无疑。
尽管脱去了艳丽的妆容和华美的纱裙,但那双宁静神秘的眼眸却是一眼难忘,无论如何都不会认错。兴许是昨晚的那身祭舞装扮给他的印象太深了:绛紫色纱裙、流光溢彩的珠链串、如血般浓艳的红唇、夸张的妆容,处处都透出成熟女人的风韵,
他一直以为空桑大巫祝已有二十来岁,但现在他才发现自己想错了。除去诸多繁琐缀饰,一身素衣不施粉黛的少女竟美得朝气蓬勃,也美得惊心动魄。
“你好,我是桑柔。”空桑巫祝礼貌地开口,举手投足间全无寻常女子扭捏拘束。
“长鱼酒。”
“大人,您先在这里看着,我去把他的另一个朋友喊过来。”阿驽朝大巫祝微欠了欠身子,又转身下楼去了。
阿驽一走,屋里瞬间安静下来,晶亮的雨珠从马醉木叶上滚落而下,一滴一滴敲打在窗台上,发出一连串“哒哒”声响,仿佛在演奏某种美妙的乐章。
桑柔轻移莲步款款走来,手腕上一串银环随着她手臂摆动相互碰撞着,发出清脆悦耳的音韵。
“把手伸出来,我看看吧。”
没有丝毫顾忌,她大大咧咧地坐在了长鱼酒对面。
长鱼酒捋起衣袖露出右臂。大巫祝目光下移,但见长鱼酒手腕之处尽是一片淤紫,肌肤底下隐隐有奇异光泽流动,似乎是某种有生命的东西正在急剧蔓延。
桑柔蹙着秀眉思忖片刻,随即缓缓伸手,轻搭在他右肩上,纤纤玉指顺着他的手臂一路往下滑去。
她的指尖凉得没有任何温度,被划过的每一寸肌肤都能感受到这淡淡的凉意,这是他从未午有过的异样感觉,仿佛触电般酥麻,却又稍纵即逝,再一次为他自身灼热的体温取代。
桑柔的指尖一路滑到靠近手腕的地方,终于停了下来,轻点在那一处。她口中念念有辞,念一些他听不懂的、音律单调又古怪的话语,似是楚地方言,又似是来自幽冥世界的亡灵之音。
指尖继续往下移动,直至覆在光点之上,在交叠的那一刹那,长鱼酒似乎看见那光点跳了两下。
忽然,她指尖对着光点用力地摁了下去,力气之大、出手之迅速使得长鱼酒瞬时倒抽口凉气。
“嘶——”
“痛吗?”
桑柔又接连摁了好几下,然后抬起头,关切地望着他。
“废话!”
他妈的!他都痛成这样了还摁!
桑柔“咯咯”笑了起来,笑得像一朵绽放的鲜花,“那就没什么大问题啦!”
她起身走向窗户,从伸进窗口的扇骨木上折了一根树枝下来,用这根树枝在地面上空画了一个圈,把一脸莫名的长鱼酒圈在中间。
她轻轻挥动扇骨木,红唇翕动吐出一串咒语,好似在演唱一首美妙的歌曲,美目流转见清波流盼,魅然天成。咒语在小木屋里缓缓流淌,她围着长鱼酒翩翩起舞。
“雪落梅花上,漂亮乳儿吃草莓。江边霜草白如露,翩然似梦还似歌。秋心如海又如潮,温柔月光浮于水,此愁谁得解?今夜三尺雪,梅花似我愁。”
在空灵美妙的旋律中,长鱼酒恍惚中有种回到昨夜的错觉。但现在,这舞蹈却是跳给他一人看的,这让他不由生出几分莫名的庆幸。
空灵如水的音律渐渐低落下去,一舞终了,桑柔优美地旋身,收住脚步。浅紫色百褶裙上下翩飞,裙摆上缀的各色鲜花琳琅满目,教人目不暇接。
长鱼酒定了定心神,沉声问道:“怎么样?”
“无碍。”桑柔摇了摇头,“虽说这符印被封在了你体内,但它短时之内不会伤害你,因为你的手臂还存有痛感,说明手臂的知觉并未被这符印消解。倘若我刚刚摁下去而你毫无知觉,那才危险哩!因为那就表明咒术已经渐渐侵入你的身体,控制你的感知力了。”
桑柔捋了捋略显凌乱的长发,接着道,“许多符印一旦种下便会急剧向外扩张,同时沿着经络向体内深处蔓延,如果没有办法及时取出,一旦蔓延至头部,人便会神情癫狂丧失理智,乃至最终完全沦为符印主人的傀儡。我亲眼见过这样的情况,可是你毕竟与他们有所不同。瞧,这个符印仅仅不过停留在你的皮肤表层,而未曾得见向下迁移的趋势,但这并非意外——我能感觉到他深厚的修为,或许他只是不想这么做而已。兴许……这道符印存在的意义并非侵略或控制,反倒更像是……”
桑柔蹙着秀眉头,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更像什么?”长鱼酒一脸凝重。
“嗯……我想,懂法术的人大抵都知道,种下去的符印与主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符印从属于种植者,与其主人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一旦种植者死去,那么他种的符印也将随之消亡。既然两者之间有如此关系,某些江湖高手就会利用符印监控他人,那些他想要获取行踪动向的人,通过对符印的感应达到目的。”
“所以说我被监控了?”长鱼酒闻言顿时眉头紧锁。
“是。”桑柔严肃地点点头,“只要寻找机会,将符印种在对方身上任意一处,确保他能被迫携带符印即可。这种方法既简便又不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踪,当是修习术法之人的上上之选。”
长鱼酒愣愣地望着手臂上那团青色光晕,目光变得飘忽起来。
半月前,他在鲵桓沉渊与灰衣人过招,那时候的他纵观全身处处是破绽,灰衣人想必是趁了那时间在他身上种了道符印吧。这些都能说得通,可是……那神秘的灰衣人缘何要监控他呢?他若是想要利用自己,为何不直接将将自己变成他的傀儡?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做出此等事来?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这些问题是长鱼酒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数不胜数的疑惑涌上他心头,凌乱的思绪如线团般纠缠在一起,让他不由自主感到一阵烦躁。
“你刚才围着我跳的那支舞,是做什么用的?”他突然问道。
说来也奇怪,人在思绪最烦乱的时候,往往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哦,那支舞啊。”桑柔闻言吐了吐舌头,“驱除附着在你身上的邪灵呀。这可不是一般的舞,这是一支……我边施法边跳的舞,有魔力的哦。”
“确实是……有魔力啊。”长鱼酒一时哭笑不得,“我不过中了道符印,身上哪来的邪灵?”
“怎么没有?”桑柔的语气虽然严肃,但白净的鹅蛋脸上却隐隐有笑意,“嘿嘿,我说有就有,瞧,就是那里。”
她轻抬素手,指着长鱼酒的心脏部位。
“所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拉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看你心情烦闷精气神萎靡便知定有邪灵作怪于心官,导致全身上下屡出差错。要知道,一个没有邪灵缠身的正常人,是不会如你这般烦闷的!”
“哦,照你这么说,人皆有烦恼,岂非人人都被邪灵缠身了?”长鱼酒无奈地苦笑道。
“对啊!”桑柔竟然理直气壮地应道,“确实如此。你要知道,这世多数人皆是梦中人,被邪灵困在芳香迷醉的梦中无法自拔。正是因为这世上先有了梦中人,然后,便有了巫祝。”
长鱼酒无语地看着她,一秒、两秒、三秒……
“好吧,其实也没什么邪灵……”桑柔两手一摊,吐了吐舌头,“没办法呀!再怎么说我也是空桑大巫祝,众巫之首哎,帮人看病当然要有点档次,否则怎么能显示出我的本领来呢?嘿!岂能跟寻常大夫一样随便呢!”
“呵……”
治病就治病,哪来的这么多歪理啊……长鱼酒叹了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
原来还是个孩子呢,不过倒也还挺讨人喜欢的。
“哦对了,你昨晚受了那么重的伤……实在对不住。不过我们空桑绝不会放你不管的,一会儿我便去外面采些草药送过来,让人每日熬成药汁按时敷用即可。”
长鱼酒还未开口,便闻一个低沉浑厚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巫祝大人!”阿驽恭顺地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有一个酒壶,四个酒杯。长鱼酒敏感地嗅到了空气里醇厚的酒香味。
阿驽的身后跟着一袭绿衣裳的云樗。云樗的脸色非常难看,看上去就快要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