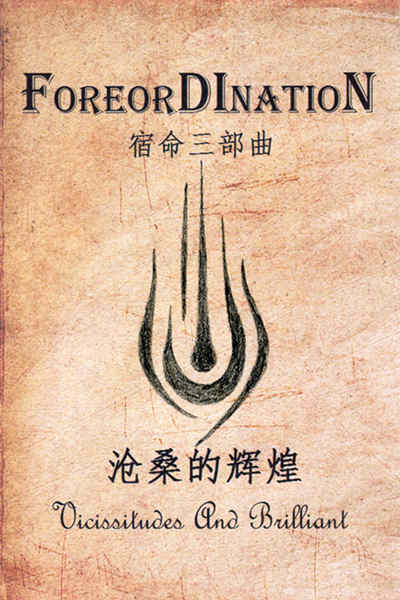当然,人类早就发现,任何单独的个体在这世间都是柔弱的,好在人类耐以保障生活的最主要技能叫做交换,这位刀客最终打算先去救出那个传说中的猛男,而且按眼下的情况看,在旅途中兼任保姆和厨子的可能性很高,用帮助这位伟大恋人达成目的的高质量服务,去换来被营救者的帮助。
因为要去救的这位据说特别正直,而且因为同情蛮人遭遇受到处罚的老大,按小姑娘所说绝对会与年轻人达成一致,这不但能让他多一个强授,更重要的在于,那座城的很多地方,只有这个家伙才能摸得进去。
那种神话故事里才会存在的身份保全系统,被罗珠一番免费宣传,功能得到了百倍以上的完善。
本来不信的年轻人在仔细检查过她颈后的那个疤后,才知道这并非戏言,要让一个肌肤吹弹得破的女子对自己的身体下刀,除了那份真挚情感外,恐怕就只有监察仪器的可怕压力了。
由于所获信息的严重不对等性,年轻人认为自己只要一接近那种地方,能留下全尸大概就要算是祖上高香烧得够本。
不能死,至少不能现在死,最起码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他身后的数十万同胞似乎全都在齐声呼唤,希望的种子如此荣幸落到了自己头上,那么肩膀上的担子必然沉沉甸甸,压得人稳重无比,脚踏实地。
两个人结伴而行的日子很平淡,神国追踪队收集到的消息无比混乱,这两个拥有超阶武力的高人,在体术和异能两方面均达到了常人无法想象的高度,打发几队完全靠科技武装起来,没学到足够搏击技巧的护卫,完全是小菜一碟。
更加不用说,这两个人中还有个可以躲藏在精神力屏障后面客串杀手,无声无息发射冲击大炮的罗珠小姐。这些护卫武士被两个人引得如同没头苍蝇一样乱转,小股部队通常会在一碰面时就被击跨,大部队围剿…..你们想想梅西的战绩吧。
指挥系统的混乱状态直到托罗到来才有所好转,当一位劫后余生的护卫出示过他的探测器数据后,神国派出的前线指挥官才知道,自己面对着的,是两位已经达成或超出于玛斯克标准的强者,整个国度唯一可以与之相抗衡的,也不过一只手就能点清的那么寥寥数人。
这些强人大多身居高职,轻易不可挪动,因为他们变故,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战略布局稳定,当然,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刚刚改造过的托罗先生,这家伙无门无派再加上无名无姓,就算是派他跑到月亮上去开展工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这位毫无炮灰自觉的托罗大哥尽职尽责地来了,而且他只用了半天时间,就从千头万绪的线索中理出一条主干,那就是这队情况不明的敌手,要去哪里?
地图上的线路左弯右绕,在包围圈里表演着特技,可是无论行走过程多复杂,总是可以发现,这队人马一直在向着东方前进。
托罗都没有借助于制图工具,只是把食指点在图上向前直线移动,让一个个地方从眼前滑走,吉安坡地…..菲比尔高原……朱门峡谷,最后,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了。
如果没有搞错,那么这个后备基地,就是他们此行的目标。
地方是罗珠选的,这个地方是托罗最近的一个职务所在地,相关地图和方位早就被她从中央处理器里一并偷了出来,深藏在脑海中决不会搞错。
可是这个小姑娘却不知道,那是托罗挂的职务,与工作被拆分成为独立的两部份,他领着同级别的待遇,却要做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工作,自始至终就未曾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坐过一天班。
当然,现在的情况可不一样了,那个地方将在未来的一段时光中荣幸地成为追踪大本营所在地,重要的叛逃者将在重重罗网中被逼入陷阱,化作可供研究的实体标本。现在的托罗看到这里,手心在不知不觉中早已经满是汗水,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自己所受的职业教育,会计划出什么样的可怕手段。
可是两个猎物全无所觉,他们一路游山玩水,间或打发掉几队不开眼的护卫队,拿大自然丰富的食品库存,滋润着自己的肠胃,结果来到目的地的大门前时,罗珠居然胖了…。
这道坚实的大门在年轻人的超级宝刀面前,简直如同纸做的一样,他使出片烤鸭练出来的精妙手艺,把摩尼刀舞得如穿花蝴蝶般轻盈旋转,只过了片刻功夫,那块叫做门的金属板就不见了,地上到处都横七竖八地洒满着各种形状的碎片。
在基地里守着监视器的托罗见状大吃一惊,当年的他和现在一模一样反应,大叫道,这不可能!!!这当然不可能,因为这种十二元合金就算是用同温层舰队的能量副炮直接轰击,也最少可以支持上数十分钟,人类要靠肉体力量直接攻破它,理论上最少需要不停地砍上一万年。
门外的年轻人当然没有机会听到敌人的惊叹,他引着罗珠向基地内部跑去,计划只要一救到人,立马拖一个再扛一个,撤。
一路来都没有见到那些爱穿一样战甲的守卫者们出现,他们不知道躲进了哪个角落,越往里走,年轻人的心里就感到越发不安,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不正常,四处充满的新奇玩意儿,让他目眩神迷,心里也一分一分地悬了起来。
托罗在里面也没闲着,本来准备好的金属囚笼依命被放下,那些粗如儿臂的格栅铁栏,在那把大刀面前显得这样可笑。
如果没有更好的设备,那么就只能凭借自己的个人本事却和对方硬抗了,他一边不住地轻声咒骂着那把奇形怪状的菜刀,一边换下自己身上的衣服。
宽大的外袍里,是一件精细的轻甲,这种板式结构的轻型战衣专门为重要人物量身定做,非常贵重。可是他手一扯,再次脱下甲胄,并把身上的装备一件一件小心翼翼地取下放在一边,直到身上除了长裤外只穿着一件黑色短衣为止。
既然对手连那么厚实的大门都不曾放在眼里,自己又为什么非要添上一件没有用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