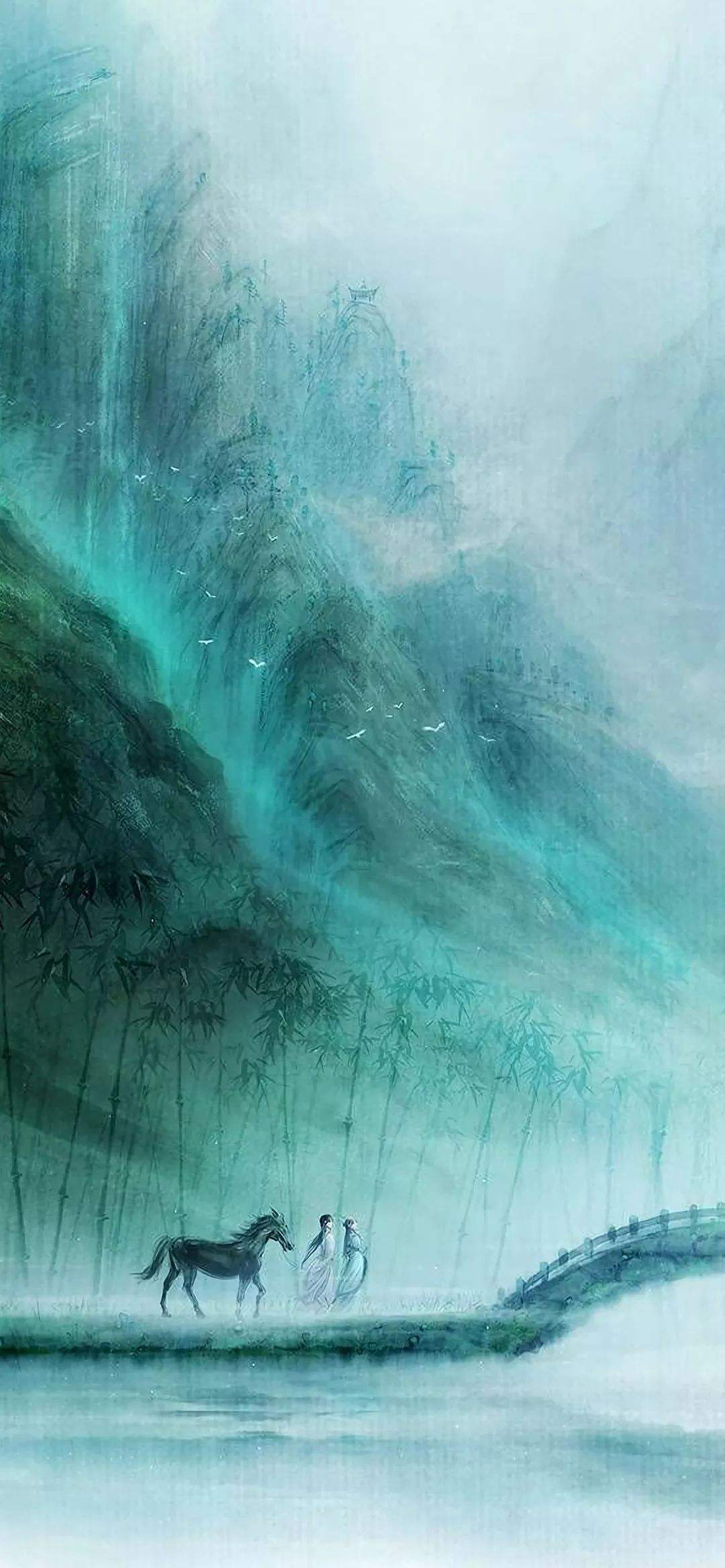“好了,我和非攻有事要说,你们先去帮我看看十二月她们的素描怎么样了。”
云卿对采蘩欲说还休的样子笑了笑,这样活力满满才是她的后宫呀。
等她二人离开,云卿收回嬉皮笑脸,一本正经地把自己的想法大概和非攻说了。大体意思就是要他们全面发展,素质教育。
非攻自然没有什么好反对的,他四人人都是云卿的,别说安排他们学习了;更何况经过今晨的比赛,一向忿忿不平的非然也收起了自己的棱角。
早上的比赛虽然周老伯没有公布比赛结果,可他们都明白胜者是谁。
眼前的事实也不容他们怀疑。
在荒郊野外,云卿一个千金小姐的生存能力,的确比非然强;至于药材辨别和中毒急救,他们以前在影部的确没有学过。
所以这方面,对他们四人今后在云卿身边行走,有益无害。
不过……
非然顿了顿,脸色沉重地望向云卿,“不过主子,属下可以提个要求吗?”
云卿没觉得有什么毛病,颔首示意他说下去。
“这身交襟可不可以不用红色?总觉得……总觉得娘气了许多。”
云卿没忍住,噗嗤笑了出来,直揉着肚子哭笑不得,“我还说何事值得你这么不苟言笑地说出来 却是为这事啊。”
“这么说,县主同意换回原来的衣服了?”非攻面露急色地确定再三。
“当然不行。”云卿话锋一转,笑意立刻消失在眼角眉梢,端坐在长榻上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那眼角精光一闪,非攻就知道没戏,心里忍不住地长吁短叹起来,连眼神都是幽怨起来。
眼前的表情配上身上的一抹银红,像极了深闺少妇。云卿忍住不要脑洞大开,还是有些忍俊不禁。
“你们的组合叫‘红不扫’,自然得穿红衣。至于兵器你们已经用了顺手,再换反而麻烦。不如先将就好了。”
云卿云淡风轻地说着自己的打算,瞥见他沉默不语,话语轻转地又道:“你们是我隐形的利剑。但大隐隐于市,越是特殊的越是要划归平常。这才是王道的生存,你可明白?”
“属下遵命。”非攻深深地给云卿作揖,心悦诚服的样子险些让云卿以为,他真的懂自己的现代语言。
“对了还有一事早上怎么没见着非忽,他去哪儿了?”云卿忽然想起来。
非攻有些为难地怔了怔,“回主子,非忽说去看看采蘋,想来也该回了。”
“随他去吧。”话音落,云卿又想到什么似地莞尔一笑起来,“从没想过一个杀人如麻的杀手会如此长情。”
“属下会好好教训他的。若无其他吩咐,属下就告退了。”
云卿颔首,闭着眼躺在软榻上,拿了帕子遮住脸挡着光线,轻摇着罗扇。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缓缓的一句话就这么顺着风飘进非攻耳朵里,在竹门外,他的脚步停了停,朝来时路的相反方向而去。
一路蜉蝣戏水,穿林涉水才找到了正坐在采蘋墓前的非忽,新鲜的土壤上栽植了许多浅黄色的小花朵,零零碎碎。
“咱们很久没有比试了,来吧。”非攻拔出佩剑,一言不合就架上了非忽的脖颈。
非忽靠在采蘋的墓碑上喃喃自语,对猝不及防的剑光连眉头也不皱一下。
“若赢了,我就告诉你谁是凶手。”
非攻话音刚落,剑下非忽的身影已经消失,耳边短暂的风拂过,却见着一团黑影,身手敏捷地落在树上。
夕阳西下唯有落霞满天,嗜血的颜色衬在半空中诗情画意有之,但在刀光剑影里却是异常诡异。
树木浓郁的绿悉数都被黑色覆盖,若有旁人,大概只听见乒乒乓乓的冷硬撞击,目光所能捕捉到的也不过残留的一丝黑影罢了。
“我赢了,告诉我是谁害的采蘋。”非忽冷着脸,收起软鞭质问着非攻。
“告诉你,你去报仇吗?”看着他气急败坏,急火攻心的样子,非攻有些好笑地反问了一句。
紧接着一个鲤鱼打挺,长剑从背后飞出,凌空一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非忽的脖颈,丝毫不带犹豫。
“非忽,不管是长情还是沉沦过去不可自拔,你当知道都是影士的大忌。别以为自己是颗痴情种,也永远不要忘了你的身份。”
只要是个人都会有七情六欲,可他们是刺客,是主人手上的利剑。再如何也不应该沉湎其中,耽误修行。
更何况,他们是影部出来的人。
非攻说完迅速地收回了剑,越过非忽面无表情地离去。
从头至尾非忽没有再接过一句话,忽地瘫跪在地上,魁梧的身躯蜷缩着发出嘤嘤的抽泣声,紧接着却是嚎啕大哭。
哭声振林樾,一片寒鸦起。
百米外的非攻有些动容,作为老大,他竟然丝毫没有发现非忽对采蘋的这种感情,何时竟然如此至深。
他心里歉疚得像做了什么错事,亲手扎破非忽的泡影,这感觉很残忍?可是,他是影士,残忍不是应该的吗?
非攻自嘲一笑。
动容什么的怎么可能会有,他不明白非忽的感情,不明白爱有何用,不明白非忽为了一个女子这样低落有什么值当?
若是男人,定要变得更强,才能在仇人面前面不改色地置其死地,方一雪前耻。
只是他非攻这一生,注定了只会为一个女子牺牲,为她抛头颅洒热血。而这也将是他的命。
这世界原本是黑白的,杂乱而没有声音的。却总有一个人在前面小步小步地坚持不地掌着灯,带着一丝光亮。
光线微弱得随时会熄灭,可他黑暗的生命,却愿意为那遥不可及的微光而肝脑涂地。
或许是从湛卢首领点名了他们四个跟随云卿的那一刻开始,或许是第一次感受到除夕的氛围,或许是第一次见一个女子面对刺客毫不畏惧的时候。
他不再是冷冰冰的凶器,是一个人。
无关风月,只是信仰。像所有的和尚崇尚佛教,道士一心问道。
世界上的事总是这么地不可预测,各有注定,有人天生为王,有人落草为寇。
云卿永远也不会知道,她的出现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可同样她也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结局是什么。
这一夜后,云卿身边短时间内都没有见到非然三人的身影,只知道福嘉县主身边有一个红衣保镖就是。
听说江左弋渊海阁的暗器最出名,镜湖药王谷以毒闻名,而墨家机关术从未消失。
转眼月余,庄子上的一切从青黄到金黄,到了丰收之际总是最忙的的时候。一批批水果运到‘人间有味’开张售卖,云卿也满载而归打道回府。
虽然可能各府都有备着解暑的瓜果,还是让下人挑了好些时鲜水果送到各府,和云卿交好的几家自然不在话下,又有雍亲王府和老太太院里,这样盘算下来量上有了质的飞跃。
红袖招开业酬宾,人间有味冰镇瓜果新鲜上市,噱头才出就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宾客上门,可谓万人空巷。
要晓得在烈日炎炎下,能得一片绿荫,一道冰凉的甜点,那简直就是无与伦比的享受了。
分明不想赚那么多钱,可是看到赚钱的机遇还是忍不住要下手。云卿终于有些理解那句形容商人的话了。
无利不起早,原来是如此。
“主子,宫里面来人了,姑姑让赶紧上大厅去。”
云卿在清凉阁里正检查着十二月的素描作品,听着外面的传话一骨碌从芙蓉榻上爬了起来,赶紧饮了一盏酸梅汤压压惊。
正厅里,蓝衣内监不苟言笑地引着后面的绿衣内监严整地站着,都好一会儿才见着人不急不慌地出来。
红衣内监面上虽没有愠色,眼里却是闪过趾高气扬的光芒。巧不巧了刚好被云卿察觉,芍药明白云卿的意思,颔首退下了。
“皇上有旨,赐福嘉县主:庐山云雾;真丝香云纱两匹;软烟罗秋香色、银红、雨过天青色、松绿色各一匹;羊脂玉如意和珐琅如意各一柄;和田白玉珊瑚珠头面一套;锦绣插屏一面;赐梧县作为封地。”
“福嘉领旨谢恩,吾皇万岁。”
“县主请起,给县主道喜,宫里的县主不少,但有封地的你可是头一位。”红衣内监阴阳怪气的声音,听得云卿有些按捺不住。
“公公说笑,左右不过皇上垂怜罢了。这大热天地,请公公们喝盏酸梅汤去去暑气。”云卿含笑着应和。
正巧芍药带着一众丫鬟上来,给每人都呈了酸梅汤,又悄悄给了宣旨内监一荷包银锭子。
红衣内监识趣地婉转一笑收了下,兰花指一翘又向云卿说了好些好话。芍药自一一应承,又吩咐下人把所赐之物都登记入库才罢。
“那内监虽然口若悬河地说了许多,倒有一点是没错的。这有封地和没封地的县主,是不一样的。”
芍药翻看着库房记录,心情也甚是愉悦。
云卿坐在一旁,随口插道:“得失君王。我明白的,姑姑和我说这些作甚?”
“县主心里明白,皇上的赏赐不过是因为和王爷的亲事。但奴婢瞧着,县主看上去并没有那么意外和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