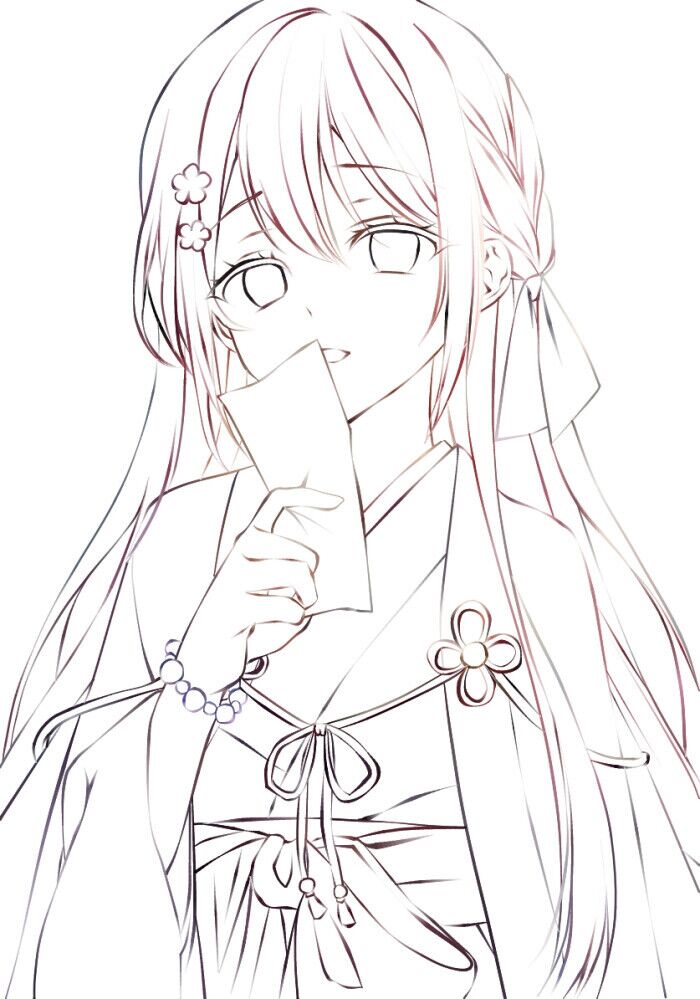【第五节】
近来姬无夜有些心事重重,常常心不在焉。这一夜,他又从漫漫心事中悠悠地回过神来,脚下的步伐一滞,定睛抬眸看去,前方竟然是晚晴居。他微微有些诧异,为何自己不自觉竟走到了慕容凝的房门口来?偏偏这一路他走的顺畅无比,似是再熟悉不过。
他摇摇头,自我否决了脑海中不切实际的想法。正打算不露痕迹地转身离去,晚晴居的门却吱呀一声开了。
他愣愣看去,却见慕容凝亭亭俏立在月色下,宛如身披了一笼银色轻纱。
两人都是僵立在那里。
姬无夜很想拔腿离去,奈何足下像是生了根,腿似是灌了铅,将他牢牢地钉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还是慕容凝先回过神来,唇边弯了抹笑打破尴尬:“今晚月色正好,我正打算出来散散心。”
她只着了件宽松的月白中衣,随意地披了件藕荷色薄衫,清淡温和的模样一时叫姬无夜一句话也说不出。看着他迷惘的神色,她拈起裙角向他盈盈走了几步,语调轻柔:“夫君,你何时来的?”
许是那声夫君唤回了姬无夜的神志,他笼起手轻咳了一声:“那个,我也是为了赏月,随便走走。”
“这样啊……我还以为夫君站在晚晴居门前,是因为……”慕容凝的长睫微微地颤了颤,一双似水明眸渐渐地暗了下去,那话音里浓浓的失望听得人于心不忍。
“顺便找你。”不知为何他竟十分见不得她失望的模样,没来由便脱口而出了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的话。
慕容凝重新抬起了头,眸里亮晶晶地:“不知夫君来找阿凝所为何事?”
阿凝……
姬无夜突然感到一阵天晕地转般的模糊感自脑海之中传来,阿凝……好熟悉的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可为什么,什么都想不起来?再要细想下去的时候,剧烈的疼痛宛如一把利斧劈开头颅,痛的他不得不放弃继续思寻。
“无夜,你怎么了?无夜?无夜?”
再恢复清明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慕容凝焦急的面容,那面容是那样刻骨的熟悉,似乎曾不止一次地在在他的梦境的片段中显现过。被她紧握住的手掌传来冰凉的触感,让姬无夜一瞬间醒悟过来,慌忙地抽出手避开了她关切的视线。
“你没事就好。”慕容凝的眼眸中划过痛惜与自责,她如何不知那是织梦术法的后遗症,她希望他能想起她,却又害怕他因此而痛苦受伤,不知不觉中便攥紧了拳头。
姬无夜却并未察觉,他有些纠结地小声问道:“那个……百里公子有没有同你说些什么?”
“该说些什么?”慕容凝无意识地微微偏头思索了一下。
这样的动作落在姬无夜的眼里又是一阵胸闷窒息,他赶忙开口:“没、没什么,你不知道就好。我总感觉有些事模模糊糊地,自己也记不太清,不是怀疑你……”
慕容凝有些困惑地看向他。姬无夜不知他那番伤人的话,百里长卿是绝对不会说来让慕容凝添堵的。他发自肺腑地觉得愧疚,一心想着要怎样对慕容凝好一点,好弥补一二。
“要不……你也搬来风临楼吧!”苦思冥想了半晌,他方才期期艾艾地开口。
慕容凝定定地看着他,一点反应也没给,眸中翻涌的颜色让他有些看不懂。他有些心虚地解释着:“我想着你如今怀孕了,我总该、总该做点什么,那个,你若是觉得这里住得好,不想搬也行……只要你开心、开心就好。”
慕容凝动容地看着垂首于她面前的姬无夜,他如今已经比她高了整整一个头,是手握重权的大将军,刀光剑影间可令天地变色的人物。可她看着紧张而不住搓手的他,仿佛还是看到了那个一和她对视就磕巴说不出话来的沉默少年。时光轰隆隆碾过多少年岁,将太多的人和事都变得物是人非,偏偏眼前的这个人,是她这么多年了,一直埋藏在强势坚韧内心唯一的一抹柔软。
“夫君,你是看阿凝如今可怜吗?”明明知道他失了忆,可她还是不死心地想要知道,他的心里是不是始终还有一丝位置留给自己,藏在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的地方。
“不是的!”姬无夜极快地否认,第一次道出了这么多日来的所思所想:“知道你怀孕后,我是真不知该怎么面对你,总觉得自己亏欠了月衣。可这几日,我渐渐想明白了,既然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我应该负起责任来。”
仿佛觉得这样说还不能剖明心迹似的,他犹豫了一下,有些别扭地唤了她的名字:“阿……凝,我想要好好照顾你,真心的。”
“知道你有了孩子,我心中……甚是欢喜。”
明亮的月色下,慕容凝眸中的点点星光映着琉璃般的光辉,脆弱的仿佛一碰就碎。
——
风临楼是季府的主楼,之所以名为风临,乃是因为其共有五层,从最顶层的阁楼眺望去,能将整个东街口都尽收眼底。不知昭和帝挑这一处赐宅给姬无夜的时候,是否别有深意。风临楼底层有左右厢房,如今慕容凝和白月衣各占一间,中间仅有一间书房相隔。慕容凝已经搬至风临楼月余,却连白月衣的一面都没有见着,连偶遇都不曾有过,可见白月衣躲她躲的多么干净彻底,她也乐得清静,只当这风临楼上上下下都只有自己一个人一般随意。
偶尔姬无夜不在的时候,慕容凝便也会去书房坐上一坐,她如今行动不便,却也不愿意整日闷在厢房之中。所幸虽然许久不曾执笔,她一手的簪花小楷写的却依旧如昔日一般漂亮。那日她刚刚写完一阕词,突感不适便回去休息,一时竟忘了将那张宣纸一并收去。
当晚,姬无夜就敲开了她的厢门。
沉默半晌,他坐在她的榻边,目光有些游离:“没曾想,你的簪花小楷写的这般好。”
“嗯?”慕容凝将将吐了一场,有些病恹恹地随口应着。
“我是个粗人,对诗词歌赋连皮毛都没入门。只是有句话想问,不知这首词,可是你亲自所作?”姬无夜忍着有些紊乱的呼吸,有些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的回答。
慕容凝半倚着床榻,抬眼看着他小心翼翼捧在手里的那张宣纸,复又敛了眉,淡淡地回:“确是昔时之作,一时情绪罢了。”
“果真……是你……”姬无夜颤抖着唇,那唇上竟失了半分血色,捧着宣纸的手有些难以克制地抖。
瞧见他的反应,慕容凝心下一动,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眸中陡然亮起了色彩。
“你记得?你竟然记得我给你写的诗?”
姬无夜面上的表情复杂又痛苦,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我从未怀疑过月衣,唯有那一件事。说来,也是极小的一件事,便就是这首诗。我也不记得这首诗怎的就在我的案前,我似乎也不曾翻看过,若不是那日我正巧撞见了月衣将那张纸撕碎,我甚至都没注意过它的存在。”
“不知怎地,我只捡了几张残片,脑海里竟浮现出整首词的全貌来。我虽不懂书法,那一横一勾却都跟刻在脑海里似的,熟悉无比。我也不懂韵律,却觉得这首诗再朗朗上口不过。
而今才知别离苦,心绪凄迷。红泪偷坠,满城春色还无味。
情知此后来无计,不知归期。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西。
正是这一首。”
他的嗓音低沉喑哑,吟起词来的时候沉稳有力,微微颤抖的声线更是平添了一抹凄迷,几乎让慕容凝沉醉,她强忍着情绪,克制着问:“她是怎么和你说的?”
“月衣说那是她闲来练笔之作,因觉得写得不好,便撕了想再写一首给我。可我让她将这首诗再念给我听的时候,她却不肯说。后来,她果真给我再作了一首,但那字迹虽有七分相似,我却能分辨与原先的那首并非一人所作。当时我虽奇怪,却也没有再纠察下去。却没想到,竟是你……”
“是啊,是我。几月前我与你分别,在冥州但看春意盎然,心心念念全是你。却又因为我们的孩子,不得不在那里等至春尽,几乎是一日一日数着日子过的。你不知我写这阕词的时候,是有多么地思念你。然而待我归来之日,桃花谢了,梨花落了,一切都不一样了。”她回想起当时期待又甜蜜的心情,只觉得是发自肺腑的伤感。
姬无夜捧着那副宣纸,笔墨隽秀,一字一字,相思之意,缠绵刻骨。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抬起了头,墨瞳之中隐有山崩地裂之势,面上动摇之色难言而喻:“我们之间……”
慕容凝看着几欲崩溃的姬无夜,她微微仰起头,直直的凝着他的双眼,双手费力的抚上他的面颊。
只见她极力地勾起嘴角,扯出个宽慰的笑容来:“我们之间,还真是从来就没有容易两个字呢。那时,你的记忆也没有找回来,却能那样记着我的词,我很欢喜。”
她此刻的面色苍白,却更加令人怜惜,他不知为何,竟欲哽咽。
“我觉得,这便够了,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