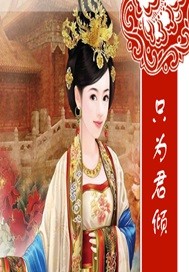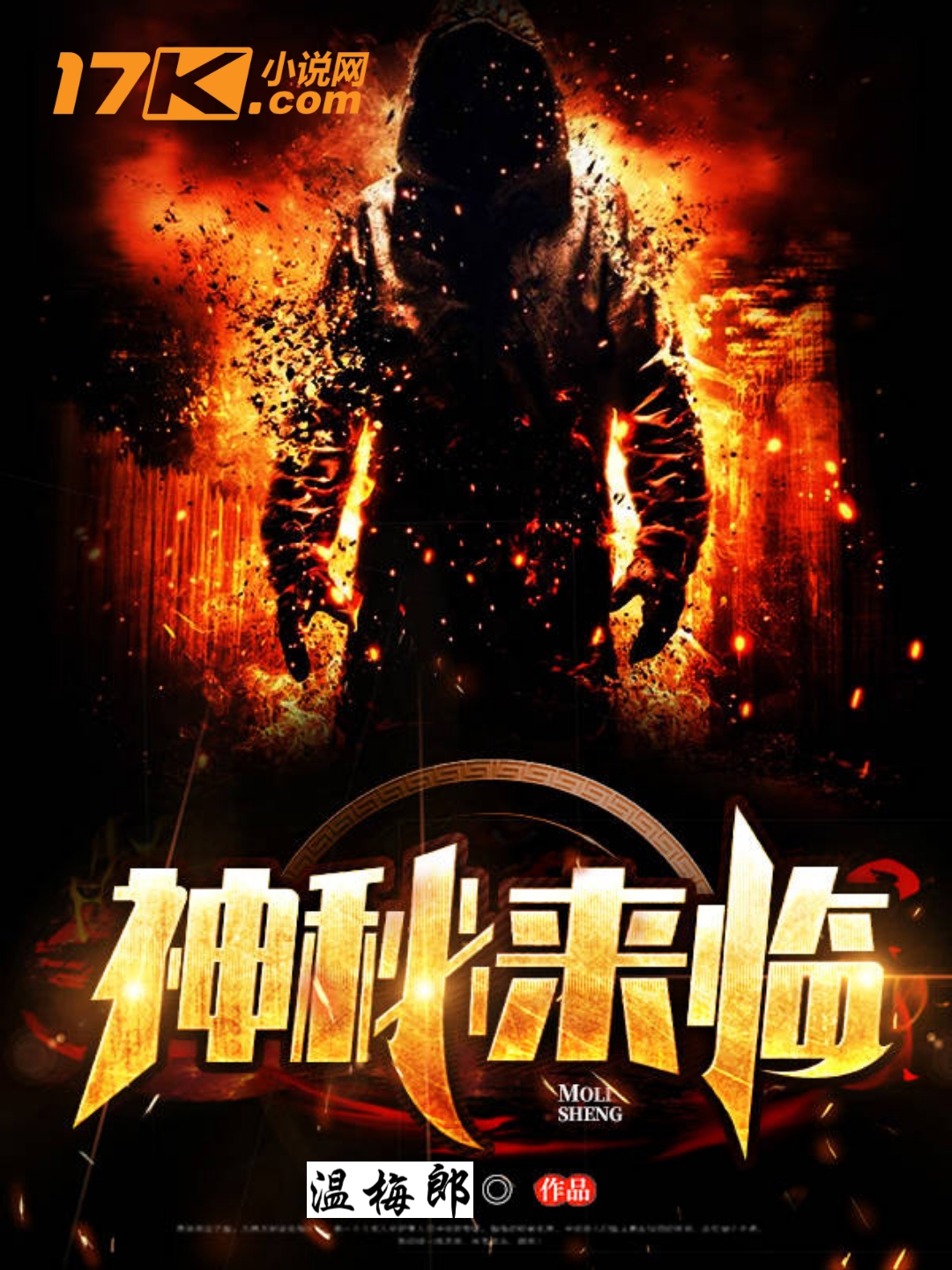楚文胥很了解楚皇,他相信齐光在楚皇帝跟前伺候了那么久,自然是更了解的。
楚皇不算暴戾也不算昏庸,他只是疑心实在太重,最怕的就是朝中权利失去制衡一边独大。
即便是太子,他也不放心,这也是为什么,楚皇明明知道齐光或许会有狼子野心,却仍放任些许,便是想用齐光来牵制太子。对于楚文胥也同样是这样,即便如今楚文胥已经是楚国的太子,将来也有可能就是楚国的天子。
但是楚皇心中还是有所顾忌,一方面,他要顾忌楚文胥身上的实权太重,会以太子之身便能行监国之责,可以丝毫不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另一方面,他又要顾忌,若是楚文胥这个太子做得太稳定又权利丰厚,定然是会引起其他皇子和旁系不满的,如此,朝廷上的利益之争便更是水深火热了。
所以,楚皇也希望齐光可以稍稍牵制一下楚文胥。
在楚皇的心中,当一个皇帝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制衡,他也将这一想法贯彻地十分透彻。
是故,楚文胥和齐光都明白,齐光这一次在边境上吃得败仗,到了楚皇那里并不会有多么严重的惩罚,楚文胥离开梧州,皇帝也顶多只不过是斥责几声罢了。两相权衡,谁都不会占太大便宜,谁也不会损害太多。
只不过,若是齐光还想把楚文胥去往明国的事也说出来,想在这上头占点便宜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明楚两国这样交战的时候,堂堂的楚国太子却跑到了敌国的地盘,这种事情往严重说很有可能便牵扯到通敌叛国上,齐光如果没有能将楚文胥一击毙命的证据,是不会轻易说出来的。
否则,只会让楚皇觉得齐光是在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地对付楚文胥,会对齐光更为不满。到时候,楚皇有了新的能牵制楚文胥的人,便也不会再需要齐光了。
所以,楚文胥断定,齐光手上即便有些东西,也不会全数控告出来,顶多也就是让他能减轻几分罪状,让自己讨上几分骂罢了。
只要,能在期限内回去楚国京都,便好了。
楚文胥的一句话落下了,朝灵立马便明白了他的意思,只是狄阳却还有些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楚文胥却也不再多说,倒是一旁的朝灵仔细的给狄阳解释着,当然,一边解释还要一边趁着机会嘲笑上狄阳几句。
渐渐的,在这个饭桌上,便只剩下狄阳和朝灵两个人互相斗嘴的声音了。
只是不得不承认,阿喜对于楚文胥的看法和心思,也因为这一顿饭慢慢有了些改观。
她跟楚文胥认识,虽然也有上了一段时间,可是实际上接触并不是很多,她只知道他这个楚国太子有几分功夫在身上,手底下又有狼队,鹰队还有狐队,这些赫赫有名十分能干的暗队,还有狄阳和朝灵这两个文武兼备忠心耿耿的人在身边。
但是她却恰恰忽视了,能够让这么多能人,在自己手上为自己卖命,恰恰更说明了楚文胥这个主子的能耐,他年纪轻轻便能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在如此鱼龙混杂的朝廷之中,还能以一个最为首当其冲的东宫太子身份,站住这么久的地位,这权衡之道和以退为进的道理,想来楚文胥要比楚皇帝更为明白。
今天这一番话听下来,阿喜觉得,楚文胥这个人或许要比他这个楚国太子的身份更有威胁力,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好应付的主。她也丝毫不怀疑,不久之后,这楚国的天下,或许就是楚文胥的。
倒也不知道是不是阿喜一顿饭想的太多,让她吃的便更少了。
楚文胥虽然替她点了几个清淡小菜和一碗清粥,那店家也细心地上了几碗能开胃的咸菜,可就是不知道怎么的,阿喜觉得自己的肚子饿极了,偏偏到了嘴边,却是什么都吃不下。好像自己的喉咙在极力排斥着那些东西,只要她敢往里头塞,它就敢让她全都吐出去。
弄到最后,那满桌的食物,阿喜可能顶多也就吃了两口菜小半碗粥下去。
她想着或许真的是因为自己太累了,左右今天晚上都是会在金瑜城停留上一晚的,等她休息好了,明天再多吃点东西,应该有力气撑着上路。
只是没想到还是事与愿违,一晚上的休息时间并没有让阿喜好受多少,反而在夜里醒过来的时候,她觉得浑身更难受了。
原本也就是因为少吃了点东西,浑身提不起力气,如今却觉得手脚发软,额头也是烫得不行,连声音都是哑了起来。
她挣扎着想起来,倒上一杯水喝上一口,却发现浑身都不听她使唤一般,力气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连抬起手都是困难的很。
阿喜撑着床,好不容易的站了起来,却没想还没往前迈上一步,脚下便是一软,整个人向着地上倒了过去,意识模糊,便是晕了过去。
第一个发现是阿喜生病的还是朝灵,第二天一大早,所有人都起了床,准备赶路。
朝灵便到了阿喜的房间来叫她,其实阿喜模糊之中,似乎是听到了朝灵的声音。可是她整个人还是晕乎乎的,连眼睛都是睁不开来,哪里还有力气回他。
只听他的声音像是在门外响了不少次,房门才被硬闯了开来,朝灵叫着她的声音便是更大了,一下子跑到了她面前,一边叫着阿喜一边晃着她。
阿喜只觉得自己耳边嘈杂的很,若不是真的没有力气,她真的很想应上朝灵一声,也免得他的声音在自己耳旁实在是闹腾。
朝灵也被地上的阿喜吓了一跳,本以为她也只是有些不舒服,在金瑜城休息一晚,睡上一觉应该就会好很多,哪里想到竟然如此严重,还昏倒了在地上。
朝灵也不敢耽搁,立马通知了楚文胥和狄阳,又吩咐手下的人,立马在金瑜城找来了一个大夫。
阿喜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床上去的,只知道一会儿的功夫,她的房间似乎就站满了不少的人,她的身上盖上了被子,右手也被拿了出来,手腕上覆上了些什么。
耳旁还有不少人在说着话,只是阿喜的意识一时清醒一时模糊,有时候能听得清那些话语,有时候却是完全昏睡的状态。
楚文胥也已经到了阿喜的房间,他坐在房间里的桌子前,手握成拳头放在桌子上,看着还躺在床上似乎看起来很难受的阿喜,眉头皱成了一团,脸色也并不好看。
狄阳和朝灵都是焦急地等在一旁,只看着那大夫在阿喜床前把她把了脉又是看了双眼和舌头。诊断完了之后大夫起了身,朝灵才是敢上前帮阿喜又盖好被子,唤着大夫坐到了桌子前,也不等其他人开口,已经着急地先行问道:“大夫,她怎么样了?”
那大夫已经上了些年纪,两鬓都是发白,但声音还算沉稳。他摸了摸自己的胡须,才是开口道,却也没有直接说,只是发了问:“不知,这位夫人这个情况已经多久了?这几日是不是少饮少食了。”
楚文胥听着那个大夫的话,也知道他是把阿喜错认为自己的夫人,只是如此紧要关头,楚文胥也不想解释,只道:“我们急着赶路这两日行车颠簸,她的确有些吃不进去东西,但之前并未见如此严重,只是昨日看样子也有些无力。”
“是水土不服加上感染伤寒了。”那大夫点了点头应了声,才下了诊断。
只是顿了顿,声音又是大了几分,看着楚文胥声音里也多了几分责备之色,“你也真是的,你自家的夫人,也太不懂得怜惜照顾了。你们这两天应该赶了不少路吧,男子之身本就体壮也就罢了,但她一个女子哪里经得起这么连番颠簸。她本就受了点伤还未全好身体本就劳损,再加着水土不服吃不下东西身体没了支撑,如今又长途跋涉感染风寒,这几样加一起,能不生病能不晕倒吗?”
那大夫或许也是救人心切,以为阿喜是楚文胥的夫人,说话语气也是重了一些。
狄阳听着,护主心思起了些,正想着要开口说话,楚文胥却是抬了抬手拦住了他,并不在意这些,只是凝起了几分神色,“她,受伤了?”
“你连这都不知道呢?”那大夫摇着脑袋一脸不喜地看着楚文胥,“你自己夫人,怎么连她受伤了都不知道?老朽刚替她探脉的时候,看到她手臂上有些许伤痕,外力所致,时间应该不久,原本是在好转的,只是这段时间估计也没怎么休息,有些反复让伤口也好得慢了点。”
楚文胥听着大夫的话,眉头皱得更紧了起来,也不回话,只是起了身走到了阿喜面前,挽起了她的袖子看了一眼,手臂上果然有着那大夫所说的伤痕,再往上挽上一些,伤痕还有更为严重一些。
所见之处已经有这些了,也不知道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受伤。但他没想到,这丫头身体这般不适,却也不知道跟他们说上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