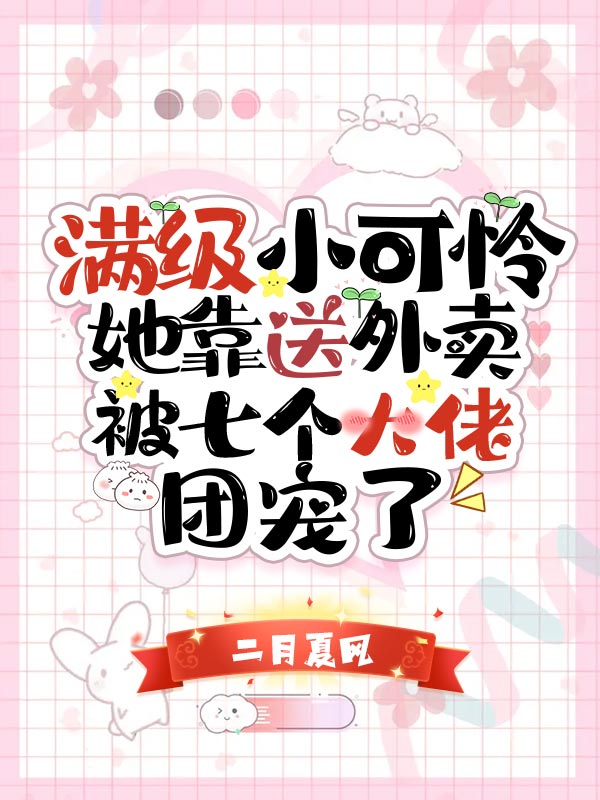九十
李仁能耐心地等琼打完电话,才回到她身边。他重新拉来一张椅子,坐在她的对面,看着她。他的神态,他的眼睛里流露的情感,琼都感到似曾相识地熟悉。
她想起来了,还在少年时代的时候,有一次从成都乘火车去西安,站了一整夜,她的腿都肿了。在她旁边,一位北方老伯数次给她让座,她不肯,因为他是个老者,没有老者给青年让座的道理。后来,老伯强行将她按到座位上,自己到车厢衔接部抽旱烟去了。为了让她坐得安心,老伯一直呆在那个地方,不回来。
在琼的眼里,李主任就和那老伯一样,是一位老者,一样有着沉默而慈祥的表情。
这样一想,她不再提防和反感他,反而觉得是不是自己误会了他。
她主动问:“主任,你没事啊?”
“没事。想和你聊聊。”
“哦,聊什么啊?”
“聊什么都行。琼……”
琼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男女相对,她最怕的,是别人引出一些让大家都感到尴尬的话题。以她本能的智慧,只能是善意地东拉西扯地和他漫谈了。
“主任你是哪里人啊?”
“北方的,关东汉子。”
“那么,我猜对了!”
主任笑笑:“当然,你听我的口音就知道了,人的口音,一辈子都改不了的。”
“嗯。只是那附近几个省的人的口音,我是分别不出来的。”
“你没有去过北方啊,如果在北方生活过,你一定很容易分辨的。”
“我没有语言天赋的。”
“你肯定没有去过那么远、那么荒凉的地方吧?”
“北方不都是荒凉的啊!”
他愉快地说:“我年轻的时候,赶牛车,常常在夜里走,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这就是北方。在大平原上,你会很寂寞,你得自言自语,得唱歌,大声地喊,大声地唱……唉,说到这里,我真是想念北方啊!我在北方出生长大,后半生却要在南方过,真是有点说不清的……”
“说不清的乡愁。”
“对,是乡愁。可能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吧。”
“总这样说!主任你其实一点也不老啊!”
“是吗?可我觉得自己老了啊。”
“唉,主任,你最想念北方的什么?大雪?土豆牛肉?热炕?野味?”
“都不是。”
“那,是什么?”
“我想念北方的夜空,夜空里的星星。在夜里,北方天空里的星辰那么大,那么鲜亮!冬天的时候,你偶尔经过一个满是灌木的丘陵,会看见灌木林中野兽的眼睛亮亮的!像那天上的星星也是这样,像那些野兽的眼睛一样亮!”
“哇,你不害怕吗?是狼吧?”
“多数是狼。我不怕,因为我一般都是赶着马车的,狼不会袭击赶着快车的人。”
琼想起《三套车》里的描述: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她问:“你唱歌吗?”
“不,我不会唱歌。我觉得很紧张,想赶快回家,吃我娘煮的面片儿。在夜里,我先是瞌睡,后来是越来越清醒——因为冷。一直那么走着,只有马车的吱嘎声响着。慢慢的,天就要亮了。关东的天亮得很沉重,很忧郁、很朦胧。我感到自己的帽檐和露在外面的头发都结了霜。在晨光里,路边亮出几枝冷峻的野花,还有一枝芦苇的茎叶上歇了只无名鸟,它看看我,颤一下就飞走了。远方积水的沼泽地,浮着片片银光……”
“真像是电影画面啊。”
琼不说话。
她不想惊醒这个沉浸在回忆中的北方男人。他已经不年轻了,回忆在他以后的生活当中,会有着越来越多的内容。
他没有沉睡。他的目的,也并非就是回忆本身。
他看看表:“我有没有耽误你去接孩子吧?”
“啊?现在吗?多少时间了?”从来不关心时间的琼,突然感到自己和时间脱钩了,错过了,心里有些着急。
“五点了。”
“那我得马上走了!我到那学校还需要半小时呢。”
“打的。”
“现在我们学校前面的的士越来越难打了,又是周末,下班时间……这样吧,我送你去!”
“那太感谢你了!”
九十一
李仁能不时回头看一眼副驾驶座上的琼,她的气色不太好,一定是心里着急的原因。他尽量把自己的宝马车开得又快又平稳,消除琼的所有不适。
面对这个娇弱的女子,他时时有呵护她的欲望。
是的,琼这样的女人,任何成熟的、有足够智慧的男人,都会知道小心待她。她是个十足的女性,那样的敏感,又没有足够的经验。她安静,常常故意把自己放到人群的边缘。她与男人既亲近又疏远,似乎没有人能够进入她的内心。
她了解男人的灵魂,却不一定了解他们的行为。她是如此纯洁!
她是只适合生活在书本里、校园里、梦想里,生活在她自己的情感里的。
她不是现在那无数的女人,不是可以被金钱诱惑的。但她同样危险,因为她会被美、被梦诱惑,被情感诱惑。而所有可能会诱惑她的,也都可能是假的,甚至是丑的、恶的。
他听到过她梦中饮泣,看到她太多忧伤神情。在她调来海大医院的时候,他也知道一些在她身上发生的事件。
他觉得她是个孤独的、需要帮助的女人。
而且,慢慢地,他已经爱上了她。
他必须压抑着这个爱。
“琼,你平时,周末喜欢做些什么呢?怎么样打发两天的时间啊?”
“没什么,就是陪孩子。”琼看着车窗外。她一直回避着他的关心,似乎他的所有关切,都过度了,让她不安。
薄暮时分,汽车一直在海滨大道上急驶。天色空茫,水天相连,琼又有了虚幻的感觉。
“想听听音乐吗?”
“不用了,这么安静,挺好!”
“我在南方,生活了快二十年了。”年长的男人十分温和地说,“北方和南方,差距太大。去年我回去过,看见老家,居然没有什么变化,几十年前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歪枣树还是那棵歪枣树,老黄牛还是那头老黄牛……”
“是啊,你要再回去,肯定是没法过的。”
“对,那边的节奏太慢了,我已经无法适应。但我在南方,虽说该有的都有了,就是从来没有开心过。”
“为什么?”
“现代人只关心别人的钱和生意,不关注他人的心灵。这一点,南方尤甚。”
“过去大家都太穷了,太没有钱了。现在都有了点钱,都去追求物质,享受一下,也应该。”
“钱由贝始,最初是为了交易。人类历史有300万年,钱的历史才有几千年。就好像人造了神来治人,人类造了钱币,现在钱币也统治了人……”
琼笑道:“希望人类早一点推翻钱的统治。但,这几乎没有可能吧?你说,会有那么一天吗?金钱失去效力。那是什么状况?共产主义吗?”
“那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
她接着说:“但是,人、主任,我喜欢听你讲北方。”
“啊,”他高兴地说,“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儿。你如果坐车在北方的大平原上,会看见成片的枣树林,所有枣树的根部,都像患血吸虫病人的腿,又粗又难看。你猜为什么?”
“不知道。”
“因为北方的枣树有个臭德性:不剁不结果。所以,果农每次收获之后,都要带一把斧子去枣树林,挨棵挨棵地剁(当然不能砍伤了树干),嘴里说:‘看你不结果!看你不结果!再不多结果就砍死你!’剁完了之后,就施肥。于是,到第二年,枣树上就会硕果累累,比上一年收获更多。”
琼笑起来。她笑的时候真是美!
“有意思。在我家乡,重庆乡下,有些老母鸡总不下蛋,整天孵空窝,咯咯叫,好像抗议人们把它的蛋都吃掉了。这种鸡叫‘赖抱母鸡’。乡下人都靠卖自家的鸡蛋换点油盐,所以就捉住它放到河水里去淹,一边说:‘看你不下蛋,淹死你!’连淹几次,母鸡就不叫唤了,又开始了下蛋。”
他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他们似乎回忆起来彼此的某种陌生,又不说话了。
经过前面的渡口,就可以看到玛利中英文学校了。
琼提醒说:“主任,待会儿我和孩子跟校车。你住的地方远,送我到了学校你就赶紧回吧。”
李仁能沉默良久,说:“我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
“什么?”琼是个容易走神的人。
“我是说,你以前对北方人了解吗?”
“北方有冬天,漫长的冬天,人们在冬天里寂寞,就喝酒、讲故事、谈恋爱。南方人忙着挣钱,没有时间做这些,这使南方人无味。北方的生活有诗意。北方天气寒冷,所以人冷峻,但他们的心却是热呼呼的……”
她调皮地扭头看他:“主任,我说的对吗?”
“对,是这样。”他回头看她一眼,说:“你应该嫁给北方男人。北方男人最疼女人,他们一高兴,就把女人抱起来往天空里抛……”
琼脸红了一下。
在嫁人以前,她向往过男人吗?她好像什么都来不及想,她没有经验,也没有人教教她应该怎么做。在之前,她甚至也不知道怎么和男人接近和沟通,怎样去了解他们。
但是,关于男人,关于异性,关于爱,她是有理想和憧憬的。美的理想,罗滋那样的男人……罗滋……她那时,对他了解吗?
不,她对他一无所知。那只是幻想,也是幻象。
她幻想过这样的男人:他强大深邃、光明华贵。他是阳光暖暖的国度,而她是它当中的一片小小花圃,一畦小小果园。她自由生长,自我完善,承受着他的雨露阳光,也奉献她的温柔忠诚。她的花瓣的每一种色彩、叶片上的每一粒水珠,皆为向他表达她的心灵、她的感激和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