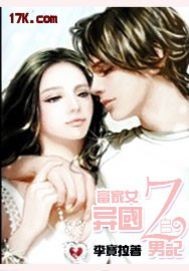我让自己气息充足,发出野兽一般的呼呼声。我感觉,这样说话会比较有力,像个真正的奥特曼。
我大声说:“战士们,现在而今眼目下,我们的敌人是自称是我们的老板的人,对不对?”
“对!”
他们真诚的呼声给我带来振奋。
“我认为,我们要找机会,有机会就一起逃跑!”
“奥特曼,你给我们口令吧。”
“口令就是奥特曼!”
“奥特曼!奥特曼!”
我突发奇想:“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一起逃跑,跑出这个破房子,我们要唱着歌出去!”
“唱什么歌啊?”
“唱国际歌吧!”雅克热情的说。
大家开始乱哄哄地唱起来。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
我说:“这歌太复杂了,记不住,也唱不全。”
“那唱什么呢?”
“还是唱国歌吧。两个理由:第一,这首歌才能让人产生勇气。第二,我们在学校里每天都唱,不会唱错。”
“可是,奥特曼,有些人不会哎,比如没上过学的。”
“我来教你们!从现在开始吧!”
雅克打断我:“Stop!我好像听见外面有声音,金毛鼠回来了!”
大家安静下来,听一阵,没动静,是虚惊。我们重新开始练习起来。
我打算以后每天晚上都领着大家一起唱,以后胆量一定会壮些。
9
夜里,除了火车的声音,没有其他动静。大家睡不着,就开始讲鬼的故事。
原来,小孩子都怕鬼。而且,他们越怕,越要说,比赛着,看谁能将各种鬼怪出现的情景,描绘得更逼真,更吓人。
惊惧的叫声越厉害,讲故事的人越得意——虽然他往往也把自己吓了个半死。
从棚屋的漏洞和缝隙透进来的光,将活动着的小孩们,照出奇奇怪怪的影子,更渲染了鬼魅的气氛。讲故事,我可是高手。我一开讲,他们的脖子就伸长了一大截——
有天晚上,我半夜醒来,看见墙壁上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扭动。我知道,那本来是一包棉花,爷爷买了,准备请裁缝给我做过冬的棉衣。
可它到晚上,就变成鬼了。
窗户是蓝色的,鸡和狗有的睡了,没睡的也一声不吭,像被施了魔法。
鬼从墙壁下来后,站到桌子上跳舞给我看,又把舌头伸出来——它的舌头是红色的,有一米长!“呼”地吐出来,像火苗,打几个旋,又‘嗖’地缩回去。
后来,它可能觉得一个鬼玩有些无聊,就一下子从窗户的缝隙溜出去了。
它去叫那些坟地里的鬼。
在我们的木房子后面,是一大片坟地,很多鬼住在那里。
我听见鬼们一个接一个,“吱嘎——”把棺材推开,出来了,很多鬼都冒出来了!它们在木房子四周跳起舞来。
每个鬼经过窗户的时候,都要吐它的红舌头给我看,还伸出爪子,往空中胡乱抓一番。哇,那指甲,白白的,像长颈鹭鸶的脖子,那么长……
“啊噢——”
小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尖叫,又疲惫又害怕,尽量挤到别人身边去。
雅克问我:“真是出来找爸爸的?”
“嗯。”
“奇了怪了,爸爸有什么好?”
“我爸爸,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我不理解。在我看来,我爸爸虽然是个大人物……”
“什么大人物?”
“博华集团老总,知道博华不?到处捐钱的那家。他还是十大经济风云人物,在电视上看像那么回事的呢,厉害吧?”
“厉害!”
“狗屁!他在我眼里就是狗屁,混蛋一个!”
“哦,我永远都不会,用这些字眼来侮辱我爸爸,永远不会!”
“那你说说,你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你得从头说,细节决定成败,从细节说!”
我不认识雅克的爸爸,可我觉得,他说话,多半已经有他混蛋老爸的腔调,什么细节、成败之类。
“得,你听好,听我慢慢道来,用手指撑好眼皮子吧——”
听说,我爸爸小时候,高鼻子,卷头发,风谷中学教音乐的林老师特别喜欢他,教他小提琴和脚踏风琴,还有唱歌,每天早上都带到他松树林那儿练嗓。
爸爸高中毕业,去一个很远的林场当知青,在那里种土豆、养猪,在那里得了肺结核。
后来他考上本省的艺术学院,因为病,只读了一年,后来就一直待在家里。他床头的柜子上,摆满了各种小药瓶。
我喜欢听秃顶爷爷咿咿哦哦读古书,听英俊爸爸拉琴。
当我听到自己喜欢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木房子就会漂浮起来,我就要飘到窗外,飘到远处的树枝上,甚至飘到更远的松树林那边去。
爷爷说,爸爸小时候不但拉琴,还会唱京戏,会讲故事。
他把学校里老师们的孩子集中起来,坐满一架大楼梯,自己站在楼梯下教他们唱歌:
月亮在白莲花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云朵像白莲花,想起来很美。
“是很美。”眼睛半睁半闭的雅克说。
爸爸有一个小收录机,可以听磁带,也可以录自己的琴声。
一到晚上,吃过饭后,他就打开收音机听音乐。
很多时候,他到外面去,在夜色里拉琴,拉一些二胡曲子,比如说《良宵》、《二泉映月》……
一些闪烁着月光的水就从琴弦上流出来,绕过我们,绕过偶尔从小路上走过的人,流向远处。爷爷就会跟着琴声,唱起来——
听听琴声悠悠,
是何人在黄昏后,
身背着琵琶沿街走。
阵阵秋风吹动着他的青衫袖,
淡淡的月光石板路上人影瘦,
步履遥遥出巷口,
宛转又上小桥头,
四野寂静灯火微茫,
映画楼操琴的人,
似问知音何处有。
一声低吟一回头,
只见月照芦狄洲……
如果他拉那支特别忧伤的《病中吟》,你会觉得深灰色的天空低垂下来,就在我们的额头上浮动。
爷爷背着奶奶,给爸爸买了一个CD机,可以听碟,它是爸爸的宝贝。
我以为雅克睡着了,刚停住,他冷不防说一句:“别停,继续说呀,来点感动人的。不过,要感动我可不容易。”
爸爸不拉琴的时候,就默默地做事情。煮饭,扫地,他把每个人的房间都打扫得很干净,把爷爷的书、杂志、报纸摆放得整整齐齐。
我病了,不吃饭,爸爸把我抱到屋后的一张小板凳上,拉提琴给我听。
他会用提琴,叫家里所有人的名字,或者用提琴朗诵歌词——那是他曾经教我唱过的一首歌:
有一只小蜘蛛,
爬进排水管道里,
天下大雨,
把蜘蛛冲出来,
太阳出来把雨水晒干,
小蜘蛛又重新爬进排水管道里……
我嘎嘎笑。
他又换另外的乐器,用口琴吹起一些很有节奏的曲子来,两只脚在地上交叉着,蹦蹦跳跳。
由于他用双手的掌心,做成了节拍器和音箱,口琴声就变得像手风琴一样,在空气中产生很多共鸣,将木房子前面那片高高的青草呼呼摇动。
我尝试跟他一起跳,但总是在该出左脚的时候出了右脚。
很多年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不管是行走,或者跳舞,如果你想和对面的人出一样的脚,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爸爸穿的是爷爷的旧反帮皮鞋,硬硬的牛皮,鞋帮一直裹至足踝以上。
这种鞋在乡下很普遍,是专门用来对付春天和秋天的泥泞路的。
爸爸就这么一双鞋,一年四季都穿,在石子路或泥水里趟来趟去,一只鞋的头,已经像河马一样张开了嘴巴。我乐了。
“爸爸,你的脚趾头跑出来了!”
爸爸不好意思,蹲下去,徒劳地按他的鞋帮,扯里面的尼龙袜。袜子也是破的。
“鞋补不上啦。袜子没补,就是知道它们想跳舞嘛!”
“你撒谎!”
“嘿嘿。”爸爸说,“那我们补袜子去啦?”
我不同意:“我想看它们跳舞嘛。”
音乐重新开始……
(插图2 爸爸会用提琴,叫所有人的名字,或者朗诵歌词。当他拉琴的时候,我就要飘到窗外,飘到远处的树枝上,甚至飘到更远的松树林那边去)
10
我梦见爸爸了。
可能因为睡觉之前,一直看着棚屋顶的那些缝隙,火车站的灯光从那些地方透进来,星星点点的。
梦里,它们变成县城夜晚的天空,星星大得不得了,一颗颗地闪亮。有的有拳头那么大,像一个随时会叮当响的小吊钟!
很多小星星,细细地,密密地,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山、或者小岛的形状,闪闪烁烁。原来,它们就是爷爷所说的星辰啊!在夜晚的天空里,他们彼此遥望,用光芒的闪烁来彼此交流,就像树和树们的交流、蘑菇和蘑菇们的交流。
它们全都有着喜悦的神情。
哦,不对。爷爷说过,星辰包括了日、月、星,一昼夜可以分为十二辰。
他教我认过水星、木星和金星,还有北极星、北斗星,还有牛郎星和织女星。不同的季节,它们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北斗星常常是在天边,组成一个大问号。天空里的星星太亮了,密密麻麻,像钻石,像水晶,而且离我那么近,仿佛只要我伸出手去,就可以摘到。
我飞起来了,轻飘飘的,有些星星就从我的耳边滑过去。
我看见了爸爸。
(西篱其他作品:《废墟之痛》http://520yd.com/book/520yd.com;
《十二重天》http://520yd.com/book/520yd.com;
《猫》http://520yd.com/book/520y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