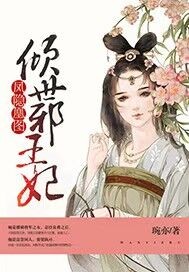邹陶双眉一振,重新凝视着她,华服裹身,步态清尘,衣袂翩飞之处糅合着无邪与高贵,他素日里见惯的女子皆是莺莺呖呖,矫揉造作,哪里见过有这等非凡定力之人?
她的眼里似乎时常泛着淡淡笑意,即便那笑意毫无温度可言,可只是冲着那份与常人相异的特殊,也实在令人怦然心动。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女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周旋在列国之间,只一计一谋便叫人万劫不复,她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在他打量她的时间里,邹陶脑海中飞快地掠过了许多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想法,而再抬眼时,已经将一切纷乱思绪尽数抛开。
他只道,“姑娘深谋远虑,胆识过人,邹某钦佩,然则邹陶此生只认当今一人,已将生死枯荣全然系于今上,除非身死,否则绝不叛主!”说罢,大步走出了营帐。
琉璃倒是因他的话一愣,没想到面对她这样的话语他居然还会如此平静,她早就看出邹陶对凌湛忠心耿耿,不可能易主,却没料到他竟然敬佩她,一个致力于天地的大丈夫竟敬佩她一个女子?
“只可惜……”
琉璃看着那墨色的身影远去,未尽的声音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右手轻抬拂过左肩上的伤处,眼神的深处,那清冷糅合着的最后一抹暖色,已经消失殆尽。
两国议和的时间比路茗所想的更快结束,琉璃乘坐马车缓缓归还,到得斜峡关城下的时候,南夜昨夜派出潜入锦耀腹地的锐士已经离开约有十个时辰了。
城门甫一打开,路茗便快步走到了琉璃所坐的马车前,一脸担忧地盯着那纹丝未动的车帘,同样担忧的还有被她勒令不准随行的忍冬,紧随在路茗身后上前,手都快触到那车帘了。
琉璃探得车外两道紧促的气息,便知来人是谁,轻摇了摇头,掀开车帘,弯身往外走去。
只见她通身乳白纱衫,略显苍白的面颊,还有纱布紧缠的左肩,以及渗出了纱布之外的血迹,路茗只觉得脑子里“嗡”地一声,像是有一根弦被人生生扯断了,“他们居然敢对你动手!”
他平素温和宽仁,如此怒态,更是平生少见,不说他一手带出来的士兵,便是琉璃都微微一惊。
可她还是点了点头,“嗯。”
路茗看她面上微白,放大到他眼内,便好似成了弱不胜衣的姿态,目光登时冷厉,转向她身后所立的将士,冷声道,“还杵在这里做什么?护不住她,要你们何用!”
她知道他此番定是要对这些人施以军法了,可是此时却绝不是做此事的最佳时候,琉璃轻拉了下他的衣袖,阻止他下令,道,“路茗哥,今日邹陶亲自前来议和,他的身手岂是一般人能及?再者,我只是小伤,并无大碍。”
“邹陶?”路茗凝眉一利,可一触到她身上的血迹,只能先将此事压在心头,伸出手也不知是想抱起她,还是想扶住她,最终却还是收回了手,道,“璃儿,这些事你暂时不要在管,我先叫大夫前来为你诊治。”
“不必了,让忍冬去为我看看便好。”琉璃没有下车,抬眸看了已经急红了眼的忍冬,又返身进入了车内。
路茗还想再说什么,可一想到她所伤的位置,以及军中清一色男女有别的大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忍冬上车,换下了原先的车夫,往城中驾车而去。
待回到房中,忍冬拆开她简单包扎的纱布,将琉璃左肩的衣襟掀开,在大片白皙无暇的肌肤上,那已经血迹凝结的伤口便直直地跳入了忍冬的眼中。
忍冬死死地咬着牙,眼前的这一位可是苍雪最尊贵的人啊,居然有人胆敢伤她,恨不得立马提剑将邹陶碎尸万段。
琉璃扫了一眼不言不语为她上药的忍冬,却没有忽视掉那双聚满了滔天恨意的眼眸,她就是知道如此,此行才没有带上忍冬的,因为她知道,如果忍冬在场,便是拼了自己的一条命,也一定会当场与邹陶拼个你死我活的。
可这却不是琉璃想要的,这一剑,她必须为了顾全大局暂时忍下,但这场仗结束,她也绝不会留下这个伤她身者之人的小命!
忍冬妥善地包扎好伤口,又为她换去了一身衣裳,这时才直直跪在了房中,“主子,属下护主不力,罪该万死!”
琉璃坐在床榻之上,除了面上隐隐发白之外,已经看不出她身上受伤的痕迹,她静静地凝视着跪在房中的忍冬,久久才毫无波动地说道,“若是死了,还如何报这一剑之仇?”
忍冬跪立的身子一凛,缓缓抬起头来,只是还未待她看清琉璃面上的神色,便见原本坐在床沿上的人已经倚靠在了床头,朝着她轻微地摆了摆手,道,“有些乏了,你去屋外守着吧。”
琉璃确实感到有些疲倦,忍冬轻浅地走出房门后,她便躺到了榻上,这一躺,那种无力的疲乏之感顿时铺天盖地地朝四面八方涌来,不消片刻,便已沉沉睡去。
这一觉很长很长,眼皮始终沉重得睁不开来,也可谓是她这数月以来睡的最沉的一回。
“璃儿如何了?是不是伤得极重?怎会到此时还未醒来?”迷迷糊糊的时候,琉璃听到屋外隐约传来路茗焦急的声音。
接着是忍冬的声音,“路大人莫急,主子的伤口婢子已经敷上了沉鸢大人留下的伤药,伤处应当无碍,只是主子这些日子以来思虑过甚,这回又伤了血气,能够这般沉睡兴许是好事。”
“忍冬。”琉璃出声时,声音虚弱得几不可闻,而且因着睡的时辰有些久了,刚出口时还带着几分沙哑。
可是再微弱的声音由忍冬与路茗听来都仿佛天籁,路茗面上一喜,便想抢先进得屋来,可手刚碰到门板又缩了回来,琉璃刚醒,他身为男子不可如此随性地踏入房中,只能转而催促着忍冬快快进去瞧瞧。
“主子醒了,可感到乏饿?厨房里备了碧粳粥还热着,属下这就去端来。”忍冬上前,扶着琉璃起身,又为她在身上垫了个软枕,匆匆说道。
“我睡了多久?”琉璃没有回应她的话,先是问了一句。
“主子睡了整整两日。”
闻言,饶是做足了心理准备的琉璃都被这个答案弄得一惊,随之淡淡一笑,那可真够久的,随后想起路茗还在屋外,便道,“你去取粥吧,让路茗哥进来。”
路茗进屋时,见琉璃还倚靠在床榻之上,便矗立在离拔步床不远不近的位置,只是那眸子却仔细地落在她的面上,观察着她是否还有不适。
见他如此,轻笑,却什么也未说,便让他维持着这适当的距离,半晌,才收敛了笑意,问,“路茗哥,战事如何?”
“按照时间来算,突袭的人马应该已经深入锦耀腹地,如今全军戒备,只等消息传来。”路茗知道她想知道的事便是他不说,琉璃也会通过别的渠道知悉此事,索性便直接将情况道了出来,也免得她再生他想。
说罢他才又补充了一句,“有任何情况我都会第一时间来与你说,这些日子你只需好生休息即可。”
琉璃没有反驳,等到忍冬端着粥前来的时候,路茗已经必须回营了,如今战事紧急,由不得他抽出太多空闲的时间,之前每隔几个时辰前来询问已是极限,此时又见她已经转醒,心下也安定了几分,便先回去处理战事了。
她不过喝完粥的功夫,忍冬便听她的吩咐捧来了最新的各方战报,当看到斜峡关暗中调遣兵马靠近长汀关的消息时,眸中不由染上几分氤氲的笑意。
本该警醒警觉的邹陶,大概是琉璃先前给他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只当她善于谋划而不擅用兵,他几度忘却了斜峡关内还有一个身为统帅的路茗。
琉璃合上了书文,掀被走下榻来。
不出意外,等到晌午过后,邹陶定会发觉南夜军的异动,可是待到那时,南夜军已经紧紧咬住长汀关守军,而他再听闻敌军突入腹地,两面夹击,先不论他是否调遣及时,用兵如神,却是已经扰乱了锦耀军心。
而他们想要得到的效果,便是如此。
这一招可是有奇效的,就算是用兵如邹陶,此时也难以将这种情绪全部压制下去,更何况,恐怕连他自己都正在不爽的边缘。
当然,这一招还是有办法的,如果是凌湛离开宫城,御驾亲征的话……
忍冬一面为琉璃梳妆,一面却仍觉得有些不放心,那纠结的神色直接透过铜镜映入了她的眼帘,可她什么也未说,其实忍冬说的很对,沉鸢的药疗效奇佳,虽然肩上仍会不时传来痛感,但感觉明显好了不少,她也总不至于用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琉璃走出屋门时,迎面正好碰上疾步而来的佚伯,对方一看到她的身影,忙上前回道,“族主,门外有人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