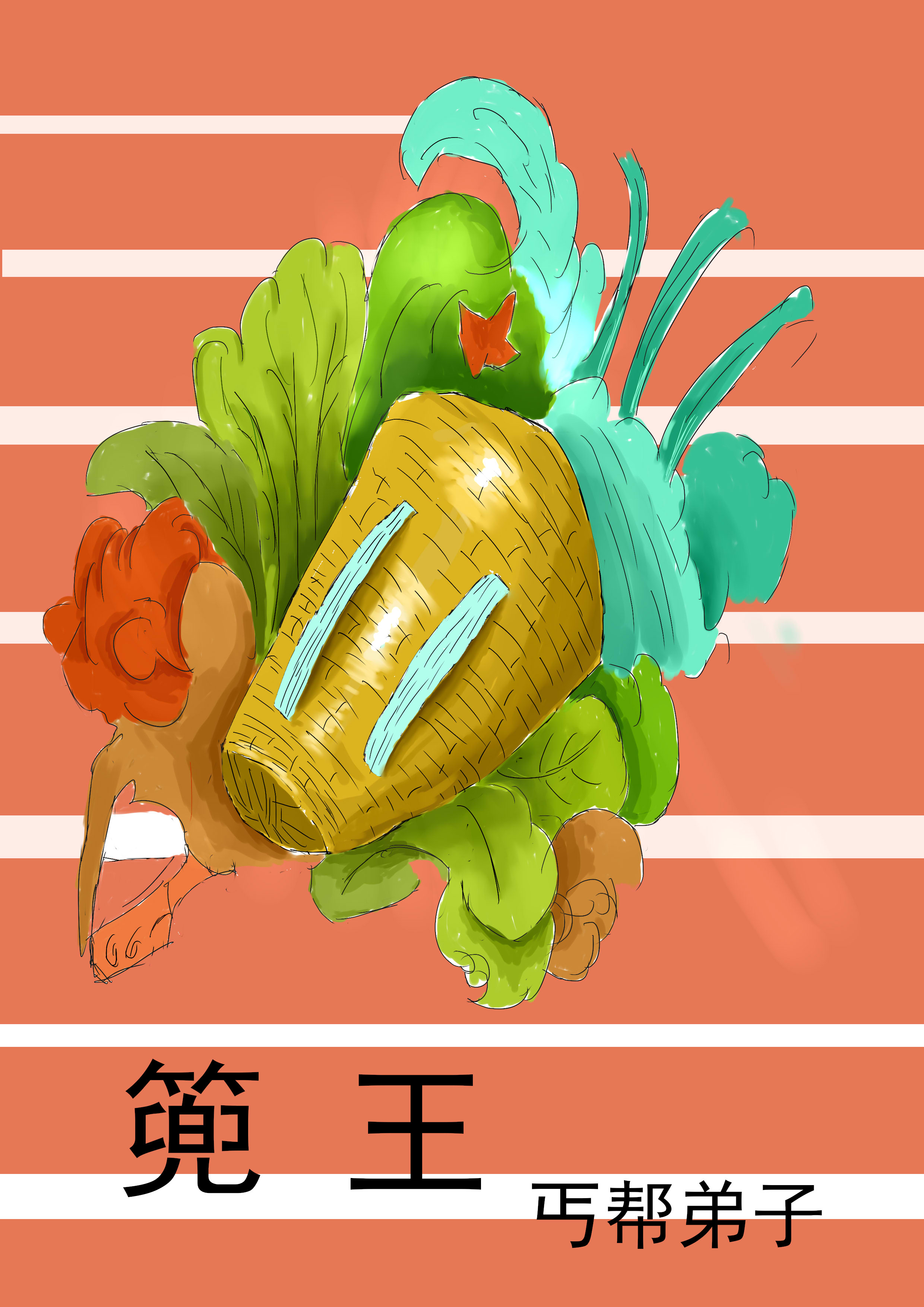那间关押张副队长的黑棚在第二日中午时分被人撬开,而后,一副垫了厚厚的褥垫的担架,横在了门口。
几位身着白衣的医护人员小心地把“奄奄一息”的张步扬抬了上去。接着,一辆红白相间的救护车也适时驶了过来,医护人员七手八脚地把病号安顿上车。
“张队长,你为革命工作受苦了!”一位蓝客队员看着绝尘而去的救护车,怜惜地感叹道。
旁边的几位队员也应和着说,但愿张队长能早日康复,带领我们继续李队长未尽的农场革命大业。
这些人都是李队长生前的铁杆亲信,在刚刚寻到了他跌落于深谷的残尸后,痛定思痛后更要见风使舵,赶忙过来解救身陷囹圄的将要顺理成章地荣升为正队长的张步扬。
如果李队长泉下有知,要扼腕叹息,虽因争风吃醋把他打入死牢,但没有及时对他的犯罪行为进行定性,使得张队长在政治上清白,反身扶正理所当然。
下午,讣告有及时发送起了效果,世界各地的李队长的亲朋好友及同事都闻讯赶来。
张步扬不顾身体的病痛来到葬礼现场,以生前挚友的身份接待着众多的吊唁者。
“节哀顺变,节哀顺变……”哭成了泪人的张步扬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但看到一对老年夫妇迈着颤颤巍巍的步子缓缓走来。
特别那老妇一路哭着死去活来,须旁边的人架着双臂才能勉强挪步的情形时,张步扬意识到重头戏要开始了,便舍弃了泛泛应酬的状态,开启嚎啕大哭模式!
只见他摆着双跨冲向老妇来的方向,半路却踉跄跌倒,边艰难地爬起来,便向老妇哭喊着:
“我不孝啊,不孝啊。没能守护好李队长,我失职啊,痛悔呀、该死啊!”
老妇人低头看着在她面前佝偻着身子哭喊的青年,一把抱住了他,一老一小相拥而泣。
“孩子,你是不是小张啊?”“是啊,我就是啊,李队长为革命工作光荣牺牲,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
“倚红,这真是太恶心了,张步扬这小子的演技要拿奥斯卡奖了。”列席吊唁的非言媚悄悄对身边的王倚红说。
“表姐,你说的是,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你说农场这真是王八碰上乌龟了,一正一副两个队长都这么下流、卑鄙。
不过,看张胖子的父母倒是挺可怜的,身为千董事会成员,腰缠万贯,这么多钱,唯一的独生子也无福消受,眼看就要带棺材里去了。”
“我看未必,他老两口马上就会有一个孝顺的干儿了。”非言媚向张步扬的方向努了努嘴。
老两口年事已高,在怪石岭处的儿子的墓碑把他们的悲恸推向了**,老妇人哭得几乎迸出了眼珠,舌头在下颌的上仰中伸长着,不断地倒吸着气儿,喉咙中发出了咯咯的哽塞的怪叫,像一个正在遭受折磨的蜥蜴一般。
张步扬见状跪倒在老妇人膝下,用脊背撑着她将要倒下去的身体,并连连劝道:
“妈,就让李队长安心地去吧!有我呢,您人家可要保重身体哦,儿子我和李队长都不想您有个三长两短啊。”
最后,在张步扬的搀扶下,老妇被劝离现场,接受医护人员的护理。
在李队长因“抑郁症”(这是他在农场的亲信向上级打的报告中所说的)在怪石岭自杀事件发生后,千度总公司立即派来了调查小组,他们也在葬礼现场。
“看这个张副队长的表现,可以暂时排除夺权谋杀,再说他也没有在案发现场的条件。”其中一位体胖的调查员说。
“我看也是,这个张队长是位至情至性的好人哦,作为同事,对死者有如此挚情,真是难能可贵。”另一位廋小的调查员也慨叹道。
体胖的思忖了下,说:“听说李队长在这农场里夜夜做新郎,稍有姿色的黑五类分子,都要过手,如果不是自杀的话,不排除有情杀的可能。”
廋子说:“若真是这样,那就案情可就石沉大海了。搞几个男女关系还好调查,就怕搞一窝,让我们无从下手!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看这李队长自杀的可能性最大,他本身有些武功,而且有众多保镖,这农场的劳改分子,皆是些穷困潦倒的下里巴人,谁能有本事杀得了他?”
“嘿嘿,你真是坐井观天,你以为这些黑五类都是些善男信女?他们中有很多在六年前革命尚未开始时,是纵横互联的黑客高手,别说杀一个李队长,把互联世界挑翻了天也是分分秒秒的事儿。”
胖子不屑地给年轻的同事上了一课。
瘦子担忧地说,“公司让我们过来调查,这天高皇帝远的地儿,只留我们调查组几人,别查来查去,罪犯抓不到,反饶上小命!”
“所以嘛,这工作的流程是要走的,但工作的深度和火候,我们还是适当把握一下。更重要的是,借这个事儿,或许我们还能借机捞一把。”
“怎么捞?这种事儿也能捞?”瘦子惊喜地望着胖子油渍渍的大脸说。
“这张队长,必是要新官上任三把火,体现一下自己对农场的管理才能。有我们在这里对这里的人员进行排查,势必会影响其正常工作。到时候,对我们必会有重礼相送,劝我们尽早撤离。”
“有古话说,雁过留声,老哥您倒是雁过拔毛,跟着哥混,好有钱途哦!”瘦子谄媚地说。
“看了吧,说曹操他就到,这姓张的来了吧”胖子向廋子示意了下。
张步扬走到两人近前,堆了一脸的笑,点头哈腰地说了些“辛苦了”之类的客套话。
胖子则严肃地说:
“张队长,我们来进行一些查取证工作,在案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农场里的所有人,都将是犯罪嫌疑人。所以,还要麻烦你跟我们回总部一趟,接受问询。”
张步扬虽说有此聪明和心机,但二十来岁的年纪,使他稍有稚嫩,脸上呈现出了惊慌之色。
“我不是凶手,农场这么多的事务,我离不开,请您收回成命,要调查就在此地好了!”
张步扬在昨晚作案之后便被老浪头重新关到黑棚中,对调查组是不是在枪上找到了他残留的指纹,或是脚印、毛发等证据并不知晓,但暗中担心自己的杀人行迹会败露。又想到如果到了总部,必会遭到严刑拷打,若顶不住招了,就便宜了非言媚等人了。
所以在调查组派人把他硬生生地往警车上塞时,挣脱出来,对胖子央求说:
“要抓我也可以,但我要带上我的证人,她能帮我做不在场证明。”
“谁?”胖子问。
张步扬小心地向伸出手指向不远处的非言媚快速地一指。“她,非言媚。”
胖子见他所指的人竟是一位绝世美女,便欣然同意,痴想着去往总部路途遥远一路寂寞,有美女相伴,倒也是一个乐事。
非言媚已经注意到了张步扬对自己指手划脚,低声对王倚红抱怨道:
“真是个蠢货,懦夫。这点儿事儿也应付不了,非要拉个人下水!”
随后两名调查员过来,在简单问询了姓名和身份后,把她也带走,塞到了警车内。
强子远远望着这情形,忧心忡忡地问老浪头:“怎么办?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啊,要不杀过去!”
“去你的吧,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还不是自寻死路。稳住,死无对证,静观其变就好!”老浪子说。
这时,经过一番护理后重新回到儿子墓碑前的老妇人,也在强子不远处看着绝尘而去的汽车,喃喃自语地对老伴儿说:
“那个被调查组带走的姑娘,怎么那么像小媚呢?”
“唉!我看你是伤心过度了,小媚早已失踪多年,怎么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地呢?”
这话让强子听了,不由在心里打了个问号?难道非言媚和千度公司渊源很深?这老妇说的小媚是不是和媚儿是同一个人?
在吊唁的人群撤走后,已是傍晚时分。老浪头痛快地舒了一口长气,说:
“终于自由了,强子,来陪我喝酒去!”
有点神不守舍的强子被老浪子拽着到他的住所走去,远远地看到门外的空地上已经升起了篝火。
几百名黑五类分子都聚集到这里,在火堆旁边摆了几十张小桌,桌上满满地放着酒菜,三五成团地吆五喝六地举杯畅饮着。
老浪头带着强子也进入了人群中,找了一张桌子,两人推杯送盏起来。
“强子,现在工厂也建得差不多了,机器也到位了,你可要跟着我大干一场哦。”老浪头边仰脖干了一杯酒,便抖着盈了酒珠的胡茬意气风发的说。
强子有点不以为然,那个破工厂以代码生产为主,服务器硬盘生产为辅,说到底还是为专制的千度公司服务,受其奴役。
对老浪头的反常常态度,强子不置可否,闷头喝了一杯酒,内心里满是对非言媚的担忧。
这时,几个蓝客队员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地来到人群的边缘不远处做出一副警戒的样子。
由于李队长的死亡,副队长也被带走,农场呈现管理真空状态。十多名蓝客队员当然不想出什么差错,见黑五类分子们聚会狂欢,便要过来干预。
老浪头见状,从兜里掏出皱把把的一叠流量币,离开作为向几位队员走去,强子见他陪着笑脸和对方解释了一通,几名队员便撤离了。
其中一位临走时撂下话说:“老浪头,看好你的弟兄们,出了事我就崩了你。”
“放心吧长官,这农场附近方圆几十公里都是雷区,我们就是想跑,也不能把命舍了不是?”老浪头谦恭地笑着说。
“这附近果真有雷区?为何我看吊唁车辆来去自如,并无忌惮?”强子问复回来坐在自己对面的老浪头。
“他们有专们的防雷芯片,我们却没有。这里的劳改分子又不像你能跃能飞,所以只能死死困在这个农场。”
强子暗自苦笑,自己似乎也飞不了几天了,在地球带来的真元之气,在互联世界的几场恶战中已消耗得所剩无几。现在只能维持自己的生命所需。
就是吃下去的食物,也要先在胃里形成一个疙瘩,再用白衣少年在自己血液中注入的编译气来消化,才能为自己所用。
长此以往,若再遇上敌手,自己体内的能量不知能否再抵挡一次战斗。心里不由焦急不安,便忍不住问了老浪头一个问题:
“老浪头,我问你件事儿,你认不认识一个人?”
“谁?”
“浪江翰。”强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得很清晰,因为名字比较拗口,生怕对方听得不清晰。
“哈哈哈……”老浪头噗嗤吐出了一口酒,仰头大笑,指着强子,神色中满是嘲笑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