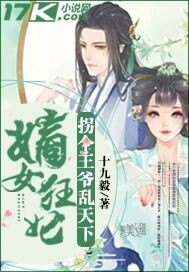百里誉低头看着握在自己掌中的那只手。
干枯,焦黄,布满深褐色的斑点。
洛琈终于有了抽回手的气力,半侧过身,不去面对百里誉,半晌,语气不善地开口道:“找不到便不必回来?大难临头,谁给你权力遣走我的儿子?”
百里誉默然地牵了下唇角,“阿尧他,也是我的儿子。我们的儿子。”
洛琈僵硬着身形,不作理会。
百里誉缓缓又道:“我让他走,是因为他的妻子曾对我说,所谓夫妻之道,就是要在最艰难的时候并肩作战、成为彼此最信任的倚靠。这个道理,从前我没能想明白,如今既然懂了,便绝不会以孝义之名强留下一位女子的丈夫。她为他而来,不顾生死成败,而此时此刻,她或许正身陷险境、孤立无援,一心期盼着他的出现,期盼着他的扶持与帮助。阿尧就算最后寻不到她,也要一直走在寻她的路上,方不算辜负。”
洛琈依旧沉默着。
地面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摇得她头上戴着的帷帽也微微颤动,晃得轻纱起伏飞撩。
好在有了前一次的经历,两人都反应迅速地稳住了身形。
领着部属尝试冲破结界的禁卫统领,汗湿鬓发,满面焦虑地上前跪倒,“陛下,末将无能。这结界……似乎无法可破!”
洛琈抬了抬手、示意那人起身,继而声音沉着地吩咐道:“破不了便罢了。若有还能用的坐骑,想办法把我的印鉴送到国师手中。”
统领迟疑了一下,躬身领命退去。
百里誉朝洛琈走近一步,“阿琈……”
洛琈下意识地后退一步,截然打断了他:“别叫我!”
她微微扬起头,侧身面对着百里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刚才,借着青灵的话,无非就是想暗示你自己的想法。这么多年,你或许是后悔过,或许也曾觉得对不起我。所以从前在朝炎皞帝面前,你尽力维护九丘的利益。阿尧帮我做事,你也从未曾阻扰过。就连现在大泽拿出钱来填补九丘赋税的缺口、从旁推动议和,也是少不了你的首肯。可这又能如何呢?从我离开你大泽侯府的那日起,你对我而言,便什么都不再是了!”
百里誉望着面前的女子,只觉得满心苦楚。
是啊,她早已不是自己记忆中那个笑容甜美、神态娇俏的九丘姑娘了……
凌厉的话锋,紧绷的身形,君王独有的威仪。
是自己,亲手将她推上了一条孤独无助的道理,一步步让她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这一次的重逢,诚然并非蓄意预谋。可这样的重逢,又怎不是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反复描绘反复臆想过的?
细想来,到底是因为青灵的一番话、触动了他心底深藏的某种情绪,竟令他一反常理地违抗帝命,亲自将她送到了南境?还是说,他其实一直在意着有关九丘的一切,唯恐战火蔓延,唯恐毁了两国议和、伤了那人的利益,所以忍不住也跟了过来?
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或许,只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牵引着,让他在今时今日这样的情境下,再次出现在了久未谋面的妻子面前。
百里誉垂了下首,声音依旧温和,“好,我懂了。”
其后,便缄口不再言语。
九转噬神杀的魔力一次次地漾开。
三转,四转,五转……
两人始终彼此沉默。
百里誉走到结界边缘,试着以各种方法找出破绽,甚至以十足十成的劲力相抗,直至面色发白,也撼动不了分毫。
他其实,也很清楚,弑杀过天帝之子的魔物,岂是轻易能破解的?
他疲惫的转过身,却见洛琈正静立望向自己,见他转身,又迅速地侧过了头。
整座北园已经开始塌陷倾斜起来,头顶上方的结界不断收拢、下压,似乎是要将笼罩着的所有事物朝地下深处挤压。
禁卫几次过来请洛琈乘上坐骑,却都被她挥手退了下去。
第六次的震动袭来。
这一次,威力明显大过先前几次。所有的人,全都失去了平衡,半跪到了倾斜的地面上。
百里誉起身搀扶洛琈,被她用力推了开来。
或是因为明白大限将至,洛琈的声音不再像先前那般冷静,夹杂着怒气对百里誉说道:“你留在这里做什么?不管这魔斗是谁设下的,要对付的人都只能是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哪里来的就哪里回去!”
百里誉并不接话,默默解封出一柄长剑,大力贯入地面,扶住。
身下园中的青石地板早已零零散散地被卷入了殿内,就连泥土地,也倾斜的厉害,靠外的一侧慢慢上扬翘起。
先前还不肯放弃希望,结阵、合力、使出浑身解数尝试突破结界的禁卫们,此刻也都放弃了,散开围坐在不远处,以身体连接筑出一道屏障,挡在了洛琈与魔斗之力的中间。
第七转。
有离得殿宇近的禁卫被卷了进去,半空中发出仓皇的呼喊。
死生一线,终究是本能占了上风。
洛琈身体微倾,帷帽亦扬了开来,露出苍白而衰老的容颜。
九丘洛氏的情咒,在她的眼角和唇边留下了无数道凄苦的皱纹,也染白了鬓边头顶的发丝。
唯有那双眼睛,依旧像从前一样,清透妩媚。
她直直地望着百里誉,“为什么不走?你来时用的那个通道,以你的水灵修为,或许还能打开,你为什么不去试试?”
百里誉凝视着洛琈,似乎丝毫没有为她容貌的剧变感到惊诧。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嘴角笑意清俊温柔,“我已经弃过你一次了。一次,已经太多了。”
洛琈的目光一瞬不瞬,直直地瞪着他,仿佛是想借此来表示自己的无所谓。
然而泪水,不知不觉间,却已流了下来。
“你不是弃我。你只是在我和你的家族之间,选择了后者罢了。”
洛琈咬着唇,“从前我不明白,怨过你,恨过你,可后来……”顿了下,“后来我接替了阿玚的位子,成了九丘的国君,一举一动皆牵系足下万民性命,又怎能不懂……你当日的不得已?”
百里誉眼中情绪翻涌,唤了声“阿琈”,缓缓朝她伸出手去。
这一次,洛琈没有躲开,任由百里誉一手拄着剑,一手拥住了自己。
她微垂着头,额头轻触着他的衣领,低低道:“这么多年了……我对你,其实,早已无怨亦无恨……可我……”
蓦地顿住,不再继续。
百里誉语气淡然地接过了她未完的话,“可你,也无法再爱我了。”
洛琈抬起头来。
百里誉的视线却落在了别处。
他费力笑了笑,道:“我明白,有些错,一旦铸成,便再无可挽回。伤过的心,亦是无法痊愈到不留半点痕迹。你能不再怨我,我已是此生无憾。”
他沉默了一瞬,低下头,望着洛琈,“可我还爱着你,一直都爱着你,一辈子也只爱过你。”
也不是没有试过遗忘,劝自己接受一切只是一场错误,可终究,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时我太过骄傲、不懂退让,只一味想着要你迁就我的不容易,却忘了顾及你的难处、你的不容易。我把你我的结局归咎到命运身上,怨过身份的禁锢、怨过洛珩的疯狂、怨过皞帝的狠绝,甚至憎恨过家族赋予自己的责任。可其实说到底,我只是懦弱了,懦弱到只敢委曲求全、只敢明哲保身,却从不敢想、更不敢尝试,找出两全其美真正解决矛盾的法子。”
顿了顿,“这些年来,我从旁瞧着阿尧和青灵的相处,见他们一点点地拉近朝炎与九丘、化解纷争,甚至重筑整个东陆的政局,既让我觉得惊讶,更让我觉得自惭形秽。这两个孩子,从一开始被政治绑到了一起,连我也从未相信、有朝一日他们能够向彼此交付真心,到如今这般的同心共志、不离不弃、生死相随。他们身后牵连着数不清的利益纷争、家族血仇,比起我们当年,复杂艰难了何止百倍?说起来,我百里誉一生自诩精明,可却实在不如我的儿子,更不如阿萝的女儿。”
百里誉牵了牵嘴角,露出一道略显自嘲的笑来,“所以现在,上天要罚我,罚我到死、都只能爱而不得。”
洛琈的眼泪簌簌不停,几番翕合嘴唇,却始终说不出话来。
要说无所作为,她又何尝不是?
只想着九丘的危难、洛氏的存亡,一味地将丈夫的无奈与选择归罪于背叛。
这么多年来,一颗心,确是长出了坚硬冷酷的外壳,可那些暗藏的悔恨与自责,又何曾真的消失过?
半晌,她扬着头,颤颤巍巍地问他:“所以……你是后悔了吗?后悔一开始遇见了我……”
“怎么会?”
百里誉的双臂微微收紧,笑看着她,“从前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一双世人艳羡的儿女,按着我们生意人的算法,纵然最后,想要的仍是没能得到,可收了这许多年的利息,我已是赚了。”
洛琈闻言,似是也想笑,可眼泪却愈加汹涌,唇畔挤出来的弧度竟比哭更难看凄苦。
第八次的震动袭来。
天摇地动,山崩地裂。
围护在洛琈前面的禁卫,尽数被卷入了流光与暗砾交织的巨大漩洞之中,四周天昏地暗、一片混沌。
百里誉紧握着剑柄,稳固住两人的身形,施展出最后的神力与魔斗抗衡着,却依旧挡不住一点点被拉入暗黑之中。
狂风扬起他额前被吹乱了的长发,闪烁的流光映照在他轮廓清俊的五官上,一如许多年前初遇的少年。
洛琈仰头凝望着他,突然间,竟觉得前所未有的安宁平静。
一生之中,见过太多的腥风血雨、征战杀戮,悲欢离合、情义责任、家国权力,一切的一切,到了最后,又有什么意义?
若能再选一次,自己可还会愿意在那一天、出现在同样的地方?
飘零的思绪缠绕着陈年的回忆,不知不觉间便说了出来 —
“你可还记得,那夜凭风城新年庆典,我站在堆满蓝铃花的船头,对你说过什么?”
“当然记得。”
那夜她垂着条辫子,跟几个大泽的船娘挤在一起、俯身浇着水花,皮肤白皙的一看便知不是本地人。
她的莲灯,撞翻了他的许愿灯。
旁人都认出了他是百里家的公子,低声催促着她道歉,可唯独她不识得他,起身挽着辫子财大气粗地说:“不就一个愿望吗?你求的是什么,我赔给你就是!”
他于灯火波光之中静静望着她,轻轻浅浅的笑意让她最终莫名的红了脸……
很久很久以后,久到孩子都已经生了两个,她才偶然获知,那晚他那盏被撞翻了的许愿灯,原是被朋友硬塞来的姻缘灯。
签上,一共就写了四个字:
一 世 良 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