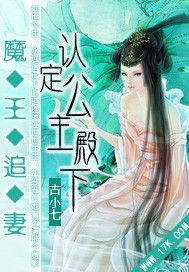就像平常一样,每当店里没有什么生意时,芊芊就喜欢坐在门口,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
除了路过的之外,这些车辆和行人,大部分都与一监狱有关。
或者是一监狱的警察和他们的家属,或者是一监狱犯人的家属。
有人说,幸福就是两点,一是医院里没有咱家的病人,二是法院里没有咱家的犯人。
这些人,许多都是监狱里有他们家的犯人,他们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
一监狱里关了八千多犯人,他们倒好,自己进去了,图个清净。可是,他们的家属就倒霉了。
一年四季,刮风下雨,每天都有从四面八方来的家属,大包小包地,千里迢迢来探望他们。想想,其实也怪可怜的。
唉,管别人的事儿干什么呢,我自己的幸福又在那里呢?难道就这样,跟那个黄书友过下去?
今天,芊芊的门前显得比较拥挤,因为梅右前院子里的四辆越野车都出动了,门前还停了一台大吊车。
“他说要和两个朋友做二手车生意,看来,今天是开张了。只是吊车都来了,想必买的车也不会是什么好车,否则,也不会用吊车去吊。这能挣钱吗?是不是提醒一下梅右前,别被人骗了呢?
管他呢,最好让他赔个精光,到时候,没钱了,让他跪下来求本姑娘,那时候,我再帮他,就成了他的贤内助了。”
芊芊没头没尾地胡思乱想间,就见一架直升机从隔壁院子里升空,向一监狱院子里飞去。
“不是说做二手车生意吗,怎么鼓捣起直升机了?”
芊芊还没想明白,就见梅右前那个较胖的朋友,开走了吊车,吊钩上,还挂着一个大铁箱子。
跟别人开吊车不同,这台吊车开的飞快,很快就在一监狱大墙的拐角处停下来了。吊车臂开始伸展开来。
“难道一监狱的锅炉烟囱又坏了?他们是给一监狱换烟囱的?这个梅右前,看来还真的有两下,把买卖做到一监狱里去了。可是,他们的锅炉烟囱才换了不长时间啊,怎么这么快又坏了呢?”
芊芊以前见过一监狱生活区换锅炉烟囱,据说是锅炉房那里地方太小,吊车进不去,所以,吊车才停在大墙外面进行吊装作业。
那次吊装作业,芊芊没当回事儿,可是,她的邻居梅右前却当回事儿了。因此,钱多多和凡奇策划了这个方案,用吊车把圣林从生活区吊出来。
这是个异想天开,不宜引起注意的法子。
实际上,就连大墙上的武警,起初都没有在意。
因为以前有过类似的做法,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次,还跟以前一样,是要修锅炉。
就在芊芊疑问之间,就见一辆车飞驰而来。芊芊认得那辆车,正是梅右前的那个瘦一点儿的朋友开的那辆,刚才比吊车开走的早一点儿,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只见那车在一台大货车后面急速掉头停下,那人跳出越野车,只一下就爬上大货,大货发出一阵轰鸣,后轮冒出白烟,飞快驶去,然后一转弯,横在马路上,把马路封得严严实实。正在行驶的车辆,只好停下了。
那个瘦子一下子从大货上跳下来,没几步,又一下子跳进他的越野车里,又是一股白烟冒起,随后传来刺耳的声音,越野车飞快而回,向着吊车方向前进。
那吊车吊着个铁箱子,也正飞快返回。芊芊看见,大墙上的哨兵也跟着吊车往这边跑,边跑似乎还向吊车开枪。
那架直升机也跟着吊车飞,从直升机上,还掉下来一个什么东西,被铁箱子上的人一下子接住了。
此时,芊芊才意识到,原来吊车没有吊什么烟囱,而是吊了一个人。
从监狱里吊出了一个人。
从监狱大门跑来一帮哨兵,手里都拿着枪。一边跑,一边向吊车和铁箱子开枪。
空中铁箱子里那人手里也拿着一个大枪,一瞄准,大枪里就吐出一张大网,把那帮哨兵全都罩进网里。
那帮哨兵想挣脱,可是,越挣扎,网越紧,直到把一帮人向粽子一样捆住,再也动弹不得。
到了金如意门口,吊车停住。铁箱子还没落地,一个人就从箱子里跳出来,几乎同时,梅右前那个胖朋友也从吊车上跳下来,此时,梅右前也从院子里冲出来,三人也不说话,各自跳进车里。各自拿出个警灯放到车顶,几股白烟从车轮下冒起,又是一阵刺耳的声音,芊芊本能地捂住耳朵。
但她的眼睛还是看的清清楚楚的,三台车飞驰而去,最前面的,是那个胖子,早先那个瘦子在三台车过去后,跟了上去。刺耳的警笛声想起,原来,最前面和最后面的车顶,不知何时亮起了警灯,最后那辆车的牌照,也从蓝牌变成了白牌。
路上的人和芊芊一样,也被这一幕惊呆了。
这是要干什么?拍电影吗?不是倒腾二手车吗,怎么又拍上电影了呢?
不对呀,怎么没见到摄像机呢?
四辆车没影了,芊芊终于回过神来。
梅右前确实把活儿干进了一监狱,只是不是吊烟囱,而是吊了一个犯人出来。因为箱子里那个人,下身还穿着一条囚裤。
只是梅右前的两个朋友,怎么会穿着保安部队的衣服呢?看来是假冒的。
天杀的梅右前,原来你根本就不是做买卖的,而是劫狱的。你骗我!
芊芊无力地坐回椅子里。
“芊芊再见。”
芊芊回忆起刚才梅右前从院子里冲出来时,跟她说了这么一句。也不知怎么回事儿,芊芊竟然冲着梅右前逃走的方向挥了挥手,心里也说了两个字。
“再见。”
一排长刚刚向连长汇报了暗访组检查的情况,得到了连长的表扬。就在此时,停电了。他看了一下手表,是4点钟。
监狱停电的事儿,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偶尔还是会出现的。比如线路春检、秋检,或者是欠费太多时,供电局拉闸停电。
每到这些时候,他们这些负责第一监狱警戒的保安部队,都会接到通知。
监狱会启用自备发电站,用柴油发电。即使生产用电不能保证,但是,大墙电网用电,却是无论如何都要优先保障的。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一排长意识到,事情远非停电那么简单。
一台吊车停在了监狱生活区的墙外,几个月前,锅炉换烟囱时,曾经在那里进行吊装作业。
不过,那次监狱事先通知了他们,他还派了两个战士到现场执行警戒任务。这次,却没有接到狱方的通知。
按照规定,监狱如果进行这样的作业,是必须事先通知负责外围警戒的保安部队的。今天没有通知,就一定有些异常。
就在一排长准备派大墙上的哨兵去查看时,对讲机里传来那个哨位的报告,说有人接近大墙,一个监控探头被扯了下去,大墙照明灯已经熄灭。
说到监控。一排长回头看一眼监控屏幕,已经是一片黑屏。按了几下键,也没有什么反应。显然,监控坏了。
接下来,一排长沮丧的发现,固话不通,手机不通,网络不通,一监狱的自备电站也不发电。再加上此前的停电、监控失灵、有人接近大墙,作为一位富有经验的老战士,一排长立刻判定,肯定是有状况发生,而且,绝对不是小事。
但是,一排长也不是太担心。
大墙以内的警戒,由监狱警察负责。大墙之外的警戒,由保安部队负责。
一排长相信,即使发生犯人脱逃,甚至爆狱的情况,即使警察们处理不了,到了他的警戒范围,他也完全可以控制事态。
他不相信,有人可以冲出保安部队的警戒范围。
战士们的枪,可不是吃素的。
只是刚才飞进去的那架直升有些不对劲儿,难道又是哪个商家做广告的?会不会跟监狱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这也太夸张了吧?又不是外国大片。难道还会有人驾驶直升机,把犯人从监狱里弄出去?
跟狱方的联系仍未建立起来,电力仍未恢复,大门和供行人通行的AB门也打不来。
一排长喊门里的警察开门,警察说:有犯人逃跑,其他人都去增援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打不开大门。
这个狱警确实没有撒谎,那个电动大铁门,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只是靠着人力,一个人确实打不开。
此时,对讲机里传来互相矛盾的命令。
狱侦处长赵玉棠的命令是:逃犯在生活区,向生活区靠拢,要哨兵开枪,截住逃犯。
监狱长赵观澜的命令是:逃犯在九监区,向九监区靠拢。哨兵坚守原岗位,就地警戒。
一排长虽然无所适从,但也不愿意无所作为。
他判断,狱长和处长的命令可能都是对的,是有两个罪犯同时逃跑了,只是分头行动而已。
于是,他跑到大门对过的店铺里,借别人的电话。
手机仍然不通,他就找固话。虽然现在用固话的人不多了,他还是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一台固话,打通了连队,要求派人增援。
虽然事态还没有蔓延到他的防区里,一排长还是宁愿多做一手准备。
即使监狱警察们控制住了事态,没有扩大大自己这里,增援部队白跑一趟,也是值得的。
出了超市,一排长就发现,那台吊车的长臂已经探进了大墙内,正在往外吊着一个吊斗。
他立刻明白了这台吊车的意图——有人劫狱!
他立刻带领门口的4个战士向吊车冲去。
进入射程,一排长毫不犹豫地命令开枪,可是,射击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反倒是吊斗里的人射出一张绳网,把他们几个罩住了,绳网越裹越紧。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四台车扬长而去。
这回,一排长看清了,其中的两个人,正是刚刚来进行暗访的所谓“首长”。
这两个“首长”,以检查为名,把执勤哨兵们的子弹集中到一起清点……。
天啊,怪不得刚才的射击没起什么作用,难道是他们偷偷把子弹给掉包了?
一排长猜对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
警察们合力打开了监狱大门,赵观澜等一大帮警察冲出来,向着吊车方向奔去。
那台大吊车,此时静静地停在路边,离吊车大约五米处,一架无人直升机的残骸正在燃烧。距离直升机大约10米处,几个战士仍在绳网中挣扎。
马路上堵满了车辆,烦躁的喇叭声不时响起,间杂着司机们的咒骂声。远处交通岗上的交警已经赶过来,正在那辆横在马路上的大货车上,试图把大货车移开。
一监狱的五台警车停在门口,它们也只能停在门口了,因为路已经被来往的车辆堵得死死的了。
喇叭不断地叫着,警笛一直响着。但是,毫无用处。警车就是动弹不得。
“卫狱长,立即报告省局和省厅,联系兴阳市警察局设卡堵截,请求省警察厅启动五省追逃机制。
狱侦处立刻开展侦查,尽量查清劫狱人员的身份和作案手法。抽调精干力量,开始追逃。
狱政处立刻点名,进行隐患排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各生产监区停止生产,立刻收工回号,清点押犯人数。
……。”
几个警察好不容易弄开绳网,把一排长几个人解救出来。
就在此时,副连长也带着20多名战士,跑步赶来了。
驻地通往一监狱的唯一一条道路,被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一辆大货车给堵死了。他们的车出不来,只好跑步赶来了。
“我们的人有没有伤亡?”
赵观澜问郑新民。
“没有伤亡,就连一个轻伤都没有。”
“看来还是对我们手下留情了。”
赵观澜轻声道,除了郑新民,没有人听见他说了什么。
“好了,接下来,就准备应付铺天盖地的舆论和压力吧。”
赵观澜看了赵玉棠一眼,赵玉棠点点头,她明白,真正艰难的时刻,现在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