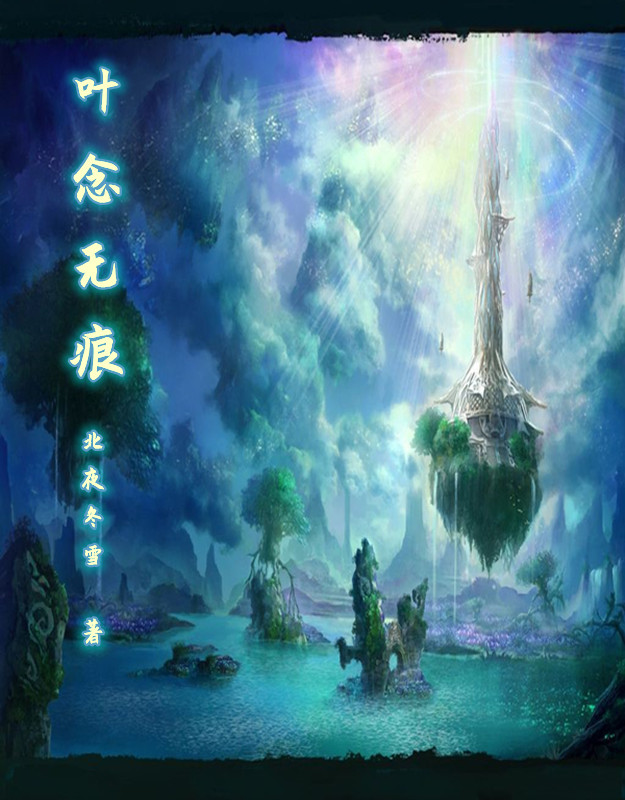寝宫中,鲁元公主愤心漫至,熊熊烈火早已煎熬在了心头。
她自是愤愤不平,前日方才与那苏哥哥共座一齐用膳,今日竟沦落到了如此的地步,她真不敢相信,太后竟会为那霍府之事,便对她下了如此的狠意。
那霍府算什么东西,怎得劳她母后付了如此的心思。她越发不思其解,怅然恼怒。
她还是没有参透太后的意思,便只得依依自叹着。
“公主,您吃点东西罢...您早膳不用,午膳也不用,奴婢怎与太后娘娘交代...”另旁的花卉苦苦哀求道,临勾起的愁眉似月,一脸的急迫之象。
“花卉...此事与你无关。”公主淡声道,只是临着头扶着脑袋,眼睛微而一闭,又轻而一睁,满面的愁容让花卉的心又紧了紧。
“怎能无关...太后若是知晓公主今日未曾进膳,奴婢的脑袋怕是要保不住了。”花卉低首急急落道,颤心抖瑟,“也请公主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多多少少吃点什么罢...”花卉又临身而近,膝跪而下,安声劝道。
鲁元公主闻声后默叹,似若无动于衷,又微眼撇了一下花卉,眸若空醒,望而无际,又再叹了一声。
“公主...”花卉苦心相劝,公主盼若无睹。
也罢,这鲁元公主就是如此,曾几何时让这些奴婢太监们省得了心?他们也皆看着这公主的脸色过日子,实在是难言以持,可说是已早早地习惯了。
但他们也不解其意,这太后可从未如此狠心待这鲁元公主,甚不想竟是为了那霍府之事。
良久,那公主终于受不住这虚下的折磨,终于起身跨步振声而去,可殿门前的侍卫是太后亲派而来,怎会就如此让她轻松就走了。花卉见状再紧紧速步随去。
她方才临近了那殿门,便虚而被那影门临出来的威立身影唬愣住,终于摒心握气,便狠狠一个拍手而去。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公主扬喉昂声一喊,可这吼声丝毫振不了那殿门前的侍卫的身,其几人身影仍矗立如山,连一个稍下抬头皆无。
“公主...您别这样,太后会愈发生气的...”身后的花卉匆匆步至,再悠悠劝道,生怕这公主又再惹出祸端,让那太后火势不收,那便全然无了机会求得原谅。
公主见那殿门前侍卫无声以出,心里愈发燎火漫飞,面上又咬牙切齿。
“快放我出去!我要见母后...”她愤吼着,“你们竟敢如此蔑视本公主!待我出去,有你们好看的...”她开始威胁起殿门外的侍卫,扬袖振而一挥,切齿道。
“这是太后的命令,公主还是好好待在寝宫里罢。”殿外终于传来几个似冷冰雾剑一般的轩昂声,竟耀显得那般无畏,“若是公主离了此处,我们也不好向太后交代。”
公主闻后便自知不能如此硬来,又开始漫心冷静下来,忽心沉沉,又临着殿门贴着脸,欲要好声好意与那侍卫言谈一番,以软计取胜。
可她貌似太小瞧吕后了,如此便显得不自量力一般。
“侍卫大哥...你们就放我出去罢。”她先是欣声一笑,故作出满面喜色,唇角扬起一番波澜,可却不是真心切意。
“公主,您就...”花卉轻声暗道,她也知晓那侍卫不会如此便宽心而至,可还未言毕便被公主狠狠斥断。
“闭嘴!”公主忽而厉声呛道,惹得那花卉不敢再轻言什么,便只能低首而过,抿嘴默默。
公主又临出几下娇柔笑声,双手抚着那殿门,尽了力地与那殿门外的侍卫愈发贴近,又沿着门缝微微探过殿外之景。
“侍卫大哥...快放我出去罢,本公主会记着你们的。”她依旧不肯放弃,便不假思索道。
公主如此淡声临笑,那侍卫依旧全然不予搭理,无论公主如何言声好意,皆得不到那殿门外的一声回应,她又终于七窍生烟了。
须臾,殿门外一个昂然凝声将公主此刻的无声怯愤收容了起来。
“太后娘娘。”闻那殿外侍卫恭礼道,公主速速地收起那番咬牙切齿的模样,闻殿门声一振,她又疾步转身而过。
临后的花卉闻声知其所然,便微而退步而去,屈身并礼。
“太后娘娘到。”随那殿门敞开后,扬声而来的便是那王生公公的传到声。
接着便开始敛过一阵簌簌冷风,凉透在公主心头。
公主自是在与那太后赌气,完全无视身后威立着的太后,竟踱步往前就去,忽而一挥缎袖便坐了下去,再并手栖于膝上,满脸不自乐,又撅起小嘴来。
“太后娘娘...”那殿门旁屈身的花卉微声落道,“公主她...”她又结声道,心里狠颤一番,眸转四探,不知晓该言些什么。
太后自是从宫女嘴里得知公主绝食之事,便扬袖一起,落步而去,满脸肃然,临着冷风亦不惧。
落至那公主门前,太后微而一睨那桌上的膳食,仍完尽如也,公主是滴米未进。
“又与哀家赌气?”太后肃声道,实是没有一点笑意,满面的肃然令旁人漫心怯过。
公主抬眼悄悄睨了那太后一眼,甚是许久未见自己的母后如此肃面以对,但仍是悠心闷气,腹中有道不尽的愤声、言不完的委屈。
“母后为何如此待我...”公主喃喃道,低首如初,“莫不成真是为了那霍府之事。”她蹙着婵眉,再显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是!”太后厉声确道,“你如此之作,是乃无视霍府,无视霍相!你让哀家如何不处罚你?”太后故作一副怒发冲冠的模样,狠挥一把衣袖,再扬风坐下。
“我没有!”公主驳声道,昂首而起。
“没有?你探而虚往,方才踏入霍府便临身而走,你让哀家今后如何倾待霍府?”太后肃目对之,公主扬目而过,微而泄下了气势。
“我...那是霍府阴气太重,我才...”公主胡里八道,自是再没有言辞反驳,便随口脱声一出,怎知此言会再番惹怒太后。
“满口胡言!”太后嗔怒斥道,愈发地怒不可遏,“霍公子卧病无助,你不好声问候,竟如此咒言相告...瑶儿,你太让哀家失望了!”她怒声落道,再摇头而过。
太后言后便扬袖耸而站起,落袖轻荡无痕,她怒形于色。那鲁元公主瞧了亦是心中狠颤,终于知晓自己惹了何许大的祸端。
“母后,我...”公主随之起身,怅然自道,“我错了母后。”她终于知晓认错,但已然于事无补了。
“你就在此好好待上几个月罢,时日一到,哀家自会放你出去。”太后肃然道,言毕后便踏步要走。
公主闻声愈发地焦心如燎,又急不可耐,便落步随之身后,着手便拽住她的衣袖,不肯松放。
“母后,瑶儿知错了!母后不要禁足瑶儿...”她苦声疾首,可那太后无动于衷,仍是面显深肃。
“这皆是你自己闯下的祸端,莫要责怪于旁人。”太后狠袖一挥,空袖临风便将那公主无情地往后一推,公主并手一空,忽而便坐倒在地上。
公主空眸似墨,恍惚不定,仍悉抬着手临于半空,怜目淡望着那太后的背影,心沉如寂,淡心无色。
“还有,勿要用绝食来威胁哀家,否则,你便再也见不到你的苏哥哥。”太后泯心漫过,忽而转过头来,肃眸一撇,悠声落道,势如凌气冲生,面若傲降百嗔。
这话可把那鲁元公主的心狠狠地虐刺一番。
公主闻后悚心惊颤,抖手厉下,匆而紧叹。她不曾想她的母后竟会搬出她的心爱之人来降住她,更不曾想她的母后竟会视那霍府如此之重的地位。皆是她屑意了。
可她未曾知晓,太后如此之举是对她最好的保护。
最英明之人还当属太后娘娘,如此之举不但拥护住霍皖一派的势力,予了那霍皖十足的面子,亦有理由倾护住她的公主。
如此一来,鲁元公主便不敢再做出一些格外之事。
她这辈子可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没有这公主的尊贵身份,可以没有这雍容华贵的生活,可以没有这皇宫的所有一切,但方是不能没有她的苏哥哥。
一落夜,公主怎般皆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只是脑里全全浮着那苏霖的影子,浑然不去,缠了她足刻半夜。
小窗临进的霜色月照方才让她迷心淡解,终于好不容易地入睡。
寝宫里黯声墨色,方才复了那往日般的安宁。
临风飒飒悄然拥入魂,阑月茫茫微声倾入身。
云灵临于窗下,望那浮华落月貌似一日较一日金黄,世上的一切彷若如此,繁声迷途,朗生若朴。
苏府的生活让她满是惬意。但她心中另有一颗沉石难以磨尽。
她并无落忘她来这长安城的目的,二十年的搜寻,她不能就此放弃。
但苏府与那霍府的恩怨,她实是不得不插手一番,只因这苏府之人待她尚如亲人,她不能坐视不理。
她也忙若故求,苏霖切不要对她有别意之情,否则予何人来说,皆是痛切疾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