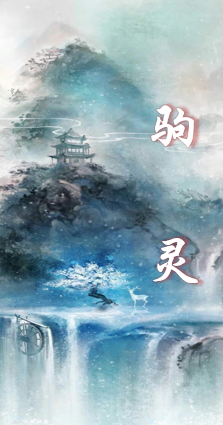夜凉如水,云遮寒月。到了下半夜,黎明时分,山风愈发的刺骨寒凉。
凌舒痕加了几次柴,才让火堆保持着原有的火光,四处漏风的破庙里才得以有一丝温暖的气息。
白瑾依旧卷缩着娇小的身体坐在茅草堆上,发着楞,不知在想些什么。身旁的木架上还有几只烤鸟丝毫没有动过,静静地躺在那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凌舒痕刚将手里的最后一根木柴扔进火堆里,才一转身,便看到她一个人坐在那里愣神,时而咬咬嘴唇,时而皱起眉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装载不下的满目柔光溢出眼眶,嘴角勾起一笑,随手拿起一只盛着温水的竹木筒走向她,问道:“在想什么想得如此的出神?”
白瑾听他这么一问,抬起头来,一张小脸面无表情,半响才轻轻地吐出一句话,“我在想玲珑体内的寒毒。”
凌舒痕听后收起了玩味的表情,撩起衣袍的一角,俯身坐在了离她不远的草堆上,“怎么?想到什么了吗?”
白瑾有些微恼的摇摇头,“我想不到!但我就觉得奇怪,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不对劲?”凌舒痕挑眉,眉心处像被一条细线拉扯了一般,中间有了一丝痕迹。
“嗯。”白瑾咬了咬唇瓣,点点头,“我自小在雪苍山上跟着师父爹爹学了许久的医术,在遇到玲珑之前,并没有被任何问题难倒,可是这次我真的想尽了办法,也查不出她究竟得的是何毒,而且究竟是不是如我猜测的那般,这毒是从母胎里带出来的,我现在也不是非常的确定。”
凌舒痕见她的小脸之上浮现了很是挫败的神情,心中不免有些不舍,知道她遇到了挫折,也知道她从没有被如此的难题难倒过,可是人生在世,不可能永远都是一帆风顺,总会在春风得意时,出现一些让人苦恼的事情。
他很想将心中的所思所想告诉她,却又不忍心以现实的残酷毁了她天真无邪的骄傲。
沉默了许久之后,凌舒痕才开口,低沉的磁性嗓音温柔的宽慰她道:“别想太多了,现在担心也是无用,不如等到找齐药材了,在慢慢的对症下药,总会发现症结的所在,不必太过忧心。”
白瑾心里跟个明镜似的,十分明白他的心意,眸光似秋水,微微的朝他一笑,“嗯。”
凌舒痕有些看呆了,她那淡如凉水的一笑,就像秋夜里的溪水中月华的倒影,柔美、虚幻又迷醉。
他不明白,为何她的那张小脸,会有如此多变的神情,当你以为她是活泼天真的少女时,她又能以妩媚撩人的姿态出现,当你觉得她就是刺骨寒风中盛开的红梅时,她又像一株悬崖峭壁上的野兰,时而无忧无虑、毫无心机,时而清丽脱俗,像个冰肌玉骨的仙娥,时而娇媚动人,时而任情任性。
总之,她的一切是那么的多变,让人好奇,忍不住心中作痒,要去探究。
白瑾并不知道他的心思像个陀螺一般的转悠,只是歪着脑袋看着不远处的火堆,橘黄的火光跳跃,顺带着将她脑海里一直遗忘在角落里的问题,拉出了深沟。
有些急切的扭头看向凌舒痕,“哎,对了,那些迷晕我的人呢?”
见凌舒痕似乎没有反应过来,她有些耐不住性子的抬起手臂,小手拉扯着他的衣袖,“喂,臭狐狸,你倒是告诉我啊,他们呢?”
凌舒痕的神思被白瑾那轻轻的一来一回的拉扯给拉了回来,看着她只笑,不语。
白瑾被他瞧得有些别扭了,直冲着他瞪眼,底气不足的嚷嚷:“你干吗老盯着我瞧,我又没多长出一只狐狸尾巴来……”
凌舒痕俊脸之上有些错愕,随即抿唇一笑,“你现在才想起来?”不给她机会反驳,又挑眉答道:“不见了。”
“不见了?”白瑾一脸的疑惑,“不见了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不见了。”凌舒痕就是不明确的回答她,脸上挂着温润的笑意,可眼中深邃凌厉,当中的一丝寒光就如薄凉的柳叶刀,极细,却凌厉无比。
“你这是什么回答嘛!”白瑾不甘心的又问,誓要将砂锅打破,“他们不在这里了?逃走了?”
凌舒痕双手抱胸,不以为意的点点头,轻应一声:“唔。”
他承认他们四个败类不在这里了,现在估计已经在阎王殿候着阎王的最后宣判了。
至于逃嘛……可以算上一个,宋琴那女人是自己逃着去见阎王的,没等他下手。
“真没用……”白瑾小声的独自嘀咕,“竟然让他们逃了。”
凌舒痕俊脸一垮,装做无辜的样子看着她,有些哀怨的控述:“这可不能完全都怪到我头上来,如果你没有被那**给迷晕了,我也不至于落得如此落魄的地步,我得护着你不被刀剑所伤啊……”
说着装做无奈又哀怨不敢言的叹息一声:“唉……我好心好意护着她,她竟然还不领情,这年头真是好人难做啊!”愁眉苦脸的以掌心撑着下巴,“改明儿,我也扎根山林,当个土匪强盗好了,反正好人没好报,不如做个恶人逍遥快活几年算了。”
“呸!恶人……”白瑾眼珠子滴溜溜的一转,得意洋洋的笑骂道:“恶人倒是蛮适合你的,你这臭狐狸上山,估计老虎都得败在你手下。”
“哦,是吗?”凌舒痕笑得神采飞扬,双手在胸前抱拳,朝她轻轻俯身一拜,“如此真是太感谢小瑾儿抬举我了,真让人受宠若惊啊!”
“嗤!什么人啊,太能把自己当回事儿了!”白瑾斜蹬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还真顺着杆子就往上爬了!”
凌舒痕并不在意她的嗤笑,坐在她对面,勾起嘴角,邪魅的笑着,星目剑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