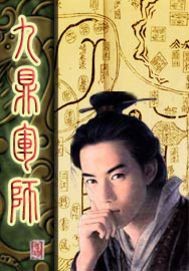凄静的灵堂中,邵安披麻戴孝,尽最后一点孝道。虽然他与父亲常年争执,但对这个爷爷,还是心存感激的。当年,要不是因为爷爷说了一句“邵氏子孙焉能流落乡野?”的话,此刻他估计还是外面的一个野小子,进不了邵府,入不了族谱。
可惜,他的父亲,并无他爷爷的气魄。邵安痛心疾首,要是父亲有爷爷的半点强硬,或者有娘亲的一丝坚强,那么事情的结局,必不会如此凄惨。
然而一切已无法挽回,逝去的终将逝去,该来的早已到来。
※※※※※
泰安元年,安儿归家。
昏暗冰冷的书房内,安儿已跪了一个时辰了。等邵老爷到祠堂请了家法回来,推开门,就着门外微弱的天光,便看见安儿笔挺的跪在阴影中,悄无声息。
安儿听见响动,并不做声。邵老爷见状一愣,没想到他真的会乖乖跪地请罚。邵老爷挥手示意下人们都出去,站在安儿身前开始训话。
“你入邵府的第一天,进了祠堂,拜了祖宗,明确告诉过你邵家家规,可你如今却明知故犯。”邵老爷断喝一声,“说,偷盗财物,是何处罚?”
“偷盗钱财,犯者笞六十。”安儿冷静的背诵道。
邵老爷藤条一挥,“记得倒是清楚,看看你自己干的什么事!”
藤条打在背上,火辣辣的疼。安儿抿着嘴,挨下这一鞭。流放时,他什么样的刑罚没见识过,他爹这点力道,不算什么。
邵老爷没给他喘息的机会, 提着藤条又是几下。藤条杂乱无章的落在背上、臂上、肩上……安儿起先还能忍受,等后面打的多了便会很痛,渐渐地身体微微颤抖。
邵老爷一口气打了二十来下,见安儿只是哆嗦,并没抗刑,心下惊奇。他最恨安儿的固执,当着全家人面屡次顶撞他,拉入书房打,则誓死不从。非得几个家丁按着行刑,才能消停。
邵老爷早已让年轻力壮的家丁在门外候着,一有动静就会冲进了。可打了这么久,安儿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其实邵老爷并不知道,安儿之所以会抗刑,是因为他没有错。对于那些欲加之罪,凭什么让他乖乖受着?然而这次的偷窃之罪,的确属实,故而不会狡辩逃刑。
“呲”的一声,衣服终于不堪重负,被藤条抽烂了。正当安儿昏昏沉沉,神志不清时,忽然感到身后一凉,衣服被父亲扒下了。
邵老爷扒开衣服,清楚的看见那纵横交错的伤痕,层层叠叠的覆盖整个后背。他不由得惊怒道:“谁打的?”
安儿这才转头,第一次认真的看了父亲一眼。
“这些年,你去哪了?”
安儿低头看着地面,还是不说话。邵老爷火气又上来了,但一看到儿子满身伤痕,什么也话也骂不出口了。他刚才还奇怪呢,儿子出门一趟,性子居然会被磨平了。现在看了安儿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痕,终于明白性子是怎样被磨平的。
安儿跪在地上等了半天,见父亲停下鞭打,反而怒道:“你打啊,还剩三十二下。你打完,我就再也不欠你什么,从此两清。”
“还是这么倔,跟你娘一样。”安儿的一句话成功的挑起邵老爷的怒火,便不再顾忌他身上的伤,继续狠狠的抽下去。
最后几十下,邵老爷越打越狠,几乎鞭鞭见血。随着藤条一下紧逼着一下的袭来,安儿一边苦苦熬刑,一边悲哀的想起了哪吒的故事。是否他也要割肉剔骨,才能真正还清生育之恩?
※※※※※
出殡那日,邵家大院张白挂丧一片哀嚎,府前车如云集,众多亲友、邻里,甚至是富豪、官员齐集丧家,前来送邵老爷子最后一程。
只见邵府送殡队伍浩浩荡荡,一路上百人相送,邵老爷子这最后的一程自是无限风光。
等过了尾七,已近新春了。邵安这么多年,从未在家过过年,现下这情形,怕是难以避免了。
前阵子邵老爷主持丧葬,忙得脚不沾地,是以住在邵家大院多日,未曾回府。邵安也乐的在主宅呆着,毕竟邵府对他来说,一直是痛苦的根源所在,直到诸事完毕,才搬回邵府。
邵老爷本想腾出个上房给邵安住的,但邵安闻言冷笑了一下,说:“还是住原来的屋子吧,我习惯了。”
邵老爷吃瘪,讪笑道:“那让下人们给你收拾一下。”
邵安再度冷笑,自顾自的走了。
从八岁后,邵安就一直生活在南边一个小院里。那院子本就是从仆役住的杂院中分出来的一块,地方窄小,且距离正院也远。他八岁时入府,身边只带着一个张妈。可邵老爷却没有再给他分几个仆人,只让他和张妈孤零零的住在这里。等到十二岁那年,张妈患病去世,他也算了无牵挂,便下了决心,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至于阿瑞,是他流放回来时,父亲终于给他分配了一个下等小厮。这些年,阿瑞跟着邵安,也算见了大世面,此次回府,颇有显摆的意味。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好歹他现在是相府的管家呢。
可邵安明白,他和阿瑞并非主仆情深。而且阿瑞到底还是嫩了些,很多事也不敢放心交给他。
等屋子收拾好后,邵安随阿瑞进去看了看。虽说这几年都没在府里住过,但看着院里的陈设却无太大改变,且家具都换了新的。墙上新挂了几幅字画,桌上添了古董,稍微布置一番,看上去也不显寒酸了。
据说邵安拜相后,邵老爷便将南院的奴仆赶去北院住了。所以晚上就不会显得嘈杂喧闹,倒有几分清幽的意境了。
邵安坐在桌前看书,偶尔抬头看看在院子里正指挥着邵府家仆搬行李的阿瑞。那副颐指气使的神态,再也看不出几年前他刚来时畏葸的样子。
※※※※※
行过家法后,安儿显然被打的不轻。昏昏沉沉中,只记得父亲打完后,愤怒的扔下藤条,撇下他就走了。安儿浑身是伤,趴在地上缓了好久,才颤抖的拉上衣服,摸索着回到以前住过的偏院。当他看见杂草丛生,荒废已久的院子时,从心底不由产生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面对眼前的一堆杂物,想收拾也是有心无力。
安儿环顾一周,找了个相对干净的角落,半蜷缩的倚坐在地上。他感觉自己浑身发烫,便将额头靠在身侧的墙壁上,用冰凉的墙面降降温,但也仅能清凉片刻,起不到退烧作用。最终安儿筋疲力竭,放任自己渐渐睡了过去。
翌日,一小厮畏畏缩缩的推开小院斑驳的大门,踏入这偏僻的地方,顿时被里面的荒芜惊呆了。他来邵府小半年了,听老仆役们说,这间院子是邵府的禁地,旁人不得入内。他以为是因为里面闹鬼,从此很听话的绕道而行。可就在刚才,管事的对他说,让他去南面偏院服侍三少爷。
他战战兢兢的在院里张望,可找了半天没看到半个人影。他望着阴森恐怖的正屋,狠了狠心推门进去,一进门就发现安儿歪在墙角那儿,双目紧闭,仿若昏厥。
那小厮吓得慌了手脚,匆匆忙忙的跑过去摇着他的胳膊,大呼:“三少爷,三少爷?”
安儿迷迷糊糊的睁开眼,面前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小厮,十四五岁的样子,傻里傻气的,一看就是新来的仆人。
安儿虚弱的开口:“你是谁?”
“奴才阿瑞,老爷派奴才侍候三少爷。”
安儿冷笑,邵老爷居然会管他的死活?
“三少爷,您怎么睡地上了?”阿瑞扶着他的胳膊,想将他从地上拉起。
“不要称我三少爷,我不是什么三少爷。”安儿甩开他的搀扶,继续靠在墙上,闭目养神。
“三……那叫您什么?”阿瑞略带惧怕的望着自己的新主子,心里直打颤。
“叫公子。”安儿没好气的说,“去,将床铺收拾了,再拿点金疮药来。”
阿瑞连声应道,手脚麻利的铺好床,过来扶主子上去躺着。他这时才发现,主子背后似乎有伤,隐约渗出红色的血迹。
等扶着安儿趴好,掀开衣衫,阿瑞惊悚的看着安儿背后狰狞恐怖的伤痕,新伤叠着旧伤,简直不堪入目。
“上药。”安儿等了半天,不见那小厮反应,便不耐烦的催促道。
阿瑞拿药的手都在发抖,这伤可比他挨打时的受的伤重多了。他轻手轻脚的小心涂抹,偶尔手重了,也不见安儿呼痛。他偷偷打量起安静的趴在床上,一动不动的主子,明明是个风度翩翩的贵公子,然而任谁也不会想到,华服之下,遍体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