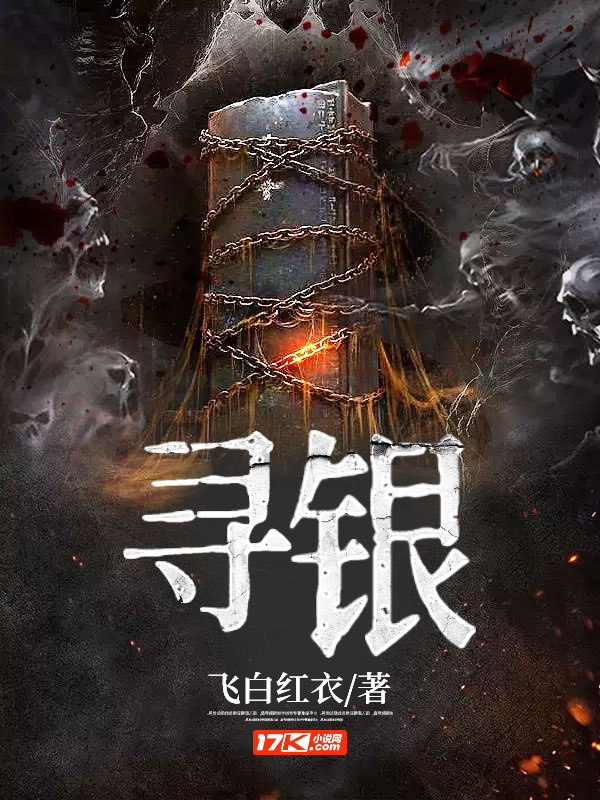赵允他们追着张同,踏入黑暗。
成群毛茸茸的猫儿跑过,喵喵叫个不停。
“好可爱的小猫,赵允,你说他们代表什么?”徐白出乎意料的喜爱猫。
“猫是可爱,那东西可不是。”
黑暗中一颗大树出现在光圈里。高大的树干,纠结的树枝,树皮上疤痕累累。枝头挂满白惨惨的纸钱,一枚枚飘落地面。踩上去,唰唰作响。
徐白眼尖,指着树枝某处间隙:“他的鞋,他到上面做什么呢?”
“据我估计,他要上吊。”
“很经典的方法。”徐白冷不丁冒出句。
张同费力的拿细树枝绑成环状,套脖子上。一咬牙,一闭眼,跳下大树。瘦弱的躯体来回摇摆。
赵允观察片刻,走到上吊者脚下。
“喂,舌头没伸,眼睛没瞪,你这叫上吊吗?”他攥住张同双脚晃动,对方没有反应。他蜷起腿部,离开地面。这下张同舌头出来了。
“上吊死不是一般难看哦。吐舌头还不算什么,眼珠会变得红红的,整张脸青紫,发肿。大小便失禁,啧,脏的要命。时间一长,颈椎骨断开,你的脖子拉的比舌头还夸张。再久一点,肉开始慢慢腐烂脱落,然后是骨头。死无全尸。”赵允无视他拼命蹬腿,挣吧的像条鱼。
徐白:“赵允,你真要勒死他?”
“死不了地,我向来不喜欢这类人。哭着喊着要死,真给他一把刀,他手反而哆嗦上了。”
树枝摇曳,带起张同,似乎要把赵允甩下。张同勉强抓住树枝,暂时不会给勒死。
“放开我!”他嘶哑的叫喊。
徐白摇头,胡闹嘛。他跑上两步跃起,手刀削断充当吊绳的枝条。赵允连忙闪开,被人坐下面的话脸可丢大了。
张同护住喉咙干咳,眼泪鼻涕全出来了。
徐白:“伙计,什么事不能想办法,非要寻短见?也许我能帮你呢?”
张同咆哮:“你管我!我要死你管得到吗?滚远一点,我又不认识你。”
徐白火了,抽出刀,刀背对着他一顿砍。只揍得他鬼哭狼嚎。
“你要死是吧。你这样的我见多了,自以为有个性,要死要活的。自私自利,不想想身边人。芝麻大的事看的比天高,简直污染社会。还死不死。”徐白边揍边问。
张同哭着跑开了,这下噩梦成真了。
赵允拉住他:“下手轻点,你不知道自己力气大啊。瞧人家小身子被你打的。抽根烟,不值得生这么大气。”
徐白点上烟狠吸一口,刚才只当在刑警队了。你说这些不上不下的小毛孩子多麻烦。抓到最多拘留,放出去吧,老祸害别人。耍起无赖你拿他没什么办法。他又不能用像对付狸追那样的方法,作为警察必须合法不是。
张同爬呀爬,摸到门口那,爬了出去。
这次他直接爬进另一见房子,门都没关。
光洁明亮,宽敞的教室里正考试。学生们奋笔答卷,只闻沙沙书写声。赵允也坐在其中,张同位于右前方。徐白好奇的捏起卷子,据说人类努力学习十几年,只为这么几张纸,总算见识了。纸面上写满问题,正反都有。他挠挠头,试着答题。题目大多超出他所知道的,这是数学吧,光数字和公式。幸好没当过学生,太难了。不如他小时候学的容易。五十岁时他就能独自打猎了,五十七学的建筑,盖了第一栋房子,六十以后正式继承家里的法术典籍。七十以后学会幻术,离家到了人间界。佩服这帮学生,十多年学的知识比自己还多,虽说这里的一年比家乡那长。
赵允飞快书写,这点题难不住他。这样,这样,再这样。对于他来说考个学历并不困难。哈,写完了。他放下笔,张同在那愁眉不展。
赵允打起哈欠,好困啊。人懒了,精力自然就差,赶紧收工回去睡才好。他想到这儿,前面的女生硬生生扭转头颅一百八十度,惨无人道的面容吓他一大跳。
“哇!”人吓人,吓死人哪。
张同丢下卷子,夺门而逃。剩下满屋僵尸。四肢残缺的,水里淹死的,肚破肠流的。赵允跳讲台上,有些恶心。徐白手舞长刀,切菜似的切割他们,打的酣畅淋漓。等他切完,赵允去开门。
“无趣,徐白,我要提前结束。等下要吓吓他,别插手。”
出了房间,根据蜗牛的讯息,他追踪到张同的位置,推开门。
报废的流水线,遍地垃圾。灰尘铺满整个空间。看上去荒废了五十年的厂房,光线昏暗压抑。
徐白嗅到张同的味道,绕过前面的设备,在传送带尽头的包装箱里找到他。
张同抱着膝盖,头紧紧埋在怀里。他已经不敢逃跑了。
赵允的目光愈发冷淡,低下头,一字一句异常清晰:“你的房子太多了,该丢掉的赶紧扔开,会发霉的。醒醒吧。”
说完他手放张同背上,略一用力,穿透他的胸腔。再提起,手上多了个白茫茫的雾气。张同死了般歪倒。
虚空里密密麻麻的房间开裂崩塌,发出不甘的惨叫。徐白尽力稳住脚步,封印魂魄?
他们回到现实,张同跌落室内,呼吸心跳全没了。赵允抓紧那团白雾,不让他进入囚石。他两手团住张同的魂魄,快速拍打他的胸膛。
张同猛吸口气,空洞的瞳孔恢复生气。
“亏了亏了,一块囚石都没赚到。这个人的虚空弱的很,懒得要。徐白,我回去了。中秋节,早点回去陪老婆才对。现在不到十二点,来得及。”
徐白:“路上小心。”
他们走出公寓楼,至于为什么出租的房子突然脱了层皮,那就是张同要头疼的事了。
回到家,赵允翻看短信,朱克约他明天去玉无暇。他删去短信,洗完澡,弄瓶干白。相比炽烈的红,他情愿要无色的。就像栗姐常说的,在酒中更容易找到自我。
他举起酒杯,邀请皎白的月:“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