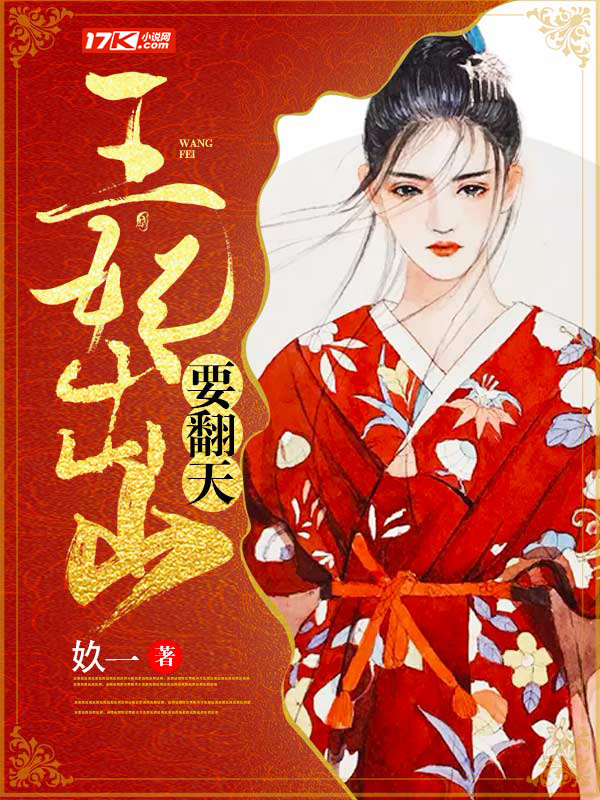不几日,便迎来了新年,除夕那夜,又落了雪,映着红灯笼的光晕,分外醉人。今年的夜宴有些冷清,连杯中酒也在醇香里透出几分萧索的意味,早早便散了。只盼着这场雪过后,来年百姓安康,无波无澜。
琅玕一直在祈王府中守到沈云岫醒来,有红茱入药,过程虽有些凶险,倒也不足为虑。
沈云岫甫一睁眼,便见一个人守在身边,还未看清他的面容,便看到一只指骨修长的手覆上自己的额头,冰冰凉凉,眼前只余一片淡青色,袖缘一圈精致的竹纹。
好一会他才完全适应了光明,恍惚间只觉有人有小勺沾了水,润湿他的唇,便本能地想要更多。阮和泪如断珠,悲喜参半。沈怀稷眼里有些泪光,连忙用手背抹了抹。祈王心悬已久,也总算是放下些许。
待他神思恢复了些许,琅玕才让人把他扶起来,进了些食,人也越发清醒了。
沈云岫眼神清明,一直望着他,“你怎么会在这里?”
琅玕淡淡一笑,取出一枚光滑的竹哨,轻轻吹响,便有一声轻快灵动的应和,一只通体雪白的鸽子从窗口飞入,落在他手上。
沈云岫伸出手逗它,那鸟儿倒也不躲,反叫得更欢,他便也笑了,“它长大了。”
琅玕把竹哨给他,在他手心里写道:别再罔顾生死。
沈云岫目光里闪过一丝讶异,又随即点头道:“放心吧,我不会了。”毕竟救一次不容易,无限接近过死亡的人,都忍不住对生抱有期望。
“哥,你们认识?”沈怀稷小心翼翼地问,可他哥好像也不知道琅玕不会说话。
“嗯。”沈云岫轻声应答,相识多年,今日初次相见,却是犹如故人,过往二十多年中,他唯一珍藏在心底的朋友。
“我已经没事了,你回去吧。”知道他不愿入世,也知道自己身处是非之中,不愿累了友人。
琅玕倒也没推辞,在他手心里写道:好生休养。
“哥,你伤还没好呢!”沈怀稷急道,连忙追了出去,怎么就让人走了?
“我已经没事了。”沈云岫淡淡道,又看向阮和,温声安慰,“别哭,都过去了。”
阮和擦净了脸庞,朝他浅浅一笑,极为听话。
屋子里一时沉寂了下来。阮和一向温婉懂礼,自不多言。祈王千头万绪,却难以吐露一个字。沈云岫疲于应对,连粉饰太平都不愿意。父慈子孝的假面一旦撕下,便是如此地冷酷无情,令人生寒。
沉默许久,祈王还是赶在他开口之前将他所有的话都堵了回去:“你好好休息,父王晚些再来看你。”说完便匆匆出了屋子,几乎是落慌而逃,他怕儿子一旦开口,全是他不想听的。
沈云岫牵动嘴角,寡淡一笑,倒也没说什么。只把阮和拉近了些,柔声道:“我吓到你了。”眼前人双眼红肿,湿漉漉的,一看就没少哭。
“也没什么,早就说好了,你若去了,我便守墓。”阮和一语带过,全然不提她的日夜守候,恨不能以身代之。
“可我舍不得,我后悔了。”沈云岫握住她的手,目色温柔,“先前在碧水城说的那些混账话都不作数了行不行?”
“我原本也没当真。”好不容易才等来他亲口说出的白首不离,退婚的胡话自然是不听的。
“先前是我不好,往后都交给我。”沈云岫目光坚定,足以撑起两人的未来!
一连二十余日,祈王都避而不见,沈怀稷倒是紧张他,日日都来探望,怕他与父亲嫌隙更深,还帮着解释。
“哥,父王他很担心你的,之前都一直守着。”只是现在突然就不来了。
“嗯。”沈云岫漫不经心地应一声,看起来毫不在意。
“哥,陛下送了好多药材过来,用不了多久就会痊愈了。”言外之意是陛下也护着你呢,不用担心。
“谢谢你!”沈云岫淡淡笑道,陛下是不会这么明着偏袒的,只能是怀稷自己去太医院里搜刮,没人拦得住罢了。
“哥,母亲早就在准备你同阮和的婚事了,我们家好久没办喜事了,肯定热闹。”沈怀稷越说越高兴。
“这是我的事。”沈云岫纠正,他从未想过要在王府办亲事。
沈怀稷当作没听懂,继续道:“这是你的终身大事,自然要好好筹备。”
沈云岫也不多解释,只道:“怀稷,我想见父王,总不见也不是个事。”
“父王最近比较忙。”沈怀稷脱口而出,说完才觉不妥。
“这话你信吗?”沈云岫反问,试问整个都城,还有谁比祈王殿下更闲?
“哥,我们先好好养伤,多思多虑伤身,别想那么多。”沈怀稷道,“每回在外面都一身伤,父王以后肯定不放你往外跑了。”
沈云岫沉默不语,这就不是别人能决定的了。沈怀稷见他神色淡漠,便也识趣离开,不再扰他,很是闷闷不乐,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大哥自小护他,什么时候变得越来越疏离了?沈怀稷摇摇头,前去传话,父王吩咐的,每日都要汇报一次大哥的情况。祈王听了神色晦暗不明,终于在三日后又去了倾澜微雨。
沈云岫虽说已无性命之忧,身子却要好好调养,平日里都待在屋子里,极少下地。无人的时候看着窗外出神,静静地半日也就这么过去了。
“哥,父王来看你了。”沈怀稷轻声将他唤回来,心里有些忐忑,为何父子见一面也会有这么多顾虑。
沈云岫回神,望向来人,目光淡漠的有些可怕,没有希望,没有怨恨,平静的像一湖水。
“你们如何判决我的罪责?”沈云岫冷静问道。
沈怀稷立刻劝道:“哥,把伤养好才是要紧。”
“费尽心思救我,总不至于是要再杀我一次。”沈云岫淡淡道,一切抛开来说,也好早些解决。
祈王在他身边坐下,缓声道:“父王不会再让人动你分毫,先把伤养好,康健些才好娶阮和,阮和是个好姑娘,定不委屈她,往后就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了。”
沈云岫了然:“画地为牢,软禁我一辈子。”
祈王承诺:“父王会找时机让你重获自由。”
“这样的惩罚未免太轻了,这结果也非我所愿。”沈云岫摇头,望着父亲一字一句犹如天倾地陷,“请父王将我宗谱除名,逐出家门。”
祈王浑身一颤,不可置信他竟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说什么?”
“哥,你胡说些什么,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沈怀稷震惊,又一阵恐惧,自古非丧尽天良,让祖宗蒙羞者,绝不会宗谱除名,这是要被万人唾骂的!
沈云岫看着祈王,“我有今日之果,皆因血脉所累。祈王一世英明,不必为我背上污名,我除宗谱,出家门,自有一番新的人生,皆大欢喜,又有何不可?”
“从前是父王错了。”祈王深吸一口气,胸口钝痛,而今才道当时错,满眼春风百事非。
沈云岫却摇头:“你没有错,母亲居心不良,你们杀她无可厚非。我身为人子,为母亲复仇也是人之常情。你对我不加管束,大概是想我平安过一辈子,不成器些也无妨。只可惜,我没成长成你希望的样子,这才有了今日的局面。”
倘若祈王府的大公子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胸无大志,整日里交些狐朋狗友,干些斗鸡遛鸟的荒唐事,无论多不成器,都能在祈王的庇护下平安过一辈子。
“别说了,父王绝不答应。”祈王被道破心事,他的确这般想过,可也没真把他往那条路上引,要成就一个人不容易,养毁还不简单么?顺其自然,看他长成人人称颂的翩翩公子,到底是更高兴的。
沈云岫一声讽笑,语中带刺道:“把我留在身边,你不觉得难受吗?囚我于王府,日日与你们相见,只会让我心中怨恨不断增长,我能杀一个,自然能杀第二个。你何必让怀稷给我陪葬?”
沈怀稷瞪大眼睛,大哥在说什么?
祈王定了定神,他发现已经不能以寻常父子的相处方式来同儿子交流了,他是在抗争。“你不会,云岫,你今日敢对我说这些话,倚靠的还是我对你的愧疚与不忍。”
“是。”沈云岫承认的很干脆,“我在一日,你便家宅不宁一日,我离你所谓平安喜乐就会越来越远,最终父子成仇,兄弟反目。我赌你不敢毁我下半辈子。”
祈王面色一变,拂袖而去。胸中气血翻涌,喉间隐隐一股腥甜,气愤之余,更多的是悲哀,竟是如此固执地拼了命的想要斩断与父亲的一切,宗谱除名,从此就是陌路,云岫决绝至此,怕是连陌路的机会都不会有。
沈云岫不停地喘气,脸上升起一股病态的潮红,似是用尽全身力气打赢了一场仗过后的轻松,低着头似哭似笑:“多谢父王。”
“哥,父王没答应。”沈怀稷悲从中来,为什么他哥拼了命地想要远离这个家?
“他会答应的。”沈云岫背靠在软枕上,总算平复了一些,他隐姓埋名,安稳一生,祈王府依旧高高在上,金尊玉贵,两者再无相干,这是最好的结果。
沈怀稷转身出去,突然很不想见到他。
沈云岫拉过阮和,握住她的手,“别怕,天下之大,会有我们安身之处。”
阮和笑着点头,道:“我不怕。”
“碧水城的家是不能要了,不过这世上有许多地方我还没去过,我们一处处相看,定要挑个合心意的地方。”
“公子,”阮和忽然打断他,一颗泪珠忽然滚落,“不开心说出来也好,静一会儿也罢,不要装作若无其事,阮和看了难受。”
沈云岫闭上眼靠在她肩上,叹息里是浓浓的疲惫,他真的是非常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