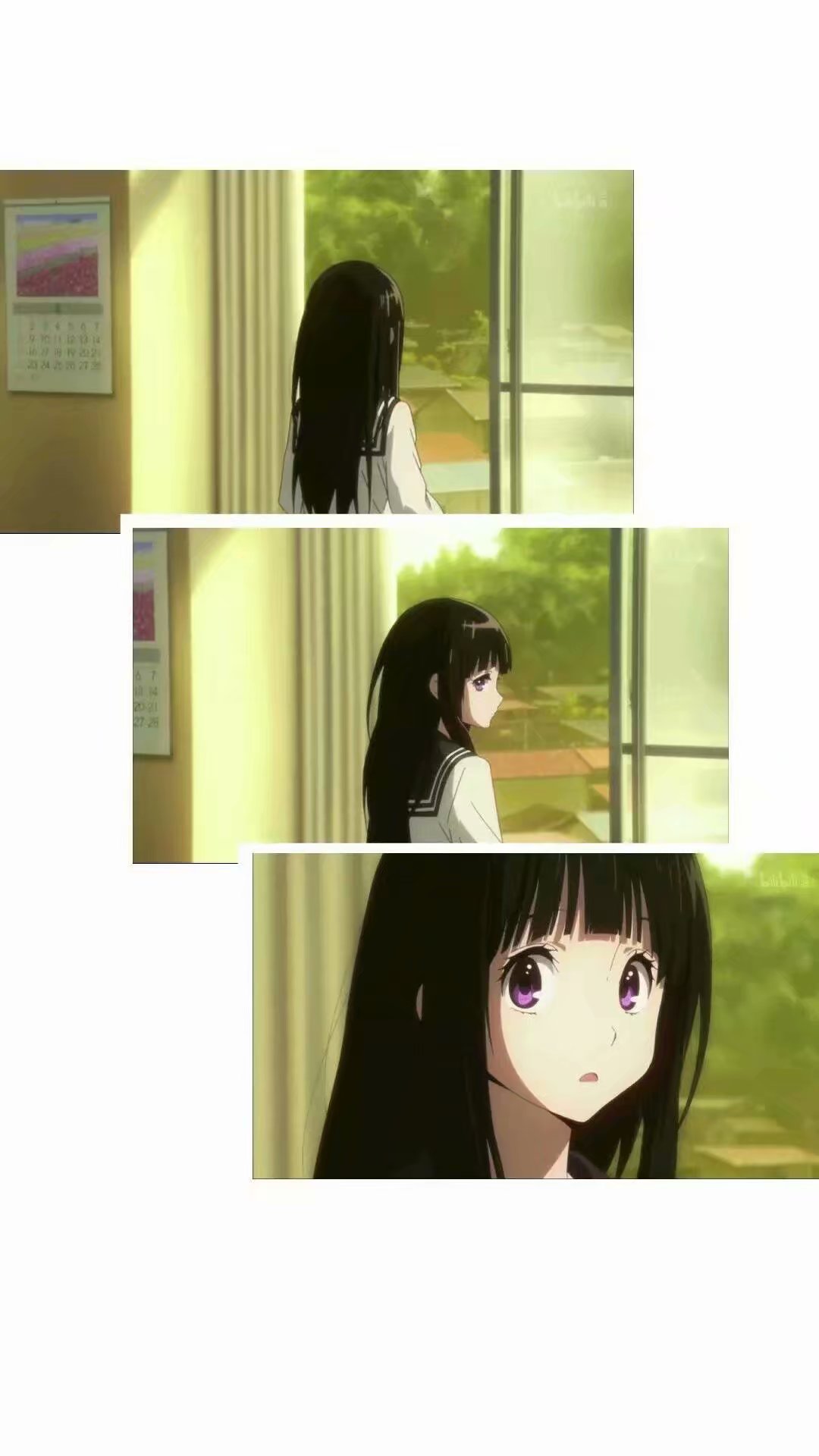“凭你的卑微就算知道了我的身份也只是徒添负担,有这个空闲,不如先去一一叩谢你的神。正是他们庇佑,你才有幸站在我的面前一直说话到现在还安然无事。”在青年右腕上的剑身稍停片刻后再次“起步”向上面的臂膀移去。尼撒有意抓攫青年仓惶逃窜的视线,似笑非笑的深瞳着实叫人毛骨悚然。“难道你们家族就没人了吗?挑这么一个狗仗人势的废物继承,简直就是自取灭亡。”
这边话音刚落,那边再次尖叫声起。
眨眼间,似乎有道什么东西比电光火石更快的速度从眼前一闪而过……稍后众人只见青年双膝跪地,弓着身,左手死死抱着右臂,几注殷红的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流出,顺着他白皙如玉的长臂滑下,在指尖滴落。
“啊……”这时,人群中也不知是谁又扯起嗓子猛叫了一声后就连滚带爬地跑出了神庙。于是这种连锁效应下,被吓得连魂都散了的众人便都一窝蜂的向神庙那扇仅敞开的大门涌去,一心只想赶快逃离这块是非之地。
“身为大家族的下一代首领,小小年纪就狂傲自大,不懂收敛。惹恼了我,竟还浑然不知?”低头看着跪在地上,全身剧烈哆嗦的青年,尼撒紧抿薄唇,双目含火。拿着马鞭的右手五指微动,原本卷曲在他手中的鞭子就伸直弹到了地上,溅起一辙微尘。声音虽轻,却是实实在在笞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里。
“滚回去告诉你的王,以后派人出使我巴比伦,千万别是你们契可弗尼德的人。否则我见一次杀一次,抛尸荒野,挂首城门示众。”举起左手,尼撒的眸子倏然敛紧,声调拔高。他用锋利的剑尖直指青年的额心,上面还滴着对方的血。
青年不敢再抬头看一眼尼撒,只能强忍疼痛,跌跌撞撞向门外跑去…...
偌大的庙堂里经过一轮又一轮躁动和沉寂的更迭,现在终于确实的静了下来,只剩下尼撒和塞米拉米斯,以及那两名护卫。
尼撒把手中的长剑和马鞭递给身后的护卫,眼中的怒火并未完全消退。他看一眼站在原地垂着头的塞米拉米斯,只对她说了一句“跟我来”,就率先走出了神庙。
塞米拉米斯紧缩着双肩,握着刚才被青年握过的左腕惴惴不安。破坏了坐庙礼,眼下不知道他又会想出什么法子来“惩罚”自己,如果现在听话跟了上去,是不是就代表接下来还有比坐庙礼更恐怖的事情发生?可是留在这里,连米底契可弗尼德家族的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他,她真的能够反抗他的决定吗?
内心彷徨,脚下踌躇,塞米拉米斯抬眼偷瞄着那抹可怕的背影,终得小心翼翼迈出了第一步。
外庭一处栓马的角落,尼撒在一匹红棕色的健马旁停了下来,他取下马缰后转过身想确定塞米拉米斯有否跟上。哪知他的视线才刚碰上她,她就惊慌得连脸色都变了,迅速耷拉下脑袋,双手十指不安的绞在一起,脚下也接连退后了好些步。
见她对自己已经惧怕到了如此敏感的程度,尼撒的心里如五味陈杂,难食其味。低头看着与她之间那段肉眼可见的距离,不觉勾唇苦笑,怕是很难再恢复了吧?……横在他俩心中的那段距离。想她第一次是主动靠近自己,现在却学会主动与他保持距离了,或许对她来说,只需这样就是最安全的。
然而,他仍是义无反顾踏出了那一步,毫不迟疑的走到她面前。
“如果他手里拿着一把匕首,你像刚才那样胡乱挣扎,不是只会伤害自己吗?”牵起她的左手,尼撒没好气的责备道。
看着她皮肤白皙的腕上那道刺眼的指印,他神色凝重的皱起了眉头。“嘁,该死的在说些什么,这是我自作自受。”自我矛盾的自我否定,他正在跟自己拗气。用手掌中唯一没有被磨出厚茧的掌心轻轻为她揉着印痕的位置,生怕指节上的老茧会刮到她的皮肤。
塞米拉米斯错愕的看着他为自己揉手的动作,以及脸上那让人捉摸不透的表情。腕上疼痛的感觉开始变得暖暖的。“陛下,那个米底人……”
“我从来没有爱过米梯斯一天。”继续为她揉搓着腕上的印痕,尼撒打断她的话,又自顾言语一通,没有抬头。“你清楚。当初打败亚述的时候,先王新建的巴比伦王国还不过一只羽翼未丰的雏鸟,别说称霸西亚,单单是整顿迦勒底内部就要耗费一番。所以那时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同盟国支撑,而从起义之初就与我们一起对抗亚述的米底是最好的选择,我必须和米梯斯成婚以巩固两国联盟。”
塞米拉米斯没有搭腔,只是静静地凝望着他,诧异他没头没脑的自言自语。她的确是想和他谈及有关米梯斯的话题,那个青年虽然口气狂妄,但他说得没错,米梯斯是远嫁到巴比伦的米底公主,两国之间无论哪方的丁点动静都会对她造成影响,都会影响两国多年保持的盟约。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突然地对自己说他不爱米梯斯?
“还疼吗?”眼见印痕似乎颜色淡了不少,尼撒才稍安的抬起头来柔声关切一句。发现她正看着自己,与她的视线匆忙碰撞后又别别扭扭转向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