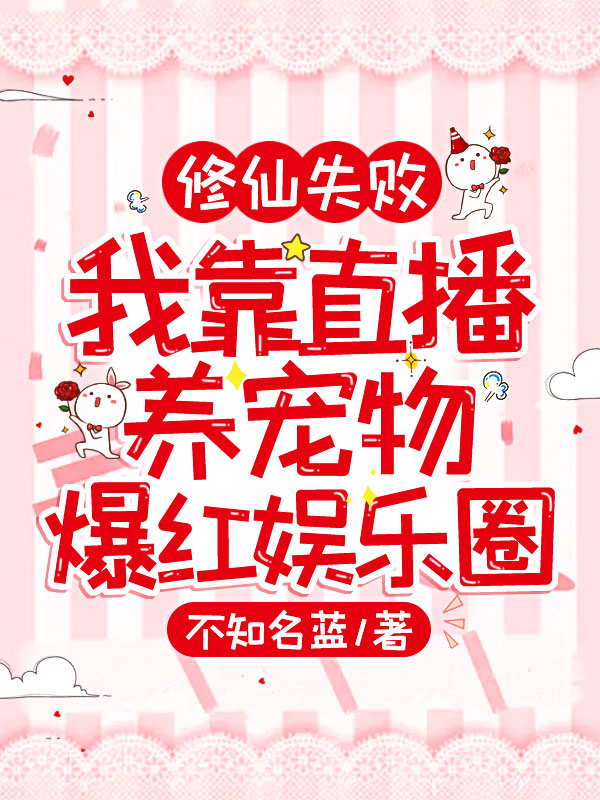“你确定?”
“是的,大人。”奇卡尚未脱净青涩的声线中还扣着断断短短地颤音,只是却能莫名让人相信他没有说谎。
确实得到了奇卡的回答,里斯浦之前还沉敛的瞳孔豁然张阔,眸子里悠着让人毛骨悚然的惺惺笑意。凌厉的直冲都奇,“奇卡,你当真不记得自己的救命恩人了吗?当初你无意弄错了夫人的汤药,险些害得夫人中毒,幸得这位大人出言相救,才让本官饶你不死。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
“请大人明鉴,小的真的从未向夫人送过任何汤药。”今天的混乱对于从未上过真正战场的奇卡来说就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战役”,所以还停留在单纯少年期的他哪会知道这识人的背后竟藏有这样一条“凭空捏造的罪状”,当场腿肚子一软,也就吓到趴跪在了地上。
低头看着地上全身哆嗦个不停的奇卡,里斯浦反而似有什么计议得逞的掂起了唇角。“恩,本官知道。这里已经没你的事了,先出去吧。”
里斯浦轻松洋溢的语气比他居高临下的气势还要沉重的压迫着奇卡单薄的背脊,他颤咧咧的仰起头,这样的位置和距离除了看得见完整的下颌,就见不着任何一个表情。何况以自己卑微的身份,更不可能直接向这位大人询问他是真知道还是假知道,只能暗自默在心底,乖乖答“是”,再悻悻起身,两步一回头的离开了木屋。
“如果都奇没有遗失前世的记忆,应该不会忘记刚才那个小侍卫。他曾一直奉命于府内,有一次塞米拉米斯旧病复发,你我均不在府中,只有布斯特留在房间里照顾,那天恰逢在庭院内巡视的奇卡路过,一个人忙得焦头烂额的布斯特便说要让他代劳送药。但是没想到布斯特千叮万嘱,粗心的奇卡还是大意端错了药碗……”视线放回都奇身上,里斯浦的话中有意无意绕着尖刺。“再后来就是你我回府之后的事了,为了帮助奇卡逃脱责罚,你以塞米拉米斯的名义收他做了你的义子,还记得吗?”
“老奴当然记得,只可惜他已经不记得了。”都奇摆出一副惋惜的模样,然而在里斯浦滴水不漏的视线密布中,从那只独目底下匆匆晃过的一种叫做“心虚”的影子还是被逮了个现形。
“不是可惜,是你自己心里有鬼。”里斯浦也不再拐弯抹角,冷冽的视线牢牢监控着她脸上任何一抹情绪的潜移,索性把话都摊开了的说。
“大……大人何出此言?”果然,在里斯浦如影随形的视线跟踪下,都奇自信的眼神开始煞不住的层层软化。最终只得以垂头躲避那束利刃般刻薄的寒光,细腻纤和的声线也跟着低沉的头颅狠狠滑了下去,支支吾吾含混不清。
“没错,陛下率兵出征的消息是众所周知,得到这个消息的你来找我也无可厚非,毕竟陛下离宫,我就便是这巴比伦唯一说话能算数之人。可是你忘记了一点,都奇,奇卡不记得你,这并不奇怪。真正的问题在你,一开始就断定了我认识你。”仍站在门边的里斯浦顺势将身体斜倚在门桓上。看着都奇的双瞳并未放松警惕,其实就现在这种情形而言,他也不清楚自己的信心究竟从何得来,只是经过以上两人的对话,就会如此坚决的认定都奇此次现身的目的绝不单纯。
“知道吗?我们现在身临的这个巴比伦,包括尼撒在内,上至贵族高官,下到平民百姓,每一个都是和奇卡一样被消除了前世记忆的人,这个世界,仿佛是被上天获许了重生,只有我才在一次意外中捡回了对塞米拉米斯的记忆。后来又阴差阳错,尼撒就像曾经一样,将他最宝贝的女人托付给了我照顾。”里斯浦淡笑着。脑中没有刻意的意识,这些话就如行云流水一般,不知不觉间逸出了唇齿,促使他没有办法去圆滑掩饰心中的硬伤,只能苦撑。“洛西说是你把她重新送回到这里的,那么就证明你对这个世界与前世的差别略有认知,至少不会像洛西初来乍到时那样记忆全无。可是刚才你的眼睛却明确的告诉了我,你和奇卡互不相识。既然不记得义子,怎么又惟独记得住我,这难道还不够让人匪夷所思的吗?不过,若是那帮想方设法陷害塞米拉米斯的人,我想就另当别论了。”
猜不出,不管从哪方面考虑他都猜不出答案,只期盼能在都奇身上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个小碎卒,老奴确实很难有印象。”听出里斯浦话中极不友善的弦外之音,都奇蓦地抬起了头,却见他是表情漠然,不答声腔。娟秀的唇角自嘲地扯出了一道弧度,接着沉声叹息道。
“既然大人已经想到了这一步,就请就地处决了老奴吧,老奴愿坦白一切……”话尽一半,都奇细微观察着里斯浦的表情变化,依是冷漠得没有半点波动的迹象。“那天城楼上的……原本都是老奴的计划。”
这番话的确是里斯浦始料未及的,他从门框上缓缓起身,静若冰面的眸子里终于有了些细漾微澜。
“大人还有所不知吧?关于弋兹帕特族的千年诅咒,解除它的唯一方法其实就在每任族长的身上,而现任的第九位族长——是塞米拉米斯……”都奇没有再说下去,她想,以里斯浦过人的头脑,联合那天在城楼上所发生的事应该不难想到。
“刚才我就觉得奇怪,你是我们所有人中最了解塞米拉米斯的一个,怎么会说出要我和她在一起的这种话。我甚至还清楚地记得你说过,就算尼撒的王宫是一个万劫不复的火坑,你也会陪着她一起往下跳。”声音带不进任何感**彩,英挺的五官冷硬得也像是一具塑像的雕砌。“你说你把塞米拉米斯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那你又清不清楚,她也同样把你当做生母一样依赖。迄今为止你的所作所为,亲手把她送回到这里,就是为了取她性命?”
都奇又重新垂下了头,闷不吭声。
“不可能,你没有理由这么说,曾经的三千年都相安无事的渡过了。现在你凭什么要这样草率决定让塞米拉米斯只身去承担这个责任,没有理由,你们谁都没有理由擅自决定她的生死。”从都奇的身上匆忙撵开视线,里斯浦的神情开始不由自主的慌张起来,清隽的紫瞳在整个木屋内急促的扫晃着,口中喃喃自语。
“凭我是弋兹帕特族第七任族长的长女。”都奇理直气壮的说着,接着便从袖筒内拿出了一把银色匕首,抽出刀刃,二话不说就朝自己右腰侧的衣料划去。随后只闻“呲”地一声,那处衣料应声裂开了一条缝隙,都奇微微拉开着缝隙展示在里斯浦面前。
“相信大人不会陌生,殿下身上也有个这一模一样的胎记。刀刮不掉,火烧不烂,这就是镌刻在弋兹帕特族族史里的永恒印记——史提梵尼瓦图腾。”
里斯浦怔怔的紧盯着都奇腰间那个黑色的扭曲图案,一动也不动。那些分分合合,重叠不断,譬如妖魅的黑色幻影啊,在他眼前不停来回的肆意张舞着,凝结了他全身激流的血液,四肢冰冷麻木,脑袋里嗡嗡乱响一团。
都奇的话就是雪后初霁的一捧融化,浇遍全身,浸进肺腑,冷彻骨髓。
“荒谬,简直一派胡言。”晃过神时,生硬张启的唇舌中,只能挤出这样一句。
动作木讷的转过身,里斯浦又脚底生根般的在原地停滞了数秒。
突然,在这个促狭的空间内就是那么恍然逝过,极为短暂的一瞬……
毫不犹豫的单手操起一旁的木椅,对着临近的长方木桌就狠狠砸了下去,顿时,只有“哐”的一声冲破屋顶,划破长空。木椅和木桌同时沦为他发泄过后的牺牲品,稀里哗啦垮散一地,支离破碎。
都奇全神屏住呼吸,紧张的闭上了眼睛,不敢再去注视那个怒意燃烧的背影一眼。尔后不久就听见了门扉被重重扣上的声音……
“押送至东宫地牢重点看守,未经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探视。”
在门外那双沉重的脚步声响起之前,他对几名站岗的侍卫如是留下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