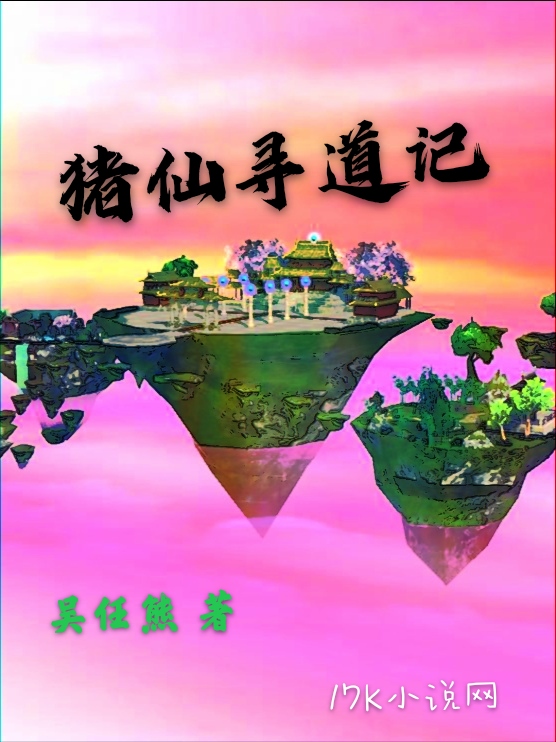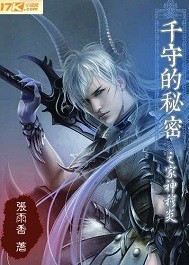塞米拉米斯呆若木鸡的杵在那里,像是一尊石化的雕像。她怔怔的看着俯在地上的耶利米一言不发,不知道现在的自己是否还有资格和能力去接受面前这位神之圣子的跪拜。
“所以……你到底是犯下了什么不能让犹太王饶恕的罪过,非要这样把你逼出耶路撒冷?”
“殿下,自当朝执政王约雅敬陛下统承王位以来,整个王室的局势就被他彻底颠覆。现在的耶路撒冷,相较约西亚先王在位之时,形存实亡。”
“约雅敬?”塞米拉米斯虽是顺口唸着这个对她来说并不算陌生的名字,却并未亲眼见过其真正的主人。“七年前他被埃及法老尼科扶植上位,后遭其改名‘约雅敬’。”
“是的,殿下。陛下本名利亚敬,是犹太王室的第六皇子,先王约哈斯陛下的皇弟。十年前亚述王室的瓦解不但没有稀散西亚的战争,反倒促成加剧之势。埃及和巴比伦这两大曾隶属国为了能够接承亚述昔日的霸位,故而将战场转移到了西亚中下部一带,岂料埃及在初战之期出师不利,连吃败仗。当时法老尼科眼见自军士气不断受挫,不得已,只能调回曾在纳西比纳一战之后被革职的上埃及领军统帅……”话到此处,耶利米不禁嘎然止声。虽低埋着头,可仍是忍不住微微抬起眼角斟视着塞米拉米斯脸上的神色。
“请恕耶利米冒犯……”暗忖思酌片刻,便又重新垂下了眼睑。他知道,在此旧事重提只会加重她对自己目前处境的负担,但这件事,包括那个人都到了不得不坦诚言明的地步,就让身为犹太先知的他为了侍奉的君主自私仅有的一次。因为即使他现在不说,总有一天,时间的缝隙也会自动将那些过往一点一滴排挤出外,昭然惹眼。“越过巴比伦王手下五万精兵的严防密布,只带一万人马便顺利攻陷耶路撒冷,像这种冒进的方法容不得半点差池,可是他……被称为‘埃及最后一位勇士’的拉舍斯夫却成功办到。”
听得出他的话中已是尽量拈轻避重,有关七年前那场血染逝尽的战争似乎也经他沁凉的嗓音过滤成了一个个和谐的静逸诵符。只是这些,仍没有办法填补她内心的黑洞,他是视观百态的神谕之子,无所不知的伟大先知,所以他理应透析这个世间的种种发生……清楚当年纳西比纳时围绕在她与尼撒、拉舍斯夫三人之间的微妙情愫。可她不同,她至今都没有办法去冷静思考拉舍斯夫曾执意出兵耶路撒冷的原由,没有办法接受后来才为自己所知的真相。
——七年前 某夜——
“拉舍斯夫,你现在撤兵还来得及。不要去耶路撒冷,至少请你这次千万不要对耶路撒冷发兵。”就在拉舍斯夫所率领的埃及密遣队准备动身前往耶路撒冷的前一晚,早已获知他们军情的塞米拉米斯便在自己的营帐内设水施咒,想要借此与拉舍斯夫对话,以打消他出兵的念头。
然而以水为媒介的那一端久久杳然无声,得不到一句明确的答复,只能隐隐听见他沉重郁缓的鼻息。等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拉舍斯夫才终于开口。“塞米拉米斯,我已经没有机会了,除了这一次,我以后不可能再重返战场。所以我绝不会放弃。”
“不放弃?难道你要拿自己的性命做最后一次赌注吗?”方知要他死心不易,却也没料想他的决心居然坚若磐石,这不禁让塞米拉米斯又急又气。眼下战势风喘云啸,她深知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势在必得,现今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拉舍斯夫临时改变主意,力避祸端。
“这不但是我最后一次为自己下注,也是最后一次和你说话。”不及话意坚定,往日桀骜的腔调犹如剥茧抽丝一般稀空乏力。“当初得知你被尼布甲尼撒带走以后,惹得你父王大发雷霆,迁怒众多。西亚好几个城邦的王公连其法老均被传召到尼尼微受审,事后我也以带兵不力之罪被收回手中兵权代免死刑。所以能够重获兵权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哪怕是命悬虎口,也不足为惧。”
“……”一时,拉舍斯夫的陈述让塞米拉米斯无言以对。就连一句衔在嘴边的“对不起”,却也是硬生生给咽回了肚里。任何方式的道歉就现在而言都是毫无用处,弥补不了那些因自己被俘而无辜丧命于父王剑下的冤魂,抵消不了在她心中根深蒂固的罪孽。
“你若执意出兵耶路撒冷将必死无疑。”悔望莫及,掂量当下情势,她更急于相告实言。“我不是危言耸听,占卜里只显示出这一个结果……你的死期,卦象之上预示了你的死期。巴比伦王在巴比伦和耶路撒冷两城之间设立了多个隐秘联络点,你们这一去则是牵一发动全身。拉舍斯夫,你带兵向来严谨,两军交战三年以来你们无一胜例,优劣势态显而易见,如果趁这种时候还分散兵力对你们只有百害,而无一利,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手栽培出来的将士白白送命吗?”
果然,一席劝解诚辞之后,让那端再次没了声儿。可这样偶尔一阵阵气氛怪异的沉默越发弄急了塞米拉米斯,她恨不得可以立刻睁开双眼仔细看清面前的水盆,尽管不见他的脸,也想凭借那鳞波漪漾的水面为自己给获一点点莫须有的勇气和安慰。
“之前法老免去了我的职务,才使得我侥幸避免与你兵戎相见。本以为这次在劫难逃,没想打听之后才知道尼布甲尼撒已将你软禁起来。”拉舍斯夫声气吞吞的说着,呼吸换气之间淡透着一丝惬意,“呵,真是天意弄人,你我二人曾并肩作战,如今却立场倒置。”
“父王生性穷奢极欲,不惜花费重金为我建造‘卡斯奇兰’;管理朝政残暴无纲,嗜爱穷兵黩武,每当战事吃紧之时,他就会下令将我关在‘卡斯奇兰’内不准踏足半步。在众臣民眼中,他是令人胆寒心惧的暴虐君王。可是在我心里,他永远都是一位和蔼的父亲,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不愿离开的人。我也不清楚那种感觉到底是从何开始,竟会把令人称羡的宠爱转念成了漫无止境的恐惧,恐惧到迫不及待想要离开他。”说着说着,塞米拉米斯情不自禁的收紧了双肩。似乎又来了,那抹曾从心底串遍全身的凉意……不觉何时,久寄身心,如鬼魅一般挥之不去的它们似乎在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渐渐苏醒,再次活跃在她的体内张狂肆叫,掀风卷浪。
“下定决心离开尼尼微以前,我一边看着父王统治下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西亚,一边仍不停为他出谋划策攻占城池,扩大版图。底下没有一个人敢公然上奏请愿,只有时任巴比伦尼亚城关大臣的那波帕拉萨尔大胆举旗反抗,甚至就连手握王室重兵的八皇兄也为此暗称叫好……就像你,你从来都不会为个人名利嗜战,你说过你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辅佐你的君主把埃及变回六百年前拉美西斯二世的盛世,你……”
“如果你至今依然只是把我看作‘兄长’。那么就请你答应我一个请求……帮我找到我的孩子。”拉舍斯夫匆忙打断塞米拉米斯的话,愠怒的声音中紧扣微微颤栗。
“你的……孩……子?”惊于他的说法,塞米拉米斯的大脑顿时懵白一片。
“恩,我的孩子,是我和埃及王妃背着尼科苟且所生。你的占卜没错,因为抵达耶路撒冷以后我会向尼科如实禀明这段**。既然我自知无能砍下尼布甲尼撒的头颅,也绝不会让自己轻易死在他的手里,这次我势必要让他在耶路撒冷一败涂地。”拉舍斯夫声线冷冷的说着,虽似恢复了以往的精神,却反倒给予塞米拉米斯相差甚远的感觉。
“为什么一定要做到这种地步?”塞米拉米斯不可置信的质问道。以她对拉舍斯夫的了解,不敢相信刚才他所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和他失去联系的这些年里,在他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为什么他要去染指法老的王妃,一向自诩不凡的他为什么允许自己活得如此狼狈?
“届时我会传书底比斯吩咐我的侍从卡文尔将孩子抱出城,日后你们相见的信物就以我最常戴的一对耳环为证。”拉舍斯夫对塞米拉米斯的话充耳不闻,继续一股脑的自说着。“塞米拉米斯,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可信可托之人。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帮我找到那个孩子。”
“恩。”塞米拉米斯只是极轻极轻的应下一声,感觉有什么东西梗在喉咙,她想要找到宣泄的出口。
“塞米拉米斯,你要相信我,像以前一样相信我……相信我所能为你去做的最后一件事。”
“恩,我相信你,一直都会相信你,和以前一样。”塞米拉米斯不敢再多问一句,她用力哽哽喉咙,不知道重复这句话到底是在告慰他濒临绝境的情绪,还是在平抚自我激动的内心。微热的空气下,只感觉两滴冰凉的眼泪顺过脸颊滑下。
“咳,看来在你面前我还真是不习惯绷着这张脸。实话告诉你吧,其实从刚开始我就很兴奋,一想到你担心我的样子就真的止不住。呵呵!”明知道她看不见自己此时的表情,可拉舍斯夫还是在那里一本正经的舞弄着拙劣的演技。似受宠若惊的傻笑,败泄出欲盖弥彰的反效。“塞米拉米斯,我一直坚信自己会找到你,一定会找到的。所以希望下次见面,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的名字。”
“拉舍斯夫……”
“恩。”
于是,这场对拉舍斯夫来说是临别遗言的对话,也在他最后一声轻到几乎听不见的回答下被圈上了句点。当咒术的热气散褪全身之际,塞米拉米斯缓缓睁开了眼睛,看着余波未平的水面,看着悄然躺于水底的一只红色耳环,与飘散着她血液的淡红水色默契的重叠在了一起。